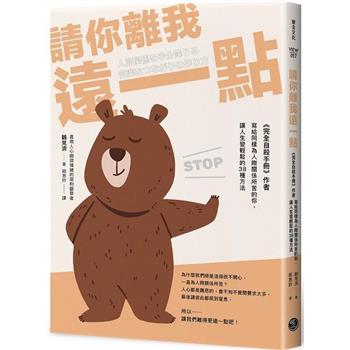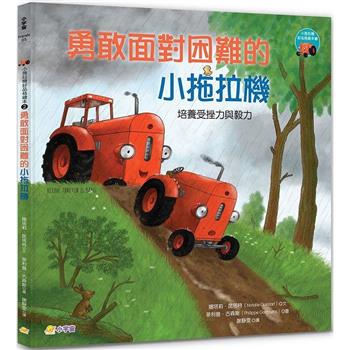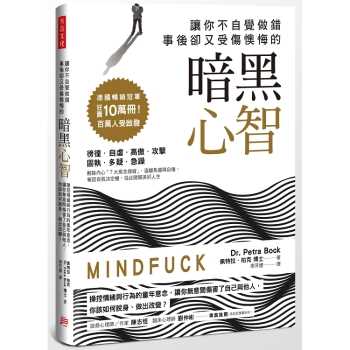如果可以重來,你想要同樣的孩子嗎?
真實記錄一對母子脫軌失序的人生,重新演繹親情的無限可能
J.P.聽的音樂像是跳針的唱盤,同樣的段落不斷迴盪;J.P.寫著同樣的日記,直到紙張用盡;J.P.最愛提的問題就是「然後呢?」,一再重複,即使在你給他每一個答案之後;J.P.是個難以跨越時間深淵的孩子,他快速旋轉,他瘋狂拍手,他重複再重複,直到生命盡頭。
就美學上來說,重複是美好的。每一個做父母的都知道孩子們多麼喜歡重複,每天晚上講的睡前故事,在笑話搏君一粲之後一次又一次地重來。重複意味著安全、儀式、熟悉。但它也可能意味著乏味。J.P.做的其他重複動作並不像旋轉或拍手那般無害。多年來他都會撕紙,總是把身旁的東西拿來咬嚼,我們屋裡裝潢完成的地下室已經被他破壞殆盡,除了撕扯、打砸之外,他還在所能碰到的任何地方塗鴉。他隨時會倒在地上,又踢又叫,咬他自己的手或咬我。我知道臨床上所有J.P.為什麼打我的理由,我也知道,在我對他濃烈的愛之外,我也得接受挫折和羞愧,甚至憤怒等這些隨著身為他母親身分而來的感受。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讓他走,但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讓他留下來。我已經筋疲力竭,沒有資源也沒有辦法再承受像他那樣我無法控制的轟炸,我無法再保持平靜。」
克萊兒.鄧斯福的兒子J.P.在七歲時診斷出脆X症,這是最常見的一種遺傳性心智障礙,在美國影響了上百萬人的生活,包括全突變患者、其家屬,以及專業醫護人員。脆X症和自閉症與唐氏症不同,它並非突如其來發生,只出現在一個人身上,而是像波濤拍岸一般,影響整個家族。當子女被診斷出脆X症時,作母親的面對教人心碎的事實,那就是她是準突變的帶原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把突變 的基因傳遞給了子女。本書作者鄧斯福把J.P.患病的消息告訴她的手足之後,她的三個妹妹很快就發現她們同樣也帶有準突變,而有些人已經有了子女──因此J.P.的三個表弟妹同樣也受脆X症的影響,在認知和社交上出現問題。鄧斯福以強有力的語句寫道,這樣的家族必須「重新檢視它的過去,並且評估它的未來。」
本書是第一本描寫與脆X症共同生活的個人回憶錄,同時也反省了人類在基因時代自我認同的脆弱。鄧斯福回想自己得知她的基因「有缺陷」時所感受到的心理創傷。鄧斯福天生具有學者稟性,而且也接受這方面的訓練。她運用詩與科學來反省她與J.P.的生活,瞭解他以比喻為溝通的方式。書中有許多充滿趣味而感人的小故事展現了J.P.靈巧的語言能力,以及他可愛的魯莽行為。本書娓娓道出一位滿懷悲憫之心的學者對文學、遺傳,和身為人母的領悟,並訴說了一個以「作我自己而自豪」男孩的故事。
作者簡介
克萊兒.鄧斯福(Clare Dunsford)
生長於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市,波士頓學院人文與科學學院副院長,經常供稿給《波士頓學院雜誌》(Boston College Magazine)。鄧斯福曾任波士頓學院及哈佛大學英文兼任講師,獲2008年基因聯盟年會提倡人文獎(2008 Art of Advocacy Award of Genetic Alliance Annual Conference),現與兒子J. P. 曼尼恩住在波士頓地區。
譯者簡介
莊靖
台大外文畢,印地安納大學英美文學碩士,現專事翻譯。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