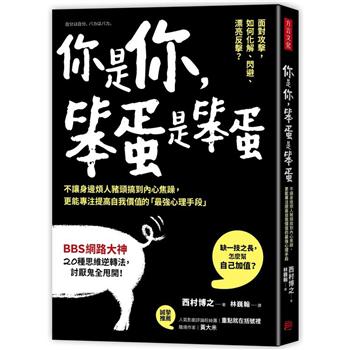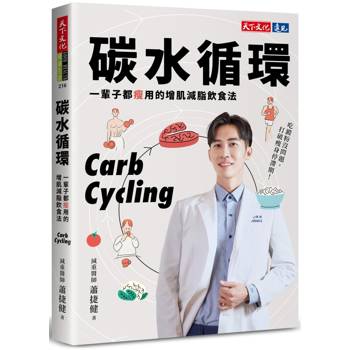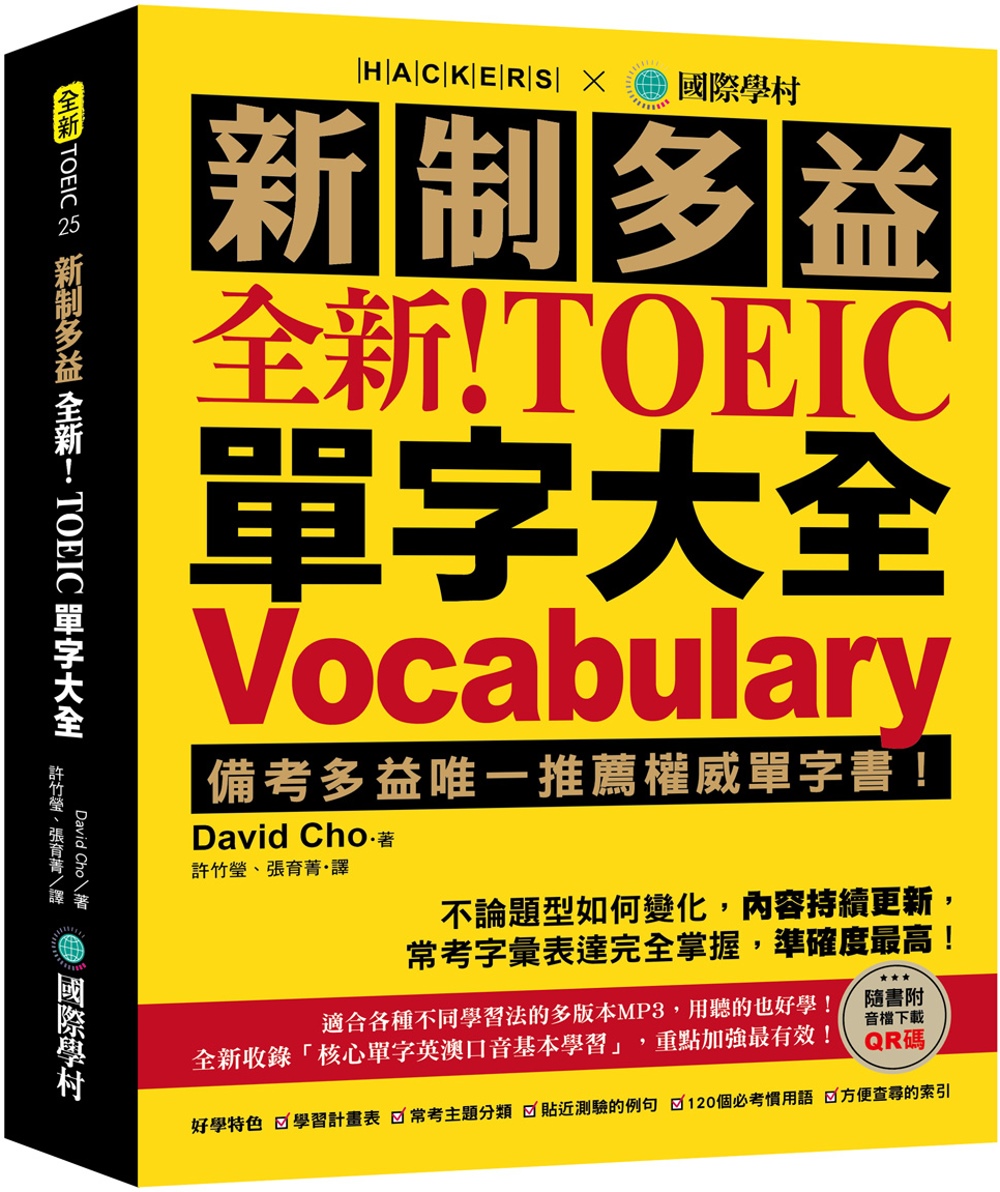「花神之路我走了四年,那是條自由之路。」──存在主義大師沙特
「啊!花神咖啡館--我在巴黎時,它就是我的家。」──奧斯卡終身成就獎得主洛琳.白考兒
「花神,就是咖啡館,最道地的咖啡館!」──法國影壇傳奇天后凱薩琳.丹妮芙
在這裡,鄰桌的客人可能是──
奧斯卡影帝勞勃.狄尼洛、世紀大師畢卡索、國際名導波蘭斯基、好萊塢巨星強尼.戴普、《異鄉人》作者卡繆、《第二性》作者西蒙波娃、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美國電影教父柯波拉、YSL創辦人聖羅蘭、香奈兒總監卡爾.拉格斐、當代建築大師柯比意、《小王子》作者聖修伯里、文學家羅蘭.巴特、奧斯卡獎&坎城影展&凱撒獎三冠影后西蒙.仙諾……
靜靜站在巴黎一角,細數著流淌於歲月中的美麗與哀愁──
再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像花神這樣人文薈萃,又如此單純美好。
畢卡索曾把這裡的牆塗成藍色、沙特被戲稱為這裡的「廣告代理商」、周恩來成為元首後仍寄上香菸給這裡的侍者、勞勃.狄尼洛愛上這裡的三明治、這裡是巴黎第六區,聖哲曼大道上,聖勃諾街角,哲學家狄德羅雕像前──花神咖啡館。
作者簡介
克里斯多弗.布巴(Christophe Boubal)
1960年生於巴黎。孩提及青少年時期都泡在花神咖啡館,咖啡館由其外祖父保羅.布巴(Paul Boubal)經營了45年,做得有聲有色。熱愛寫作和日本文化,後成為作家、詩人,另著有小說《廣島陰影》。
譯者簡介
葛諾珀
台北人。文化大學法文系畢業,法國格勒諾勃市(Grenoble)斯湯達爾(Stendhal)第三大學法語教學系(FLE)肄業。目前從事出版工作。譯有:繪本《城市花園》、《小小戀人》、《麗莎與卡斯柏》系列等;歐漫《藍色筆記》、《追憶似水年華II──在少女倩影下》(前篇)、《追憶似水年華III──在少女倩影下》(後篇);少年小說《吸墨鬼》系列。
陳太乙
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畢業,法國Tours大學法國現代文學碩士,法國Grenoble三大法語外語教學碩士暨語言學博士候選人。曾任中學及大學法文講師。旅居歐洲多年後終於返台,仍一如以往地,品味生活,歡喜閱讀,快樂翻譯。譯作:《秘密時光》、《貓的智慧》、《睡蓮方程式》、《幸福書》、《馬諦斯》、《消失的小王子》、《偷臉》、《反骨女律師》、《法國女小百科》、《王者,席丹》及《歐赫貝奇幻地誌學》系列等。


 共
共  布巴是西非國家幾內亞比索的城市,也是基納拉區的首府,面積744平方公里,海拔高度3米,1982年當局透過瑞典援助興建膠合板工廠,並安裝產生足夠供應電力給整個小鎮的蒸汽機,2008年人口6,815。
布巴是西非國家幾內亞比索的城市,也是基納拉區的首府,面積744平方公里,海拔高度3米,1982年當局透過瑞典援助興建膠合板工廠,並安裝產生足夠供應電力給整個小鎮的蒸汽機,2008年人口6,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