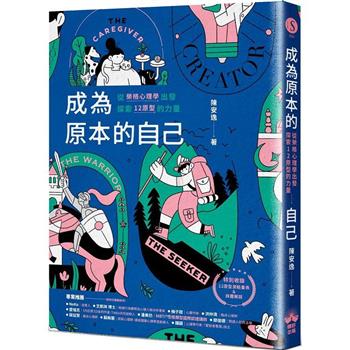前言
「窮人享受以前富人負擔不起的東西,以往的奢侈品變成生活必需品,勞動者比前幾世代的農民享有更多的舒適設備,農人比以前的地主擁有更多的奢侈品,穿著更體面,住得更愜意。地主擁有更珍貴稀有的書籍和圖畫,享用比歷代帝王更有藝術感的傢俱。」──安德魯.卡內基(AndrewCarnegie)
布蘭科.米蘭諾維克(BrankoMilanovic)是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一九八○年代在祖國南斯拉夫攻讀博士學位時,開始對貧富差距的研究感興趣,那時他發現那是當地的「敏感」議題,亦即執政者不希望學者太深入研究的議題。其實那也不令人意外,畢竟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就是想要塑造無階級的社會。
但是當米蘭諾維克搬到美國華府特區後,他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美國人很樂於為超級富豪喝采,偶爾會擔心一下窮人的境遇,但是把兩者合起來,談到貧富懸殊的現象時,大家又有所忌諱,不願多談。
「華府有個知名智囊團的負責人告訴我,那個智囊團的董事會不太可能撥款贊助標題出現『所得不均』或『貧富不均』等字眼的研究計畫。」米蘭諾維克留著大鬍子,前額髮際微禿,略顯福態,他在最近出版的著作裡提到:「他們會資助濟困扶貧的研究,但是說到貧富不均的研究,那完全是另一碼事了。」
「為什麼?」他問道,「因為關切貧困給人一種溫馨良善的印象,那表示我準備出些錢幫助他們。慈善是好事,即使只是小額捐款,也可以讓人的自尊大為提升,又能贏得大善人的美名。但是貧富不均就不同了,每次提起這個話題,就會牽涉到個人收入是否合理或合法的問題。」
重點不在於超級富豪不願展現其財富,畢竟遊艇、高級訂製服、豪宅、高調的慈善活動不就是為了炫富嗎?但是當討論從喝采轉向分析時,超級富豪就緊張了。某位華爾街的民主黨員身兼華府及數個美國大型金融機構的重要職位,他告訴我,美國總統歐巴馬就是因為碰了「富人」議題,才會疏離工商界。那位銀行家說,最好就是完全不談貧富不均,但是萬一總統免不了要挑富豪出來講,他應該稱他們是「經濟寬裕者」。直接稱他們是「富人」,聽起來像在搞階級分裂,有錢人不希望被這樣突顯出來。柯林頓在二○一一年的著作《重回工作崗位》(BacktoWork)裡也提到類似的論點,他批評歐巴馬談論富人的方式:「我不會像他那樣攻擊他們的成就。」他覺得在讓富人接受更高的稅率方面,他做得比較成功,因為他的方式比較婉轉。
波士頓的心理學家羅伯.肯尼(RobertKenny)專門為超級富豪提供諮詢,他也認同那說法。他受訪時表示:「『有錢』(rich)一詞常語帶貶義,跟『犯賤』(bitch)押同韻。我遇過一些人說:『我是某某某,我有錢。』然後就哭了。」
不只超級富豪不愛談貧富懸殊的議題,對許多普通人來說,那也可能是個令人不安的話題,因為即使在最熱切支持資本主義者的眼中,全球資本主義也不該是那樣運作的。
在數十年前,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工業化革命以前,貧富差距很小,因為整體財富和生產力相當小,社會頂層能搜刮的好處不多。工業化革命期間,實業家和產業勞工把農民遠遠拋在腦後(想想現在的中國),貧富差距因此大幅擴大。最後,在全面工業化或後工業化的社會裡,當教育日益普及,國家強化其重新分配的角色後,貧富差距又再次縮小。
白俄羅斯籍的美國移民西蒙.顧志耐(SimonKuznets)率先提出這種經濟發展與貧富差距的關係,他以經濟學中出名的顧志耐曲線(Kuznetscurve)說明這個理論:隨著經濟日益複雜及生產力的提升,社會呈倒U曲線發展,從貧富差距小逐漸變大,之後又縮小。
工業化革命初期,亞歷希斯.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在不知顧志耐的資料及統計分析下,也提出類似的預測:「仔細檢視社會形成以來的世界發展,很容易看出平等只出現在文明的歷史極點。野人很平等,因為他們一樣勢弱無知。高度文明的社會也很平等,因為他們都能隨心所欲地運用類似的方法獲得舒適與幸福。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則是條件、財富、知識的不平等--少數人掌權,其他人貧窮、無知、勢弱。」
如果你相信資本主義(目前幾乎全世界都信了),顧志耐曲線是美好的理論。經濟進步雖然殘酷無情,過程顛簸,導致不少人敗陣而退,但是一旦達到托克維爾所謂的「高度文明」,我們都會一起受惠。在一九七○年代末期以前,美國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典範,也是顧志耐曲線的具體化身。經濟學家把戰後的大幅擴張稱為大壓縮(GreatCompression),這時貧富差距縮小,多數美國人開始以中產階級自居,套用哈佛經濟學家賴瑞.凱茲(LarryKatz)的說法,這是「美國人聚合」的時代。那似乎是工業資本主義的自然形態,連雷根革命(ReaganRevolution)都趁著這個典範的勢頭而起,畢竟下滲式經濟(trickle-downeconomics)強調的是效益涓滴而下,雨露均霑。
但是一九七○年代末期,情況開始變了。中產階級的收入停滯不前,社會頂層的收入開始突飛猛進,把眾人遠拋於後。這種轉變在美國最為明顯,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紀,貧富懸殊惡化已成了全球普遍的現象,在多數已開發的西方國家及新興市場都可以明顯見得。
美國從「大壓縮」轉變成「1%vs.99%」的對立是最近幾十年的事,所以我們直覺上理解的資本主義運作,還跟不上現實的狀況。事實上,貧富差距急速惡化與我們的預期大相逕庭,所以多數人並未意識到這種事正在發生。
這就是杜克大學的行為經濟學家丹.艾瑞利(DanAriely)與哈佛商學院的邁克‧諾頓(MichaelNorton)在二○一一年的實驗中發現的現象。艾瑞利讓大家看到美國的財富分佈,金字塔頂端的20%囊括了全民財富的84%;相較之下,瑞典頂層的20%只擁有36%的總財富。9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比較喜歡瑞典現在的財富分配狀態,於是艾瑞利請受訪者提出他們理想中的美國財富分配狀況。受訪者表示,他們希望頂層的20%只擁有32%的總財富,比瑞典的實際狀況更公平。說到財富不均的議題,美國人比較想生活在瑞典,或一九五○年代末期的美國,而不是現在的美國,他們最喜歡顧志耐式的平等主義。
但是,即使實際資料與我們直覺之間有所落差,這並非忽略現況的好理由。想瞭解美國(與世界各地)資本主義的改變,你必須看社會最頂層正發生什麼事。那樣的聚焦不是階級鬥爭,而是算數問題。
曾任美國財政部長的哈佛經濟學家賴瑞.桑默斯(LarrySummers)幾乎稱不上是激進派,但他也指出過去十年美國的經濟成長極其不均,以至於「從經濟大蕭條以來,中產階級第一次覺得,把焦點放在財富重分配上,比放在成長上更有意義。」
財富大舉傾注到社會頂層的現象如此明顯,如果不考慮財富傾斜的狀況,根本無法通盤瞭解整體經濟的成長。就像全校的考試成績進步大多是因為少數資優生拉高平均一樣,社會頂層的財富暴漲也掩蓋了中下階級財富停滯的事實。以美國二○○九到二○一○年的經濟復甦為例,那段期間的整體所得成長是2.3%,那漲幅的確不怎麼樣,但是相較於當時社會普遍低迷的現象,那漲勢比你臆測的強勁多了。
不過,經濟學家艾曼紐.賽斯(EmmanuelSaez)更進一步細看資料後,發現一般的美國人的確有理由懷疑經濟復甦了,因為對99%的美國人來說,收入僅增加0.2%,但是對金字塔頂端的1%來說,收入大增了11.6%,那肯定是復甦了--至少對頂端1%來說是如此。
在新興市場蓬勃發展的背後,也有類似的故事。印度人民黨(BharatiyaJanataParty)為了蟬聯執政,大唱「閃亮印度」(IndiaShining)的競選口號,卻赫然發現城市的中產階級亮了,但上億農民仍身陷勉強餬口的貧窮線下。同樣的,中國沿海精英的蓬勃發展,跟半數在窮鄉僻壤生活的人民相比有如天壤之別。
所以,本書的目的是想帶大家一窺金字塔的最頂端,從而瞭解世界經濟的改變:他們是誰,財富來自何方,他們如何思考,他們跟其他人之間的關係。這裡不是要歌頌富人名流的生活型態,也不是要改寫十九世紀俄羅斯社會主義之父亞歷山大.赫爾岑(AlexanderHerzen)的知名小說《該怪誰?》(WhoIstoBlame?)。
這本書一開始就主張我們需要資本家,因為我們需要資本主義--它就像民主一樣,是我們目前為止想到最好的系統。但這本書也主張,結果也很重要。超級富豪把其他人遠遠甩在後頭,是如今資本主義運作的一大結果,也是影響未來的新事實。
其他有關頂層1%的討論,通常是把焦點放在政治或經濟上,那樣的選擇會牽涉到意識型態。如果你支持財閥,你會比較偏好經濟論點,因為那論點讓他們的崛起看似無可避免,或至少在市場經濟下是必然的結果。批評財閥的人通常會偏好政治論點,因為那顯示1%主宰社會是華府的政治權貴一手促成的,非關經濟。
本書則是兼顧經濟與政治面,政治決策先促成超級新貴的誕生,隨著他們經濟實力的成長,政治影響力跟著與日俱增。金錢、政治、思維之間的相互強化是超級新貴崛起的原因,也是後果。但是經濟力量也很重要,全球化和科技革命--以及這兩者創造的全球經濟成長--是促成全球新貴崛起的原動力。就連競租(rent-seeking)的財閥--那些靠政府的優惠決策致富的人--也是拜全球經濟大餅擴張所賜,變得更加富裕。
美國目前仍是全球經濟的主宰,也主導整個超級富豪圈。但本書也試圖把美國富豪放在全球背景下分析,金字塔頂端1%的崛起是全球普遍的現象,在全球化的世界經濟中,超級富豪不管是生活方式及獲利模式,都是最國際化的一群人。
十九世紀的美國經濟學家兼政治家亨利.喬治(HenryGeorge)是自由貿易的支持者,他極力主張自由企業體制,甚至反對所得稅。對他來說,那年代工業鉅子的崛起有如「人面獅身像」,他寫道:「貧困與進步的關連是當代的不解之謎……只要現代進步帶來的財富全歸富豪所有,促進豪奢,擴大貧富差距,那進步就不是真實的,是無法持久的。」
一個半世紀後,這種人面獅身像又回來了。本書帶大家深入資本家的堂奧,窺探這些人的底細,破解這個不解之謎。



 共
共  2013/09/18
2013/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