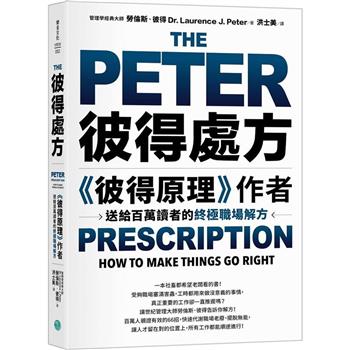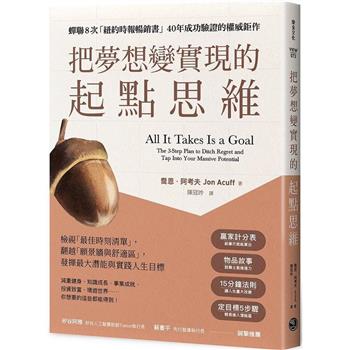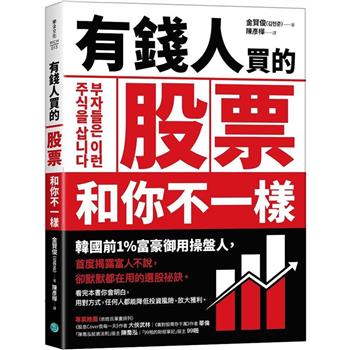你無法活著走出去!
也許,善與惡的界線向來模糊,
但是—
活人與死者之間的界線,從未如此薄弱……
波士頓WBZ電台最新消息報導:
「波士頓郊區貝爾漢的一名女子在住家中遭到殺害,警方初步認為這是一起入侵民宅的案件。女子當場死亡,死前疑似被嚴刑拷打,她的兒子獲救,被送往醫院。貝爾漢警方不願意透露受害者姓名,但是據接近調查人員的消息來源指出,這個案子『恐怖又令人髮指,是我見過最可怕的案件。』」
波士頓警局機密檔案:
1.兇案現場凌亂,兇嫌疑似翻找特定物件,行兇者超過兩人以上。
2.被害女子艾美,被斷指割喉。
3.兇嫌搜索以及行兇的過程似乎被不知名的第三者中斷,艾美12歲的兒子約翰目前保護就醫中。
4.兇案附近,有疑似FBI探員多名,持重槍械出沒。
5.現場發現一組指紋,經比對屬於已經死了二十年的FBI探員。
6.進一步調查顯示,還有更多FBI探員涉案。
她,黛比.麥考梅,波士頓警局刑事鑑識員,特警隊隊員
倖存的小男孩約翰,甚麼都不肯說,但他指名只見綽號「大紅」的湯馬斯.麥考梅巡警,這名警察正是黛比的父親,問題是,他早已死了二十年。
黛比終於突破小男孩心防,他告訴她,自己不叫約翰,而是尚恩,
就在他決定要告訴黛比,母親與他被追殺的駭人秘密時,竟然舉槍自盡……
黛比接著發現,尚恩的母親慘死的前一天,去見了殺害黛比父親的兇手。
現在,這個殺父兇手指名要見她。
到底,黛比追蹤的兇手是誰?而她奉命只能直接向警察局長報告……
她,潔米,曾經是查爾斯小鎮的警察,如今卻是兇殺案的倖存者
五年前,她失去了丈夫,失去了語言能力,唯一僅存的是她滿身的傷痕與復仇的意志。
她步步追兇,但是被她格斃的兇手卻都聲稱自己是聯邦探員。
更糟糕的是,來救援的警察始終找不到她那兩個躲藏起來的孩子。
因為還有兇手漏網……
他,殘酷的愛爾蘭黑幫老大,封閉小鎮的主宰者
但是無論他曾經如何呼風喚雨,也已經死了二十年。
為什麼二十年後,與他有關的名字又一一浮現,無論死人或是活人……
它,查爾斯鎮,波士頓近郊,總有人消失,或是不再回來,一個被法制遺忘的封閉小鎮
波士頓最小也最古老的社區,擁有全州刑事案件最高未偵破率。
鎮民始終奉行嚴格的緘默準則,一種部落式的價值。
因為:你的秘密與罪愆都屬於這個小鎮,小鎮自己會處理。
住在這裡,你要有些面對現實生活的智慧,或是小聰明。
它,幽暗小鎮裡的死亡房間,沒有人能活著走出去!
作者簡介
克里斯.穆尼(Chris Mooney)
穆尼著力描寫善惡之間的灰色地帶,曾贏得「愛倫坡獎」和「巴瑞獎」的雙重入圍殊榮。
並獲當代英美驚悚小說名家的一致讚賞,蘿拉.李普曼《貝塞尼家的姊妹》、約翰.康納利《失物之書》、麥可.康納利《林肯律師》、哈蘭.科本《第四十三個祕密》、丹尼斯.勒翰《隔離島》、泰絲.格里森《貝納德的墮落》、丹尼斯.勒翰《神秘河流》、李查德、喬治.沛倫卡諾斯、馬克.畢林漢、凱琳.史勞特等人均曾撰文推薦。
作品有《想念莎拉》、《無盡的世界》、《失蹤迷宮》、《神秘友人》等。作品已被翻譯成十六種語言。
譯者簡介
劉泗翰
資深翻譯,悠遊於兩種文字與文化之間近二十年,譯作有《四的法則》,《卡瓦利與克雷的神奇冒險》等二十餘本。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