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時候常想設法殺死我爹地。我東想一個辦法,西想一個辦法,一直想到辦法簡單容易為止。
我最喜歡的一個辦法是在他的床上放一隻毒蜘蛛。蜘蛛把他咬死;於是我顫慄著發現他死了,全身腫脹。當然我會打電話叫救護車,叫他們快來,說我爹地不好了。他們到我家時我看上去很震驚而且不知所措,眼看著兩個年輕黑人把他抬到有輪子的帆布床上,我站在門邊,好像全身發抖。
可是我沒有殺死我爹地。在郡政府的人把我送走後隔年,他酗酒而死。我聽說他們如何發現他關在房子裡面死了及其他種種。後來我便知道他已入土,房子出租給一個四口之家。
我只不過是偶爾希望他不得好死而已。而我可以說我現在過得比他活著時好得多。
我現在住在一幢整潔的磚房子裡面,大半時間隨心所欲不受干擾。我身上一有臭味便去洗個澡,然後大家都說我看起來好可愛。
這兒有很多東西可吃,一缺了什麼便到店裡面去買。今天我的早點是一個雞蛋三明治,兩面塗著沙拉醬。我也許再做一個當午飯。
兩年以前我有的不多。不是說我現在生活在多奢侈的環境中,但每天早晨校車來接我去上學,使我感到驕傲。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站在院子前面等車來接,地上是綠草,樹籬修剪成方形。
想到我的家人不是死了便是瘋了,就發覺我過得還真不錯。
每個星期二,會有一個男人到學校來。他把我從社會課課堂上叫出來,到另一個房間懇談。
上個星期他在桌子上放了一些扁平蝙蝠的圖形叫我評論。我大半只看到這些扁平的蝙蝠,但不久也看到許多一個人可以掉進去的大黑洞。大而黑的深洞深到透過桌子和地板。於是他把眼鏡拿掉,把臉湊近我的臉,說我在害怕。
我告訴他說我以前害怕,但現在不怕了。我或許會有一點緊張,但我卻不害怕了。
哦!不過我是記得我以前害怕的時候。那個時候什麼都大錯特錯,好像有人敲垮了什麼,使我的家庭搖搖欲墜。好像雲霄飛車出了毛病,駕車的人跑了,剩下我們旋轉不停、搖搖晃晃,接著飛出軌道一樣。我的父母都因這瘋狂的旋轉而筋疲力竭,而生病,而死。你說這是什麼死法!她病了,他酗酒,他們最後向這瘋狂的旋轉屈服,讓風把他們捲走。
甚至我媽的皮膚也好像疲憊到不想再包住她脆弱的軀體了。她靠著冰箱站在那裡,看我爹地繞著桌子轉圈,咒罵這個那個,說他們對不起他。她看上去面帶哀傷,好像這些都是她的不是。
她無法不生病,但當年並沒有誰叫她嫁給他。她在我這麼大小的時候,就像人家說愛得狂熱那樣愛上我爹地,自那時起心臟就沒有好過。
她有時由醫院回家來。要我是她就不回來,就在醫院躺在有冷氣的病房床上,有人來拍拍你的頭,送給你水果。
可是她卻回來,而他立刻就對著她發洩怒氣。如此這般持續下去。他坐在懶人躺椅上好像這一天他是霸王。他會叫她給他拿這個拿那個。
她一進門他便立刻問她晚飯是什麼?他想知道她預備做什麼。他不想知道我自己打算做什麼晚飯嗎?她正對著他的臉看,不看他的眼睛或嘴,但看他的整個臉,以及滿臉的醜態。他又問晚飯,問院子裡怎麼會長了些野草?像一個卑鄙的嬰兒,不像一個成熟的男人。
我把她的小提箱提進臥房。我一面走一面聽他說話,而她一句也沒回話。她站在他這位大老爺和電視機中間,看著他咒罵她。
他像是一個上了發條的玩具。雖然他是我爹地,但他實在太惹人厭使我不想回嘴。而她又太軟弱太痛苦,沒有氣力叫他住嘴。她只是站在那兒任他作惡。
他叫她去廚房給他做點東西吃,說她不在家的時候他得天天自己做飯。
一派謊言!自己做飯,哈!如果我沒有給我們兩個人做飯,我們便得進城外帶炸雞。我自己也想吃點合適的東西,但我什麼也不準備說。
如果有人問我該怎麼辦,我便會說我們吃乾酪夾脆餅乾吧。有的人藉口臥床以便丈夫不整天找她麻煩。可是我媽不去臥房,她轉身就進了廚房。我除了去替她搆在高處她搆不到的東西以外,還有什麼辦法?我擺著晚飯要用的餐具,並想像在我爹地的叉子上吐口水。
在這裡,沒有誰大聲叫誰做這做那。
我的新媽把食物做好,我們輪流上菜。然後我們享受這頓飯。吐司麵包或小鬆餅,想塗什麼就塗什麼。雞蛋有各種做法。玉蜀黍是當天摘下來的。我不把肘放在桌上,並像一個有教養的淑女一樣用餐巾擦嘴。沒有人喝叱、放屁或餵桌子下面的狗。大家吃完以後,我的新媽把盤碟放進洗碗機,關上機門,扭開開關,一會兒盤碟都洗乾淨了。
我媽一字不提疲倦和疼痛。她問是誰把房子收拾得這麼乾淨?我爹地說是他。我不知道他自以為騙得了誰。我知道他是說謊,我媽也知道。她問這個問題只是想找句話說。
媽把飯菜擺在桌子上。他問我在盯著看什麼。我盯什麼?盯著你爬在你的盤子上,好像我們要搶走你的盤子一樣。你這個貪婪自私的老傢伙!不過我沒有說出來。
他問,你為什麼不吃?
我說我現在不想吃東西。
你最好吃點吧,看你媽的樣子,這可能是她「最後的晚餐」了。
他自以為滑稽,於是嘲笑起他自己來。
我一直在看爹地和媽,想知道他為什麼這麼恨她。他不看我時,我就對他瞪一眼。我媽看起來想爬到桌子下面哭一場。
我們把他丟在桌子旁,逕自去睡覺。她全身疼痛,到胸部都在痛,到頸部都有瘀傷。我實在想轉頭不看。
我們把她的衣服由頭上脫了下來,給她穿上寬大的睡袍。我扶她睡下,然後躺在她旁邊。她只是把頭埋進枕頭裡。
我會在這兒陪你。陪你小睡片刻。
現在在我新媽的家裡,傍晚我躺在床上,看著外面下的雨。在這兒沒有人催我做任何事。
我有一袋糖果,一顆一顆吃以便可以吃久一點。我要做的只剩下吃晚飯和洗澡了。
環顧我的房間,它實在很不錯。
等我存夠錢時,我計劃買一點掛在玻璃窗上的彩色玻璃飾品。我躺在床上想像那會是什麼樣子。我已經有粉紅方格子的窗帘,窗帘的邊緣上懸垂有小絨球。是我的新媽給我縫的。她也縫了配色的枕套供我每天早上塞枕頭進去。
所有的東西都很搭配,什麼都乾淨整齊。
我躺在這兒吃過麥芽奶球以後,便會理一理被子,梳洗一番。也許我還會跟別人玩一玩。可是我也許就躺在這兒直到炸雞的香味說明可以吃了。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聽見他由後門出去。她很安靜,好像沒有醒來。他開著卡車走了,好像有什麼事要辦。但是你知道、我也知道他是去給自己買酒喝。然後他像聖誕老人一樣把酒帶回家來。他把袋子往椅子旁邊一放,就舒舒服服的坐下來。大叫大喊,要我把電視打開。我真想咬指甲、吐食物。
他的叫喊把媽嚇得跳起來。如果她本來是睡著的,現在也醒了。每一次他罵這個那個該死,她便咬咬牙。他愈喝得多便愈不可理解。
到了電視播賽狗的時候,他已平躺在浴室地板上爬不起來了。我知道我得去戳醒他。每個星期六都是如此。這個星期尤其不該讓她看見這個貪婪自私的傢伙對著馬桶嘔吐。
我站起來走進浴室叫他出來,說有人要上廁所。他可以到卡車上去睡。
他只是咕噥,想抓我的腳踝,而沒有抓住。
站起來,我又跟他說一次。在這個時候我得表現得堅定。如果我縱容他,他便會躺在那兒一直到全身腐爛。因而我用腳去踢他。我絕不用手碰他。看到他撐在洗臉台上,使我想吐起來。他歪歪斜斜的走過客廳,我猜他是在想辦法走出門去了。我沒有聽見他由台階上掉下去。
她是從那兒冒出來的?她站在門那裡把這些看得一清二楚。
我對媽說:回床上去!
媽好辦,她走回臥房,一點麻煩也沒有。只不過是有一點僵硬不容易移動而已。我讓她躺回床去,告訴她說爹地今晚不回來了。她開始啜泣,我說這沒有什麼好哭的。但她會哭到筋疲力竭。
我應該把他鎖在門外。
他是一個大人,應該帶食物回家給她慢慢吃、帶書回家給她看。可是沒有,他今夜只顧他自己。就好像她沒有生病或不是他的親人一樣。
一場暴風雨來了。我要躺在這兒陪媽,直到她胸口起伏規律為止。睡得沉沉的,呼吸勻勻的,遠離那個在卡車裡面的男人!
我可以嗅到暴風雨,空中大雨來了。
他將一覺睡過這場雷雨。我氣死了,希望閃電給他報復性的一擊。但是我不能控制雲或雷。
上帝要怎麼樣是祂的事,別人管不著的。
2
天亮的時候,我聽見我爹地進房子來了。他沒有悄悄的。如果他有一匹馬,他一定騎馬直上台階。他已忘記昨天晚上的事,並且笨到以為我們也忘了。
我媽已自己下床。我一定是睡沉了沒有聽見她。我昨夜沒換睡衣就睡了,所以今天早上省下了點麻煩。
他現在和她一個人在廚房。我知道他不會用手打她。他也許會向她丟一個杯子或一支叉子,但他不會去碰她以免留下痕跡。
我設法不讓她單獨和他在一起。即使他們同床而眠也不例外。我嬰兒時所睡的小床仍在他們房間,因而我在晚上聽到他們的聲音時,便大發脾氣非睡到我的小床上不可。有我在跟前他不敢亂動。
我想去看看,但門是關著的。我得去廚房拿件東西,於是我進去。
她坐在桌子的一端,他坐在另一端翻她的皮包。她的一些心臟藥丸在桌子上滾來滾去,藥瓶在她大腿上。
我對她說:把瓶子給我,我好把藥丸放回去,這藥是花錢買的。
他看著她,對我說她只剩下這幾顆藥了,她幾乎把那該死的整整一瓶藥丸吃下去了。
媽媽,吐出來!我把手伸進你喉嚨去你便可以吐出來。她看著我,我知道她不會吐。她不會動。
那麼我只好去商店打電話。
但是我爹地說如果我離開家一步,他就會殺死我。我一直知道他是個惡人,只是沒有證據。
他會用一把刀把我媽和我一併殺死。他看著我們兩個人,一面搓她的皮包,很有耐性,好像他一向都坐在那兒等人死一樣。他叫我把媽送回床上去。
他說,天殺的!她不過只需要睡個覺。把她送回床去,看看她會不會把藥性睡走。他向我保證藥丸不會傷害她。
我們都再休息一會兒。天還很早,我們需要多休息一會兒。
我向來喜歡好好吃一頓晚飯,然後刷牙上床。如果我不睡覺,我總會找點事做。
最近我常躺在床上看古書。我告訴圖書館的老師說我想看任何有份量的讀物,因而她給我開了一張單子。這是兩年以前的事了,現在我已讀到布朗蒂姊妹的作品。我不看漫畫或報紙。我由電視上知道我需要的新聞。
我簡直是受不了我們在學校看的那些故事書。辛蒂或勒歐帶著一隻狗或貓,總是出發去冒險。他們或是遇見土匪或是跳上一輛已開動的貨車,但警察或司機總會把他們送回家,而他們仍是好孩子。
我自己則喜歡老故事。我在這閱讀計劃一開始時,喜歡上一個穿紅色靴子、大聲歡笑的中世紀淑女。她與一群人外出旅行,不停交換故事,彼此讚賞。
我現在看的這本書對我而言深奧了一點,但是它卻在書單上。書中男男女女在一棟黑暗的大房子裡鬼鬼祟祟,專管別人的閒事。圖書館的老師說作者及其姊妹所以寫書,是因為在她們那個時代,她們不能外出工作。我想她們一定滿有錢,不需要工作。
我可以躺在這兒通宵看書,不看書便睡不著。腦子如果不善用便胡思亂想。我把我的腦子騙離那樣的狀態,一直看書看到它入睡。我認為最好一直做點事到入睡為止。
我一向喜歡躺在這兒,她把手抬起來,我把頭放到她旁邊,身子跟著爬過去。可是現在可能只有我的心在跳了。
她的心已停止跳動。
他這個天殺的,下地獄下油鍋的!
現在開始天旋地轉,我該怎麼辦?許多人會來我家,想知道我媽為什麼會死,而我不能告訴他們說為什麼。他們一時還不會來。她現在是我的,睡著了,但不呼吸。我不告訴爹地,讓他坐在那裡奇怪這兒為什麼會一片安靜。在到處的人高高興興過這一天的時候,這棟房子為何一片安靜。
上帝讓這個罪人坐在他的椅子上不能動彈,害怕一個死了的甜蜜婦人。
在還沒有人來搬動妳以前妳可以在我旁邊休息。我們不說話,只是休息。
我應該告訴她:我很不喜歡那件衣服,妳不要碰我。但是我把浴室的門關上,把我姨媽關在外面。
這口紅現在是我的了嗎?我以為我塗口紅上教堂是不妥的。她會叫我塗,但有人會說話。
把它放回去把它放回去!我老了再回來塗。他們不需要這枝口紅打扮我媽嗎?有人一定曾給她另一枝,因而她把這枝留在家裡。他們一定不會給每個做生意的對象塗同一枝口紅。
我只要漱漱口坐在馬桶上看。我由門縫中什麼都看得到。自從上一個聖誕節以後我就沒有看見過的許多人都來了,坐在那裡彼此拍拍手背表示安慰。
我爹地在想能喝一大杯酒該多好。在他們來以前,他收拾起所有的啤酒罐子塞在後門廊。
一定是有人給了他那套衣服。他向來只穿灰色的工作服。我想在他的口袋上縫一小塊布,說他的名字是比爾。那樣他便會像那個埃索汽油公司的人。女士,我能為您效勞嗎?檢查您的輪胎?換換您的油?給您一刀?
從星期天早晨起,他所做的只是給人們開門,還有點點頭或搖搖頭。他的兄弟魯道夫開車帶他進城去挑棺材。我知道他到棺材店時,我的姨媽們把他攆走了。她們有品味,知道怎麼挑。
他坐在那裡兩足著地,眼睛通紅但不是因為哭泣。當有人走過來湊近他的耳朵時,他碰碰他們的肩膀。還是個霸王,不過現在安靜了。
她終於讓他閉嘴。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凱伊.吉本絲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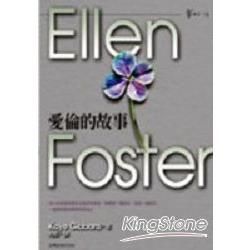 |
$ 170 ~ 180 | 愛倫的故事
作者:凱伊‧吉本絲 / 譯者:允韜 出版社: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6-02-01 語言:繁體書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愛倫的故事
11歲的女孩愛倫,生長在美國南方的一個問題家庭:她的母親長年遭受丈夫施暴,最後服藥自殺;她的父親酗酒,對她疏於照顧,甚至有暴力和性侵害的威脅。她陸續被安排居住在老師、外婆與阿姨家中,但都無法長居久留。儘管歷經種種波折,愛倫始終相信世上一定有個能讓她定下來的居所。最後她靠自己的力量找尋她想要的歸宿,她的勇氣與智慧為她帶來了從未有過的幸福生活。
本書榮獲美國藝文學會(American Academy and Institute of Arts and Letters)的蘇考夫曼獎(Sue Kaufman Prize),以及海明威基金會(Ernest Hemingway Foundation)的特別榮譽獎,是一部媲美《麥田捕手》與《頑童歷險記》的經典之作。
章節試閱
我小的時候常想設法殺死我爹地。我東想一個辦法,西想一個辦法,一直想到辦法簡單容易為止。我最喜歡的一個辦法是在他的床上放一隻毒蜘蛛。蜘蛛把他咬死;於是我顫慄著發現他死了,全身腫脹。當然我會打電話叫救護車,叫他們快來,說我爹地不好了。他們到我家時我看上去很震驚而且不知所措,眼看著兩個年輕黑人把他抬到有輪子的帆布床上,我站在門邊,好像全身發抖。可是我沒有殺死我爹地。在郡政府的人把我送走後隔年,他酗酒而死。我聽說他們如何發現他關在房子裡面死了及其他種種。後來我便知道他已入土,房子出租給一個四口之家。我只...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凱伊‧吉本絲 譯者: 允韜
- 出版社: 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6-02-01 ISBN/ISSN:957052019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60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英美文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