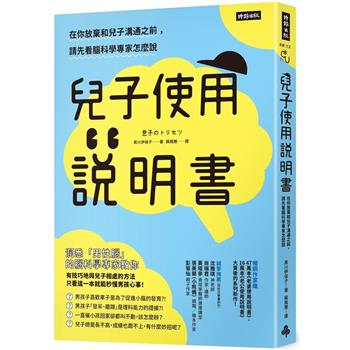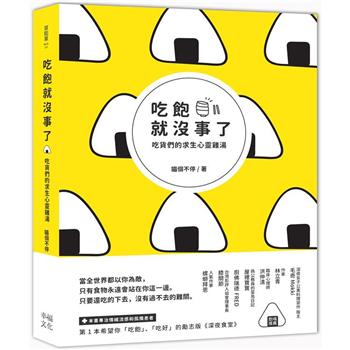得獎紀錄:
★中國時報開卷版一周好書榜★性別平等教育優良讀物100★行政院新聞局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媒體推薦:
TheNewYorkTimes(紐約時報)「作者以巨細靡遺的豐富回憶,構成了本書的素材,並邀請讀者見證由這些記憶娓娓道來的場景。」TheSanFranciscoChronicle(舊金山紀事)「本書具有相當高的可讀性,不時顯得趣味橫生。作者以絕佳的感受力,勾勒出一個幼小心靈在面臨可怖的真相時所產生的困惑。」Booklist(書目雜誌)「本書步調沈穩,並敘紛陳,不過在書中主角所必須臣服以求生存的矛盾的現實,與迷失的觀點之間,卻表現出某種戲劇化的關聯性。」HornBook(號角書目)「作者溫特女士除了刻畫出主角對於宗教的疑惑,更點出對於祖國的矛盾情感。當戰爭結束後,正如作者所說的,卡塔琳娜的心靈也將永遠停格在她所失落的世界當中,任憑貫穿整本書的回憶時光,一再反覆播放……」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