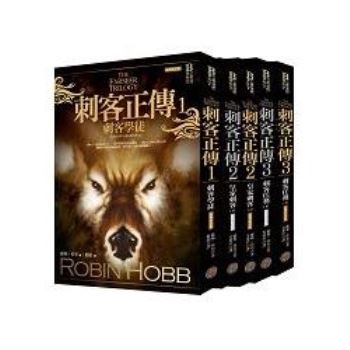我的家人都不愛我。他們的血好冷。
你有嚐過血的滋味嗎?
你有嚐過血的滋味嗎?
──史蒂芬.金的媳婦,凱莉.布雷菲,驚人暢銷作正式登場──
尖銳無比的女性心理刻劃
沉悶的小鎮,陰暗的人物,禁忌的秘密
暗黑哥德風潮再起,高潮結局令人尖叫
賓州雷契斯柏格小鎮上,兩個崩離變調的家庭,因為一名未成年少女的誘惑詭計,將悲慘撞擊:庫希馬諾家的父親酒駕撞死男孩後,因為兒子派屈克主動向警局報案而遭逮捕入獄,哥哥邁可始終無法諒解弟弟,為此兄弟失和;另外,雙親是家庭教會傳教士的艾席爾家,門風嚴厲,育有一對就讀高中、年輕貌美的女兒,妹妹花娜純真脫俗、安靜保守,相對受到冷落的姊姊蕾拉則狡猾邪惡,她過著表面得體、私下靡爛的放縱生活,在學校加入神祕團體,逐條違犯父母的誡律。當她得知在便利商店工作的派屈克,就是大義滅親的庫希馬諾家的小兒子時,蕾拉決定去勾引他,甚至折磨他。她玩火的舉動卻將所有人帶向一場失控的死亡之約。
宛如《控制》加《最後的目擊者》的暗黑青春,像電流貫穿全身般的痛快刺激,結局劇力萬鈞地送上絕妙的悲愴與救贖。在寂寞的小鎮上,兩個家庭因罪惡而逐漸接近碰撞,最後呈現出一個宛如田納西威廉斯般角色衝突強烈的典型悲劇故事。最後三十頁的大結局將遠比任何電影更衝突精采,驚悚小說迷絕對屏息驚豔。
名人推薦
「驚悚小說的高壓電。」──丹尼斯‧勒翰,《神祕河流》作者
愛倫坡獎得主丹尼斯.勒翰&驚悚天王史蒂芬.金齊聲推薦
書評
「布雷菲令人神魂顛倒,毛骨悚然又逼真的小說新作……她優美的文筆、尖銳的對話,以及栩栩如生的人物塑造,將劇情帶往可信服卻完全出人意料的結局。」--《出版人週刊》,星級書評
「作者有可以灼傷人的說故事技巧。布雷菲對筆下的底層小人物情有獨鍾,把不為人知的生活搬人檯面。」--《紐約時報》
「一場毛骨悚然的惡夢」,《娛樂週刊》
名人推薦語
「驚悚小說的高壓電。」──丹尼斯‧勒翰,《神祕河流》作者作者
「恭喜凱莉.布雷菲新作《血親》出版。這本書非常值得一看。」──史蒂芬‧金,《紐約時報》推薦書評
「【A】必讀…布雷菲以沸騰激盪的詩意語言,精確描繪了沉悶小鎮生活的樣貌,以及它的邊緣居民的無奈絕望…作者營造的張力讓人難以招架,故事的結局則令人快慰,全然地折服。」──Salon.com作者蘿拉‧米勒
「《血親》是屬於那種稀有美麗的東西,一本帶領我們進入陰暗之地的小說,不只敘事生動,更蘊藏著無比敏銳的情感強度。故事描述的是破裂的家庭和潛藏危機的過往,當情節朝向令人戰慄的結局推移,那張力令人喘不過氣來,同時又充滿震撼與感動。」──梅根‧阿博特,暢銷書《我敢》作者
「《血親》深入隱藏在憂傷、愛和憤怒底下的種種不堪,讀罷讓人震顫同時又充滿感激。一部令人膽寒的作品,也證明布雷菲是位才華洋溢的作者。」──艾瑪‧斯特勞布,《蘿拉‧萊蒙的影像人生》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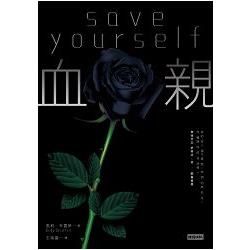
 共
共  布雷是位於比利時林堡省部的一座城市,人口14,503人。
布雷是位於比利時林堡省部的一座城市,人口14,50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