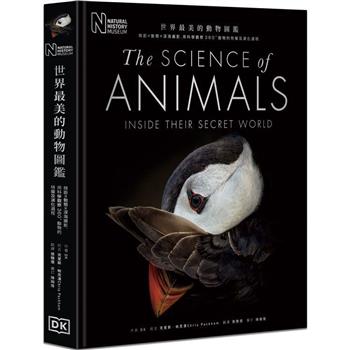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凱菈‧歐森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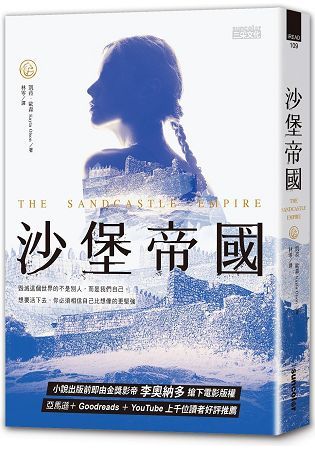 |
$ 160 ~ 342 | 沙堡帝國
作者:凱菈‧歐森 / 譯者:林零 出版社:三采文化 出版日期:2018-07-27 語言:繁體/中文  共 11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1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一座失落的島嶼,一本寫滿密碼的筆記,四個各懷祕密的女孩。
當世界只剩下海洋,你該將希望寄託在何方?
在海洋淹沒世界的那天,名為狼幫的軍閥控制了所有人的生存和自由。
伊甸試圖偷船逃離狼幫的囚禁島,但意料之外地,這趟逃亡多了三個素不相識的落難夥伴,艾莉莎、荷普和芬莉。她按照父親留下的筆記,帶著眾人航向傳說中的避難島,尋找能夠提供庇護的神廟。但伊甸沒有說的是她父親的身分,以及他留給她的龐大計畫。
她們航行了好幾天後,終於來到島上。結果才過了第一晚,芬莉就不見了。為了尋找芬莉和筆記上記載的神廟,三人往叢林深處走去,才發現這座島上不僅機關重重,更詭異的是連一隻鳥、一隻蟲、一點生命跡象也沒有……究竟是有人將芬莉擄走,還是她背叛了她們?她們會在這座島嶼中央發現什麼?科學家父親留給伊甸的這座島是庇護天堂,還是另一個恐怖牢籠?
小說的背景設定在不久的未來,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世界強國之間戰爭不斷,爭奪即將消耗殆盡的自然資源,老百姓則失去一切。唯一的希望,就寄託在女主角尋找的傳說中的綠洲上。不同於一般青少年冒險小說,書中傳達的關懷地球與環保精神,引起奧斯卡影帝李奧納多‧狄卡皮歐的注意,讓他迅速簽下本書的電影版權。而充滿懸疑的曲折劇情,有如發生在《LOST檔案》場景的女性版《移動迷宮》,想必小說與電影皆精采可期。
作者簡介
凱菈‧歐森(Kayla Olson)
從小在德州小鎮長大,喜歡看海看星空,熱愛製作音樂和拿鐵,腦袋裡有成千上萬個想法等待被寫出來。《沙堡帝國》是她的第一本小說,出版前即被派拉蒙影業和李奧納多‧狄卡皮歐的製片公司相中,即將改編成電影。
譯者簡介
林零
淡江大學英文系畢。偽台北人,浮沉出版業,熱愛小說。喜歡黑貓、慢跑,以及一人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