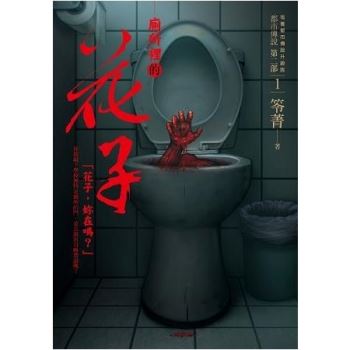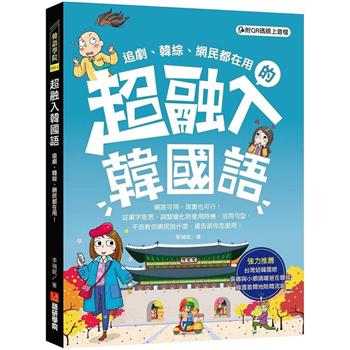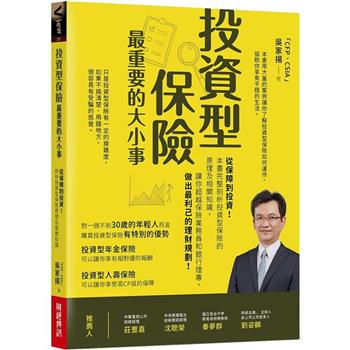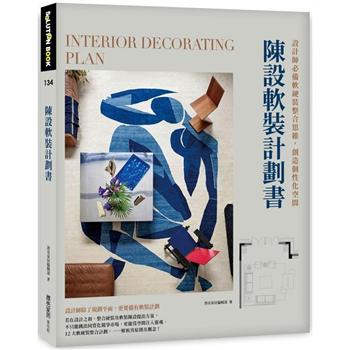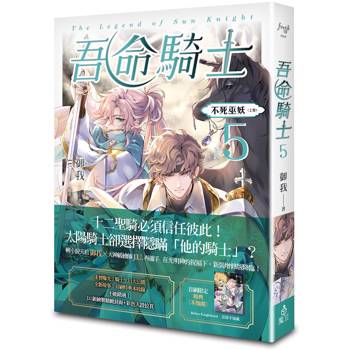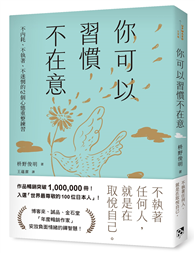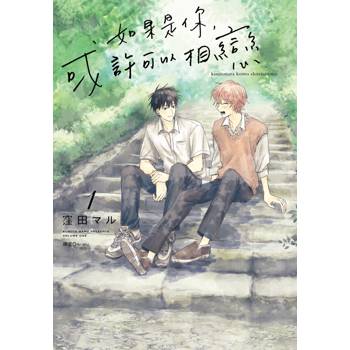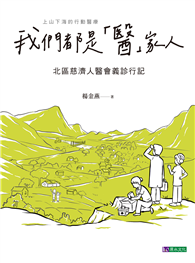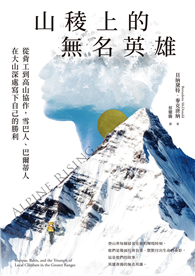撒哈拉魅力
三毛說:「你不能要求我永遠是沙漠裡那個光芒萬丈的女人……」但她的盛名的確是和撒哈拉沙漠連接在一起的。撒哈拉使三毛得到了荷西,得到了婚姻,得到了幸福。撒哈拉將三毛這個悲情放逐的女人,塑造成了沙漠俠女。由俠女與荷西的愛情神話,奇特的沙漠景觀和異域人文,三毛的善良、愛心、情趣所構成的「三毛文學」,迸發了「撒哈拉魅力」,掀起了華人文化圈的「三毛熱」。使三毛享盡了崇拜者的掌聲。
很多人喜歡三毛筆下的撒哈拉,因為那裡有艱苦條件下不朽的愛情。那時的三毛是個幸福的女人,過著快樂的日子,她一襲長裙,飛揚的長髮,眼波間流轉著靈動。在遙遠的撒哈拉,住在墳場區的蝸居,有荷西相伴,開著自己的「中國飯店」,吃著叫做「雨」的飯菜,像一個君王,陶醉在她的沙漠城堡裡。正是在《撒哈拉的故事》中,三毛開始變成一個無比美麗的女人,幸福灌注心靈的女人是美麗的,這是任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看看她筆下的撒哈拉生活吧,那種牽引著無數人嚮往的生活:在墳場區的家裡,棺材外板經過荷西靈巧的雙手,變成了傢俱;舊的汽車輪胎,三毛拾回來清洗乾淨,放在蓆子上,裡面填上一個紅布坐墊,像一個鳥巢;還有那些斜鋪著美麗檯布的飯桌、擺滿書的書架、神祕老人那裡買來的石像、角落裡怒放的天堂鳥,甚至還有風燈、羊皮鼓、羊皮睡袋、皮風箱、水煙壺、彩色大床罩、奇形怪狀的風沙聚合的石頭…… 一所普通的阿雍小鎮外的房子,一年後在三毛與荷西的手中變成了真正的藝術的宮殿,朋友們都驚歎沙漠中的房子居然能變成畫報裡似的美麗。這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幸福,而這期間的過程確是一種更大的幸福。
撒哈拉施展了它的魅力,而三毛用她的筆進行著動情動心的勾勒和描摹。
在撒哈拉的日子裡,三毛與荷西裝扮小小的蝸居;去海邊偷看沙哈拉威女人的〈春季大掃除〉;在沙漠歷險中經歷生死考驗;為了賺錢做〈素人漁夫〉;開著有聲有色的〈中國飯店〉。不過生死由命,這個幸福了六年的女人最後還是遭到了天劫,她的荷西回到了大海的懷抱,荷西說他一生有兩個至愛,一個是大海,一個三毛,所以他在三毛身邊陪伴了六年,然後回歸了大海。
她一直渴望愛人,渴望幸福的婚姻,因為撒哈拉之所以有巨大的魅力,不僅僅因為那裡的異域風情,也不僅僅因為那裡的人文景觀,更為重要的是那份盪氣迴腸的夫妻之愛。失去荷西之後,她沒有停止過尋找,但狀況卻一直是迎接追逐,又拋棄追逐,因為再也沒有一個男人可以成為她的荷西。
她說:「我希望到廚房煮菜,希望共同品嚐佳餚,然後依偎著談天,攜手散步。」這是多少個平凡的或者不凡的女人的嚮往。只是,世間有很多事情,只能經歷一次,一旦失去,就再也無法重來。「後來我總算學會了如何去愛,可惜你早已遠去消失在人海。後來終於在眼淚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錯過就不再。」劉若英的歌聲恰恰是三毛愛情的最後總結。
荷西變成了生命的永恆,所以面對再多的追求,她都要問一聲:「可以代替嗎?」
不能夠,所以,留情,然後斷情。甩給人家的「情」,人家還來不及收拾和整理,她已經揮揮手走了,連一片雲彩都不曾帶上。她迷失於那個本來屬於文學的浪漫世界,她把生活當成了文學,又把文學當成了生活。那種「無須互相遷就,無須互相尊重,兩個人就是一個人」境界,其實一直是她精心構造的夢,但她沉浸在夢裡不願意醒。更多的讀者也願意為著這個虛幻的愛情神話不斷流淚、歎息,因為現實的生活中不存在,所以通過文學構築的想像空間給予寂寞心靈一種補償。
一個人的一生,總是在成長,任何人都不例外。三毛的少女時期尤其慘澹。就像別人所評論的,《雨季不再來》的遐思、愛戀、迷惘和感傷,記述的是「一個少女成長的過程和感受」,是她「蒼弱的早期」。
直到她投進了沙漠,才迎來了生命中最重大的轉折。荷西愛情的滋潤,使得三毛瀚海似的生命長滿了綠蔭。當她再次拿起中斷了多年的筆,為讀者描繪她和荷西的婚姻、家居生活,以及她在撒哈拉的探索和發現的時候,那「筆下的人,已不再是那個悲苦、敏感、浪漫而又不負責任的三毛了。」
華岡校園裡那個做著哲學遐思之夢的三毛,蛻變成一個能夠實實在在品嚐婚姻幸福、承擔生活和生命風雨的女人;她的視野雖然還主要集中在個人的生活圈子裡,但也已經把目光投入了周圍的世界,筆下的「芳鄰」、「娃娃新娘」、「賣花女」、「啞奴」…… 都是她試圖超越一己空間的嘗試,只不過,她寫他們,結果也是自己變成了主角。
這時候的作品集《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駱駝》、《稻草人手記》、《溫柔的夜》,都不再是雨季裡的灰色基調,而是健朗的、豁達的、灑脫的吸引人的「撒哈拉魅力」。而其中最重要的作品當然主要收錄在《撒哈拉的故事》這本書中。三毛提供給讀者的是這樣平凡的愛情,是落到地上的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愛情,雞零狗碎、柴米油鹽,但自有一種憨厚的快樂存在。《撒哈拉的故事》是三毛作品中最受歡迎的一部,它寫的全是她與夫君在沙漠家中做飯、洗衣、理髮的瑣事。此時的三毛,頭髮蓬亂如鬼,臉黃如婆,好奇、多事、虛榮,只關心白菜,不想心事和未來,常常便為了一朵花、一個撿到的錢幣,而傻瓜般地高興起來。與後來那個善感、精緻到最後用一雙絲襪自殺的作家、編劇三毛相比,沒有人不懷念撒哈拉那個粗糙而茁壯的作為家庭主婦的三毛。那裡的她,知足、感恩、快樂,身體力行地展示了一種幸福最容易實現的方式。後來,荷西去世,天劫的痛苦迫使三毛走向成熟。她在痛定思痛中完成的《夢裡花落知多少》、《背影》,感念荷西的摯愛,感念父母的養育,雖然深沉而憂鬱,但「撒哈拉魅力」猶存。
一九八一年,三毛試圖突破自己的創作題材,也渴望離開了撒哈拉沙漠之後依然有新題材可寫,她做了一次中南美之行,寫下了《萬水千山走遍》。她想要嘗試著開闢另一個創作空間,以求再創一個「撒哈拉」。但終於只是走馬看花,而不是在筆下流淌的生活。離開了撒哈拉,三毛陷入臺北擁擠而冷漠的生活中,但她不能夠接受被人遺忘的幸福,她已經習慣了熱鬧,儘管有時候她並不喜歡這份熱鬧。名聲有時候牽引著她的腳步,使她不肯在盛名之下停止自己的筆,儘管還是寫,寫出來的卻不再是早先那種吸引人的文字。
再後來,她就徹底掉進了自我設計的追求和現代傳媒塑造的魅力共同構成的「陷阱」裡去了。她成了神話,她以神話引誘著讀者的腳步,讓他們為她著迷,執著地讀她的文字,因為幾乎每個女人的一生都有兩個最愛——愛情和流浪。自己沒有,便羨慕著擁有的三毛。
她想過回頭做一個普通人嗎?也許想過,也許沒有想過。反正事實上她想要不傳奇不神話卻做不到了,即使她的荷西是否真的死了,都有人做出了各種各樣的猜測,正如坊間還流傳著她不是自殺而死,而是被謀殺或者因病而死這樣種種不同的說法一樣。原來,她以傳奇色彩的生活寫成傳奇的文學,但撒哈拉時代總要過去。荷西生前死後的情話一掏再掏、幾乎枯竭以後,為了聽取讀者掌聲的召喚,維繫她的魅力,她就只能變成一個分裂的人,使自己像故事一樣生活,然後再將故事寫下來與讀者分享。然而荷西已去,大漠已遠,撒哈拉已是傷心之地。三毛無法在真空中延續「撒哈拉魅力」。所以她就轉換新的寫作空間,付諸新的尋找。
去南美,寫出的《萬水千山走遍》是失敗的;寫《鬧學記》也帶上了做作的色彩。
她甚至借助靈異世界來增添自己的神祕色彩,但終於這一切都無法使她回復到「撒哈拉魅力」時期了。
她太累了。
在她生前寫給大陸的伯父倪竹青的信中說她再也寫不下去了。她要以自己為「唯一」的素材來維持「撒哈拉魅力」,從體力上和精力上已不勝負荷,在藝術上也做不到。正如有人所評論的,三毛的後「撒哈拉」時期的作品已經失去了原先的那份真誠和感動,重複著的軼聞趣事也都是浮光掠影而已。
到她創作劇本《滾滾紅塵》的時候,她更是想著去超越自己。這是她不寫自我而寫別人的嘗試,是不取現實世界而寫歷史生活的嘗試,也是借角色來暗渡自己的嘗試,這個嘗試對三毛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但她太過留戀過去,擺脫了當初在撒哈拉創作時的思維模式,《滾滾紅塵》說是寫他人,其實還是寫自己,只是她沒有獲得自己想要的成功。她非常留戀撒哈拉時期的時光,她說:「在沙漠是一個人生,離開沙漠又是一個人生,有丈夫的時候是一個人生,現在我孀居的日子又是一個人生。對於過去我當然會懷念,因為我是一個人,我不能將我的人生用一
把刀子將它分割開來,說這是我的少年時期、青年時期、中年時期。」
但每一個人的人生都是由不同的階段組成的,有童年的天真也就有中年的滄桑,誰也不能在中年的時候總是一副童年的扮相,那樣的留戀就是病態了。所以告別了撒哈拉的三毛不該繼續苛求撒哈拉魅力的永存,只是她陷入了,哪裡懂得自渡?雖然她既想渡人,也想自渡,但她終究達不到佛祖涅槃的境界。
所以她迷失在紅塵中,最後成了一個說著不寫了,不寫了,又放不下筆的分裂人。
她的心態很複雜,真真假假,非常矛盾。幾個月不寫的話又覺得自己生活沒有交待。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劉蘭芳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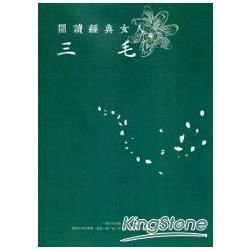 |
$ 205 ~ 234 | 閱讀經典女人:三毛
作者:劉蘭芳 出版社:思行文化 出版日期:2013-08-21 語言:繁體/中文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劉蘭芳
劉蘭芳,遼寧遼陽人,滿族,中國評書表演藝術家,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曲藝家協會主席。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閱讀經典女人:三毛
一個生性浪漫、自由不羈卻又渴望安定的女人,曾經為愛遠走他鄉,在撒哈拉荒漠中過著辛勞又甜蜜的主婦生活。她是陳平,筆名三毛,愛人荷西稱她為「撒哈拉之心」。
三毛的人生主題是愛情,愛是她唯一的嚮導。她創造了一個色彩瑰麗、童話般的浪漫世界,裡頭有她與荷西生死相許的愛情故事、不可思議的異國情調,加上那清新易讀、情感豐沛的文字風格,在一九七○、八○年代造就了兩岸三地的「三毛傳奇」、「三毛熱」。延續至今,三毛仍是傳奇愛情的代名詞,也是許多人希冀的夢想和童話。
作者簡介:
劉蘭芳,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現為北京豐台區某中學老師。
章節試閱
撒哈拉魅力
三毛說:「你不能要求我永遠是沙漠裡那個光芒萬丈的女人……」但她的盛名的確是和撒哈拉沙漠連接在一起的。撒哈拉使三毛得到了荷西,得到了婚姻,得到了幸福。撒哈拉將三毛這個悲情放逐的女人,塑造成了沙漠俠女。由俠女與荷西的愛情神話,奇特的沙漠景觀和異域人文,三毛的善良、愛心、情趣所構成的「三毛文學」,迸發了「撒哈拉魅力」,掀起了華人文化圈的「三毛熱」。使三毛享盡了崇拜者的掌聲。
很多人喜歡三毛筆下的撒哈拉,因為那裡有艱苦條件下不朽的愛情。那時的三毛是個幸福的女人,過著快樂的日子,她一襲長裙,飛...
三毛說:「你不能要求我永遠是沙漠裡那個光芒萬丈的女人……」但她的盛名的確是和撒哈拉沙漠連接在一起的。撒哈拉使三毛得到了荷西,得到了婚姻,得到了幸福。撒哈拉將三毛這個悲情放逐的女人,塑造成了沙漠俠女。由俠女與荷西的愛情神話,奇特的沙漠景觀和異域人文,三毛的善良、愛心、情趣所構成的「三毛文學」,迸發了「撒哈拉魅力」,掀起了華人文化圈的「三毛熱」。使三毛享盡了崇拜者的掌聲。
很多人喜歡三毛筆下的撒哈拉,因為那裡有艱苦條件下不朽的愛情。那時的三毛是個幸福的女人,過著快樂的日子,她一襲長裙,飛...
»看全部
目錄
緒 論 花雖逝,香永存
006不凡人生
010平凡文章
013愛情:轟轟烈烈傷己心
016婚姻:平平淡淡總是真
019她美麗嗎?
021怎麼死?
第一章 陳家有女
026 她的名字
030 一個女子的誕生
036 愛上了「匪兵甲」
039 災難的來臨
第二章 雨季不再來
044 軌外生活的開端
046 一種溫柔而瞭解你的人
051 舒凡:擦肩而過的戀人
064 樂莫樂兮新相識
第三章 「我的撒哈拉之心」
070 Echo,再見! Echo,再見!
076 六年之約你還記得嗎?
086 最優良的家庭主婦
106 生和死有愛就隔不開
第四章 一個女人的生活方式
116 簡單生活
117 讀書
119 寫作
124...
006不凡人生
010平凡文章
013愛情:轟轟烈烈傷己心
016婚姻:平平淡淡總是真
019她美麗嗎?
021怎麼死?
第一章 陳家有女
026 她的名字
030 一個女子的誕生
036 愛上了「匪兵甲」
039 災難的來臨
第二章 雨季不再來
044 軌外生活的開端
046 一種溫柔而瞭解你的人
051 舒凡:擦肩而過的戀人
064 樂莫樂兮新相識
第三章 「我的撒哈拉之心」
070 Echo,再見! Echo,再見!
076 六年之約你還記得嗎?
086 最優良的家庭主婦
106 生和死有愛就隔不開
第四章 一個女人的生活方式
116 簡單生活
117 讀書
119 寫作
124...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劉蘭芳
- 出版社: 思行文化 出版日期:2013-08-21 ISBN/ISSN:978986889593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47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