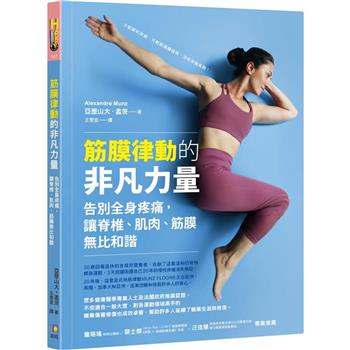人們拜神、求籤,從籤詩中望文生義得到神明的指示,殊不知在龍山寺觀音靈籤一百首中,說的都是先民歷史文化的智慧結晶,這些先民的苦心,隨著龍山寺建寺已安然渡過了兩百七十多個春秋,經過十萬多日的考驗。籤詩看似各自獨立有時相隔五十首之遙卻環環相扣,此點繼承司馬遷《史記》精神,將各籤詩間之人、事、地、言、物做有形、無形的展延,成就先民通史。
此書談及的籤詩裡,共有八位代表性人物:順序是姜太公、鬼谷子、范蠡、孫臏、張良、達摩、呂洞賓、西王母八家。西王母曾是中國人民的共同信仰,但在哲學歷史的範疇裡卻非一般人能了解,但由於她在五帝時代對中國文化有重大影響,因此於此書佔了較大的篇幅介紹。這八位古人,帶動了中國的哲學歷史,由各式典籍中流傳到了現在。
作者黃凡,以龍山寺籤詩為引,講述了其中從黃帝開始直至漢朝的有關故事,由籤詩主角說起,仔細分析當時事件,以及對於相關人物的影響,更觸類旁通廣搜相關史料、典籍,在中國書海裡為讀者講解相關的歷史故事。
作者簡介:
黃凡,本名黃孝忠,臺北市人,先祖為四百年前隨鄭成功來臺的部將。他是當代最重要的小說家,獲獎無數,並締造了三座里程碑,齊邦媛教授讚他為「一個光輝的名字」!為臺灣都市文學,後現代文學的開創者,他的作品已被翻譯成英、法、德、日、捷克等國文字,深獲國際的肯定。
黃凡是當下最具代表性的知性型作家,他用極大的勇氣革新技法,為鄉土文學論戰以後,創作疲軟的文壇注入了新鮮活力,打開了一條政治、都市和後現代書寫的道路,以致引領風騷十多年。二○○四年的最新奉獻為長篇小說《大學之賊》,除保留對臺灣社會獨到的觀察角度外,又多了一份冷峻,並由此上升到哲學的高度,使人感到黃凡的小說時代仍方興未艾。
──中國新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臺港文學研究所所長古遠清
黃凡的喜劇靈感狡黠冷峻,為近年作家中所少見,即使最貌似真實的作品,也會被他突如其來的幻想,攪得紛擾曲折,比起三、四○年代的張天翼、錢鍾書仍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央研究院院士 王德威
在臺灣作家中,我最為推崇黃凡的作品,黃凡與其他作家比起來,有相當的獨創勇氣,特別在男女關係的處理上,技巧為同輩作家所不及。
──前德國魯爾大學東亞系系主任 馬漢茂
把臺灣現代社會各個層面,用不被拘束的自由主義觀點,予以分析導入小說世界的,當推作家黃凡了,他已經超越了鄉土文學,從現代社會的各種活動現象,來凝視人性和行為,他代表了八○年代的創作目標和創作方向。
──國策顧問,臺灣文學評論家葉石濤
其作品包括政治小說,都市小說,科幻小說等各種類型,表現手法則寫實、現代、後現代並具,或開風氣之先,或獨樹一幟,均受文壇高度重視與肯定。
──《大學文選》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二○○五年九月出版。
the best example was probably Huang Fan's story Lai So, which satirized not only the Communists and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but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the ruling party, the Kuomintang, as well.──《大英百科全書》
章節試閱
天國反撲
――姜太公的十字架
〈姜太公渭水遇文王〉觀世音靈籤第八十九首
出入營謀大吉昌 無瑕玉在石中藏
如今幸得高人指 獲寶從心喜不常
臺灣廟會最熱鬧的,莫過民間的藝陣遊行。除了職業性的陣頭,還有信徒組團來神明前獻藝,我們這些沒有節目可表演的,也樂於站在路邊,對那些閃閃發亮、有趣的「藝閣」、「陣頭」指指點點,看久了,頗有點心得。
南部人情味濃厚,遊行的花樣或許不夠華麗,但人人參與的熱情,不論表演的是成人還是小朋友,沿路贏得的鞭炮、喝采,都讓人融入節慶歡樂的氣氛。
藝閣的原名叫做「詩意內閣」,有裝臺閣及蜈蚣閣之分。裝臺閣是小型的藝閣,由勇伕對扛,後來改良為機械式,倒非臺灣迎神賽會所獨有,在日本祭典、中國大陸的廟會都極普遍,還有各種爭奇鬥妍的競賽;若溯及古代,印度經典中更有諸多記載,信奉小乘的東南亞也有悠久的傳統。
蜈蚣閣的意義則比較嚴肅,具有驅邪除穢的功能,獨立於藝閣之外,被稱為「蜈蚣陣」。
陣頭是鄉土性表演,民俗趣味濃厚,但是若要強加以「藝術」來做改良,倒大可不必;人們樂於親近是因為有歷史源流,既然表演得是跑旱船、媒婆、弄車鼓、八美圖、老揹少……就是愈鄉土愈好,愈民俗愈佳;至於蚌殼精雖是出自《淮南子》的鷸蚌相爭,除了正統男主角老漁翁之外,為了減少單調,我還看過「海鮮之最高境界」,由小學生扮演的忍者龜、章魚小丸子、鯉魚娘仔、蝦公大神、東海老龍王……
民俗專家考據陣頭表演將之分類成六大類:宗教、番陣、音樂、小戲、喪葬、趣味。
每當鞭炮和八音在街一響起,不論是哪一種陣頭,大家都會放下手邊的事跑到街上看,職業陣頭、庄頭陣都一樣受歡迎,如果正巧端午節到鹿港去,還可以看到白鬍子的姜太公在街上跑。
臺灣民間搬演野臺戲《封神演義》,大家向來愛看〈文王拖車〉;彰化縣鹿港鎮興化里主祀許府三千歲的聖宮,就有這樣的陣頭。
《封神演義》與《史記》懸隔,就連記敘也跟《封神榜》不同。但和人民親近,由姜太公的「太公車」可見一斑,此車在臺灣有多種用途,甚至可用來迎娶新娘,更由於是獨轎車,新娘得坐在新郎腿上,甜蜜到不行。
《封神榜.第二十四回.渭水文王聘姜子牙》,周文王乘得是鸞輿,子牙乘得是馬,《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與文王一同乘車而歸,文王尊太公為太師。若論誰寫得有趣些,《封神演義》在這一段,可說是替天下不得志的讀書人大大討了一個公道。
臺灣民間的野臺戲只要演到〈文王拖車〉,就人人叫好。
這是描述周文王姬昌帶夫散宜生、武德將軍武吉等文武百官,到渭水尋訪賢人高士,禮聘到姜子牙;太公為了考驗文王,自己坐在車裡,令他拖車;文王已年高體邁,但表示十足的誠意,拖走車子奮力一拉,拉了八百八十步終於力竭停下,姜子牙不滿意,再三請他拖拉,但周文王真的支持不住,姜子牙這才下車,嘆息了一聲:「周祚八百八十年矣!」周送王再想請姜子牙上車,但天機已洩,周朝果然到了八百八十年時氣數散盡。野臺戲臺下有諸多「馬後礮」先生、小姐、大爺、大娘,這時候也都會紛紛表達高見,批評一番。
〈周本紀〉裡壓根沒有這一段,但〈周本紀〉本身是不是正史,也有很多質疑者。臺灣先民一點也不在意,將〈文王拖車〉在廟裡刻了石雕、粉了彩畫,還導演戲曲。武聖宮的陣頭每次一出來就非常轟動,大家都愛看姜太公讓文王出醜,當然不是討厭文王,而是重視他在戲裡的象徵,姜太公是一輩子不如意的老書生,文王替他拖車,也擴大了範圍、境界、禮賢了天下不如意的人。滿足大家的空虛失落。
武聖宮的陣頭,一團成員二十六位,包括開道的七位長吹、兩面的馬頭鑼都穿著戲服,再來是頭旗、儀仗、主陣。儀仗開始之後,左右二邊名六位,一、五是旗手,手持「周」字黃旗,其他是鎗兵,主陣出現時,由兩名鎗兵押後,宜生與武吉二武將分侍左右,服飾華美、威風凜凜,這二十四位雖然只負責化裝遊行,但步數、架勢、表情都非常講究;姜子牙的工作是安坐車內「欣賞」端午節。「重」頭戲在黑鬚黑髮的周文王身上,番陣一開始動靜,他就使勁拉車,每拉一下,觀眾就叫一聲好,厚重的古裝,濃濃的脂粉,弄得「周文王」汗流浹背。胸口、背心很快就碗大一塊濕,拉得半死也沒人同情,大家還不斷鼓勵再鼓勵,中場更不許換人,得「走」完全程才算盡了心願,還有人見他勞累,「落井下石」;要他喊姜子牙出來,自己進去涼快一下,作弄半天,「文王」只有忍辱負重,不僅是他戲份喫重,也是大家心目中「仁君」應有的態度,所以「文王」與民同樂時,真讓大夥開心,這是民間最真實的聲音。
「文王拖車」不是姜子牙一個人的故事,他之所以特別凸顯,是因為他遇明主已是七十老翁,在這之前,他是個瘋老頭、逐夫、失敗者,做什麼都被人嫌棄,在渭水釣魚連釣鉤都沒有,「釣」的是誰,非常令人懷疑,還要「高人」指點,這位菩薩心腸的璞玉,才獲得文王青睞;但為什麼籤詩上說:「獲寶從心喜不常」?這句詩牽動著一個非常大的秘密,大到迫紂王自殺,使商朝亡國,這個謎,《老子》、《孔子》、《莊子》都有興趣,但一直保留到唐代,才讓禪師給聯手破了,不過在大眾來看終究是一個謎。若要說得清楚,不是三言兩語,我和包裹居士決定合寫一本《古池》。
姜太公遇文王前的半生,是眾多讀書人的遭遇,歷史上不知有多少人寒窗苦讀,夙夜匪懈,空有滿腹才華,一肚子理想,自許「文可安邦武可定國」,卻一生得不著半個知音,甚至連一個「狂名」、「癡名」亦不可得;就連當年司馬遷也受盡磨折,但他跟姜太公一樣的能忍,姜太公受的是長期的誤解、白眼、凍餒,司馬遷在身受極刑時也無慍色,因為他「懼志行之無聞,疾沒世而名不稱」,唯有堅持到最後;想辦法將作品流傳下去,才可以償還所有的侮辱與痛苦,「雖被萬戮」也不會有一點後悔;司馬遷這句話是對「智者」的講的,但,對鹿港鄉下,臺南鄉下的「凡夫俗子」而言,難道就沒有感觸嗎?
每一年都有端午節,每年廟會上的鄉人,都憐惜著姜太公,也同時憐惜著歷史上多少被洪流淹沒,而始終叫不出一聲的石中玉!
這些人,他們的不幸來自知識份身份。知識份子販賣知識並不太難,難的是若具有理想與才華――被我們稱作讀書人的,也就是「既不放也不收的傢伙」(誰看見過仙鶴去種田百合花去織布?)一般人看待這些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衣食皆俯仰於人、不時還說些別人聽不懂狂言的人會順眼嗎?除非他們能提出什麼有力證明,最好有國王替他們背書,否則是不能被當作人看待,連李白都要待業,杜甫都得餓肚子,更何況其他呢?
中國的社會裡,思想家尤其是危險份子,不屬於正當行業,無利於大眾,還會鼓動別人造反。
古老的社會結構,漁獵農牧各司其職、各食其力、各得其所;後來社會進化有了雛型,才開始有「管理人」。經典裡所謂的「牧者」,最早的意義代表就是管理人――大家的主。這個主可不是沒事就抓幾個人去砍頭,不時找幾個美人進宮,他所擔負的真是牧羊人的責任,既繁且重還常不得休息,至於後來出了作威作福、作孽多端的昏君,純粹是人民不好,自己放棄監督之責。
管理人的系統由上而下,是王、貴族、大臣、地主……這也是最早的服務業。
古代共主不直接參加生產,但他們規劃族群方向、訂定政策、發令執行;貴族幫助政府組織各種系統,他們由於有受教育的特權,而成為知識份子,出任冢宰(行政)、司徒(賦稅.徭役)、宗伯(禮樂.教化)、司馬(軍政)、司寇(司法)的工作,即使是政府組織尚未完備前,也得義不容辭的進行人治。所謂的地主其實還有管理員身份,上有大王、小王、貴族等著他交稅納貢,下有耕夫、佃戶、奴隸等著溫飽,地主不僅要了解土地、灌溉、種植、病蟲害防治、施肥,更要管控產銷,負責農具的研發、修理,真是一點也不得閒,名義上是地主,實際上,工、商、農都一腳踢。平時還得參加國家、鄉里的義務勞動,戰爭期間,又要將耕伕、奴隸等訓成戰士,農技轉成戰技、農具成為武器,這些完全沒有特支經費,得地主自行籌備,設法指揮。
依照《太公兵法》,兵學是科學也是藝術,運用存乎一心,以河圖洛書作為兵法指南,運用隨著時空變化作適度之調度,其中奧妙就不是耕夫所能了解,耕夫也沒興趣了解。
普羅大眾對讀書人的輕視,與其本身立場有莫大關係,因為這些實際上付出血汗的勞動者,難以了解靠著一張嘴就有飯吃的讀書人,河圖洛書只不過一些數字加加減減,看來也沒什麼困難――
再說戰爭如何「寓戰於農」,以上面所提,農技,農具的轉換為例――耕戶用的丰耜,丰(柄)只要深插入土就可以作為抵擋敵人的拒馬,耜(鋤)作矛戟,農民的蓑衣、雨傘、笠帽充作軍用雨具、掘土的钁、鍤、伐木用的斧鋸、舂米用的杵、臼稍作規劃,在戰時都是攻城工具。耕田用的牛馬可運輸糧草、戰備,雞犬可充偵伺、報時,婦女所織之縑帛,拿來製作用旗。有關農技的轉換,撥刈草蕀之法便是迎向車兵、騎兵之術,耕耨田畝之法可對付騎步兵。至於秋收的禾糧、薪柴是戰備,冬天的食廩就是戰時的守備。
農人的平時編制――伍、鄰、里,一經動員就是軍隊,里吏、鄉長就是指揮,春秋雨季修治城廓、疏通溝渠,就是戰時的塹壘維修。
姜太公除了深懂八卦的奧義,有事沒有「掐指一算」外,他對農人的了解,以上這都在他的兵法中佔有一席之地,這樣的一位文武全才,卻始終被人們當做「騙碗飯吃」的老頭,不受文盲的尊敬,非經過十七年的掙扎,文王傾全國之力來配合他,尊為「太公望」,說服了所有人,他才從大家眼中的「老笨蛋」,洗清滿身冤曲。
天國反撲
――姜太公的十字架
〈姜太公渭水遇文王〉觀世音靈籤第八十九首
出入營謀大吉昌 無瑕玉在石中藏
如今幸得高人指 獲寶從心喜不常
臺灣廟會最熱鬧的,莫過民間的藝陣遊行。除了職業性的陣頭,還有信徒組團來神明前獻藝,我們這些沒有節目可表演的,也樂於站在路邊,對那些閃閃發亮、有趣的「藝閣」、「陣頭」指指點點,看久了,頗有點心得。
南部人情味濃厚,遊行的花樣或許不夠華麗,但人人參與的熱情,不論表演的是成人還是小朋友,沿路贏得的鞭炮、喝采,都讓人融入節慶歡樂的氣氛。
藝閣的原名叫做「詩意內閣」,有裝臺...
作者序
美國人的由來 黃凡
――一則有趣的臺灣文學
一九五○年代冷戰時期,美國會通過援華後,美軍跟澎湖有了近距離接觸。戰爭期間的年輕大兵,舉止自然不夠莊重;開放的態度,在漢人眼中根本毫無體統,更何況原本就在文化、語言、生活習慣上格格不入。最令人不自在的,是他們迥異東方人的長相──金棕色的頭髮,鳥一般的藍眼珠、凸鼻仔,即便穿著整齊,看起來也是毛茸茸的。
保守的澎湖人,表面上完全看不出對這些美國人有任何反應,但不久之後,人類學家到馬公市東衛村田野調查,意外得到一個新故事──美國人的由來。
採集到這故事的,不只一位,敘述者也不僅一人;由於大同小異,此處以彼岸近年出版之《台灣神話與傳說》中,所收錄之文大許教授的采風──
從前有個皇帝的女兒得了痲瘋病。另一說法是,太后生了重病,不過無論是太后還是公主,反正都是治不好的怪病,心急如焚的皇帝重金懸賞,向民間廣求名醫,結果宮裡老太監所養大的跛猴子前來應徵,說自己有個祕方包醫包治,不過皇帝得答應把美麗的公主嫁給牠,才願意提供醫療,這是趁人之危,但皇帝再不願意也只有點頭。
於是猴子大夫去到高山懸崖,萬分艱難的採了猴兒茶,治好公主。
皇帝將把尊貴的女兒嫁給猴子的新聞,立刻轟動全國,被國人引為笑談。可憐的皇帝既愧且悔,但想盡辦法,猴子都不肯交換,皇帝無法背信,只好把公主許配給奸詐又可惡的猴子。
跛猴娶了不幸的公主後,這隻毛茸茸的畜牲,不能見容天下,不得已帶著公主遠渡重洋到美國去,以種番薯、花生與芋頭維生。
卑鄙的猴子有了好太太,也很努力工作來養家活口,不久之後,還生了一個猴子小孩,外型毛茸茸的,完全是跛猴的翻版,心地更是無比奸詐,「青出於藍」。
猴子小孩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有人放屁,而老猴子卻自恃為一家之長,到處放臭屁。有一天,老猴子在田裡忙,猴囝仔趁著送飯時,把這個配不上公主的傢伙給用石頭砸死了。
公主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之後,頓失所有的倚靠,為了不失去女人應有的重要身分,以及得到生活所需,靈機一動,化妝成別的女性,用騙術嫁給無知的兒子;亂倫後,跟猴子孩兒生出許多毛茸茸又毫無品德的後代,就是現在滿身是毛的美國人。
故事裡,茶葉、生了痲瘋病的公主,婚前婚後的猴太太、跛猴、屁、猴囝仔、美國人……這些象徵,是由憤怒、怨恨的澎湖人,將順手拈來的原型,在種植花生、番薯與芋頭的土地上,一一化成自家的故事。而且又因為人類學者採集及時,留住了田野中集體創作的種種痕跡。
故事,是虛構的,但往往借來反映時代,以故兼具虛幻與現實,甚至在大家都知道「只是個故事」的前提下,將矛盾、不合理之處,以不可思議的方式處理,令人意外的情境猶如夢幻,四兩撥千斤的,風格充滿詩意,顛覆惱人的真實人生,反而特別有趣,更令人感動。
這也是人類有了語言工具,才能把自身的種種遭遇,表現成思想的文明過程。歷史的變遷中,對人類智慧最嚴厲的批判,就是在被認定為「不值得批判」的公論下遭到淘汰;只有少部分古老的智慧結晶,幸運的傳播到各地去,也開始了各種延伸,生出了子子孫孫,一個個被口耳相傳的神話、故事,憑藉著簡單的元素,在時間的洪流中不斷經過淘煉、改寫;受到挑戰的原作者早被隱沒了名姓,接受挑戰的自由創作者,逐一或同時嘗試著將之與民族的夢想、傳統,深植人心的哀愁、恐懼,用新時代觀點重新創造能再流傳的新故事。只要能抓住原型的形上精髓,情趣轉化得愈高妙,就愈能打動人心。變型得愈厲害,愈發旺如野地裡的花,經風一吹便歸無有,就連原處也不再認得它,(此處的無有,自有其高妙處,禪宗公案有最多、最眼花撩亂的表演,外人一見便徬徨無主、徒亂心魂;坊間之胡言亂語各種《公案解讀》即為明證)。
常有人認為──大題目都早已用罄,好的故事根本已被寫完;這是衛護自家缺乏內涵作品的藉口,至少是錯誤觀念。時代的演變會帶來各種新的衝突、新的問題,四周都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若是對歷史沒有認知,對時代沒有反省,是不可能造就傑出的作家、作品的。只是,要能在深度與廣度上,恰如其分、恰到好處,面臨到的考驗,也常是創作者始料未及。所以,嚼飯餵人或靈光乍現,高低之分主要決定於作者的六分才華(包括悟性),不能靠教導,也別指望水磨功夫。
這則〈美國人的由來〉,繼承了不少歷史遺產,我們不妨來充當偵探,來為之萬里尋母,即可發現它的身世不凡,譜系顯赫;爸爸媽媽、祖父外祖母洋洋大觀,主要可分為五則:
一、中國推原神話〈盤瓠〉──這神話同時是〈盤古〉之前身。所謂推原,依照彼岸學者解釋,便是推尋事物之始、起源。初民對事物成因,每每無法給予答案,只好創造神話滿足求知慾,以及特屬於人類本能的好奇心。
二、〈蠶馬〉。故事很普及,此不贅述。
三、西元前五世紀希臘悲劇〈伊底帕斯〉弒父娶母。
四、女媧、伏羲(盤古)磨盤結親(這故事與天竺脫不了關係,祖輩是禪宗公案指涉的西方人);大意是女媧、伏羲婚後生了一個怪物──磨刀石,夫妻愁憂之下砸碎愛情見證,磨刀石的碎片滾下山,流到水裡變成魚蝦。對此若有似曾相識之感,不妨參考希臘羅馬神話盜火者普羅米修斯的第三個故事──石頭人後裔。
五、本地早先的原住民神話(布農族的祖先)。典中之典是〈犬戎國〉。大意與〈美國人的由來〉相似。美麗的布農族頭目的女兒生了皮膚病,變成可怕的模樣,巫醫束手,倒有一隻狗跑來聲稱能治,惹來衛護公主的眾位勇士憤怒地趕走狗,但狗兒潛至公主床上遍舔全身,公主便告痊癒。頭目不願履約,託辭要狗變成人,才允許嫁女,狗兒經過努力奮鬥,成功改變形象;頭目只有為狗人主持婚禮,然後羞憤不已的趕走狗夫妻。狗人帶著太太遠走他方,生下小孩,但狗仔長大後殺父娶母,又生了後代,來到台灣,便是布農人的祖先。布農人表現其勇氣的神話裡,處處標榜傳統道德形象,竟在最後突破歧視,有革命性的一舉,從拒絕到接受,頗耐人尋味。(在此,我順便提一下前年秋天一篇可能是來自監獄的文學獎甄選遺珠,雖然最後只得到我的一票,但頗有文采。原典出於〈盤瓠〉,經改寫後面目全非,卻極具巧思。作者在濃濃的南國風情裡加入了魚鱗症、經血、女巫的湯、大型爬蟲類寵物、珊瑚……文中只見創造人類婚姻之始的鱗身伏羲、蛇軀女媧四處游走,又在新世紀有了新面目;也把普羅米修斯、希臘神話〈金羊毛〉裡米蒂亞弒親殺子,以及安徒生的〈小美人魚〉寫了進來,大體說來,作者作了有趣、大膽的嘗試,所以雖敗猶榮。)
〈美國人的由來〉引起人類學家的興趣,是因為特殊的時空背景所帶來的意義。
光是講述一個故事,不是文學。罵美國人是猴子的痲瘋老婆亂倫之後裔,也非文學。民間曠男怨恨政府不顧自己娶不到妻子,卻放任女同胞賣身給美國人,當然更不是文學!但能把深藏的哀痛,有了進一步的思考,賦予出深度與涵義,昇華出形上的果實,就是文學。
前言
釋儒道三學與臺灣先民
近年,有識之士討論著臺灣文化的未來、或者究竟有沒有未來時,聲音不大卻很焦慮;但是站在歷史洪流中,這絕對不是個新鮮話題。
打從先民渡過黑水溝時,無論是以何種原因踏上這塊土地――流亡的革命家、逃荒的農民、罪犯、海寇、無以維生窮漢、找尋桃花源的幻想者、漁民、甚至包括鄭氏部隊的蒙古人後裔……,早在出發之前,其實都有共同的憂患意識:遠離故土故人後,子孫們是不是自要茹毛飲血,成為化外之民。
所以,在談臺灣文化之未來,我們應回顧一下――臺灣文學之過去。
當年告別唐山的讀書人非常擔心,子孫們會因隔閡而遺忘自己古老優美的文化,甚至因為出現斷層,根本以為自己是猴子的表親。
這些子孫包括絕大多數的文盲,古來受教育的機會並不普遍(不過近來也有人稱呼雖受正式的現代教育,卻不知文化為何物的人為新文盲),一個文盲要如何承襲傳統、記憶文化,更要如何將文化有效傳承下去?除了利用節慶祭典、掃墓拜祖先、領壓歲錢……還有更好的辦法?
這並非杞人憂天,因為後來在綠島,果然發生由於須順應天然環境,而回歸了大自然的生活(一九五○年代,軍法處以隔離政策,將政治犯從內湖新生總隊送到綠島時,官方製作的檔案,影像紀錄意外捕捉到島民的生活,便是此憂之真實見證)。
當然,在這些懷疑、焦慮、憂傷、恐懼之前才得先要有子孫才行――
明鄭時期,清廷孤立明鄭勢力厲行遷界,但無法阻止流民入臺,當時約有五萬人衝破海禁,而原在臺之漢人有荷據時期之二萬五千人,隨明鄭來臺之三萬七千人,共約十一萬二千人左右。由於一五五○年代,美洲作物甘藷、花生、玉米經澎湖傳入臺灣而普遍推廣,本地的土地人口扶養力遽增,吸引大批閩粵流民,但在一八七五年廢止禁令前,這些人是羅漢腳,無父母妻女宗族之繫累。
以故,另一個現象的問題是――只有唐山公,沒有唐山媽。一直到十八世紀清據時期,除了臺灣府古來的舊住民,其他三縣:諸羅、鳯山、彰化都是無妻的新住民。
荷據、明鄭、滿清時期,臺灣是一個移民社會,在十七世紀羅漢腳已與本地平埔女人結婚生子,因為漢人(包括充分漢化),來到臺灣之後,即使沒有朝廷禁令,此地也極缺可婚配的漢人女性;島上唯一可以滿足傳宗接代願望的,是雙方在文化、語言上都有絕大差異的原住民女子,但這也非一廂情願便可達成,得排除萬難、甚至使出各種手段;例如鄭成功部隊為了安撫軍心,強制官兵搶平埔女子為妻。
在「無後為大」的壓力下,與原住民女性結合的幸運兒,解決了傳家繼世的問題,但馬上又面臨到難題――如何避免向原住民文化傾斜。
在當時,漢人完全不了解、更無機會深入的原住民文化,當然不具有任何吸引力(本島的平埔族西拉雅系的蔦松文化,在各種不利的條件下,早跟大部份平埔文化消失得無影無蹤;而尚存的其他原住民文化一路至今才得到尊重。而且經過考古的努力,發現某些習俗與大陸自新石器時代就有共通,例如成年禮同屬「海洋性拔牙俗圈」,兩岸學者指出臺灣原住民有九成拔牙比率延續到日據時期的拔牙的習俗,不能排除受大陸影響或可能於大陸系,以及一九四八年國分直一勘察之營埔遺跡有可能與山東黑陶文化末期之承襲等等,然而後代出生後,除了承繼母系的血統、體質特徵,也勢必無法避免母親原生家庭的人優勢影響。
讀書人對於現實的景況,憂心自是超過一般移民,深思之後,為了正本清源,做過種種努力。目前仍然可見的成果,而且具有代表性的當屬廟宇,剛好一在南,一在北。
在臺南府城的是建於西元一六六五年的孔廟,純粹以傳統出現;在北部的是舊稱艋舺,建於一七三八年之萬華龍山寺――不論在二十三萬兩白銀重建之前、還是之後,釋儒道三家都透過籤詩,落實於臺灣人的生活。
現以年代先後區分,先談臺南孔廟。
鄭經建於明鄭時期,永曆十九年柱仔行街的孔廟,是由讀書人來奉祀,祭典儀式與山東曲阜一樣依王制,迄今已有346年,最有趣的是儒家之表現方式,在於儒王的精神象徵――建築硬體氣度寬宏,軟體實是些牌位,頗有「文以載道」的意義。
當後人來到孔廟,在空間、動線充分的誘導下走到牌位前,不由自主地一一唸出那些莊重的、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大儒之名時,自有一番滋味。
提到儒學,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四書,這是南宋涼熙間,朱熹取《小戴禮》中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為四書,復為之章句集注,又稱四子書。
要講解四書,開宗明義地就在四本書名上。限於篇幅,簡單的講一下。
《大學》,什麼是「大」?大有無量、無上、善(形上)、始、深、尊……等義,天之大謂太,永遠都多上那麼一點,是詭辯者之最愛。人大謂奘、盛大曰奕、力大曰夯、物大異於常是奇;儒家用大、用中,用得大有謀略。
什麼是「學」呢?學初到是「術」,藉術之「覺」,先使受教者(倣效的學生)去其蒙蔽、而自反自強;對教授者也可自我覺悟、教學相長。教師、弟子都必須身心自我約束,所以儒家期許《大學》,是無上的覺悟,真諦的領受。
《中庸》,「中」,有三種解釋,其一是達到目標、相契合。進而不依二邊,最後昇華到「離二邊而不執中」。「庸」,小篆的庸,有庚有用。庚有垂實之象,象徵物實,本義作「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更是西方也是道(有人將「法」稱為道,不全),萬物得由其「道」,庚可解成「繼續」,但要克服弔詭,否則寧可藏拙。「用」是可施行,行而繼之以「常」為之庸。常是什麼?是名言上的不變易;常道,是名言上永恆的道,儒家認為已臻真理,跟「經」的意思相同。
《中庸》就是不執中,不以中為我――「無我的真理」,是出世法,但以世間名言呈現,有多不得已?本身就充滿辯證。
《論語》,論,表面上是《說文》之――凡言語循其禮,得其宜。或是考量,議,其實它是理,「有其道之理,便是智慧」,但它在法則之內,卻又以無為最上。
語,《說文》的語,解釋是「論」。直言為言,應答為語;非「不問自說」,而是以二邊相論做為表達思想的工具,有相契、對應各種關係,《論語》之意是智慧的載體,也就是微言大義――「文以載道」。孔聖人(神、明)乃指月之指。月亮固然重要,沒有這一指,學子怎脫蒙昧,君王怎會有道?
《孟子》,孟是開始,子指世法,所以是「開始講述世法」。即使是「浩然之氣」、「大道」、「矢人函人」這種學問,也說得很平實,讓學的人不至於東想西猜,誤人誤事。語言用得也很不俗――例如萬章問孟子:「帝堯將天下給舜,有這回事嗎?」孟子回答:「沒這事,天子不能將天下給人。」萬章又問:「照如此說來,舜有天下是誰給的?」孟子答:「是天給他的。」萬章問:「天給他時,是不是很誠懇又詳細地告知呢?」孟子說:「天不說話,只是就舜之德行與行事,暗示著將天下給他……讓他主持祭祀,所有鬼神都來享用,就是上天接受他,讓他主理天下事,萬事妥善,老百姓安心信服,人民接受他;天給他、人民給他……舜輔佐帝堯二十八年,不是人力能做得到,而是上天幫的忙啊!如《尚書.泰誓》說:『老天爺無眼,祂的視察能力都從百姓之視察為定;老天無耳朵,祂的聽聞能力都從百姓之聽聞為定。』這就是『天與』」和『人與』的講法。」
孟子的「天人合一」,六道不離人道,對絕對的君權有所打擊,對神秘的天、人交涉,更是致命的反撲;君王即使再「裝神弄鬼」,已被孟子一語道破。
也同時因為他把可以說的都說盡了,孟子之後,儒家再想有什麼出色的「帝王術」都很困難了。
「四」這個字在排列不是隆殺有序,次第而下;從《易》理推演是開方,暗含「天下流佈」之義。儒家要流佈些什麼呢?當然是世間最重要的兩種學問――世法及出世法。這不是儒學首創,但不論是古印度還是古中國,自古以來都是重要的帝王術。在沒有文字之前,各家學說是以祭祀來表現,有了文字之後,紀錄下的儀禮內容,頂重要的就是祭禮中「天人合一」所得到的兩種奧義。世法可教導帝王統馭人民,出世法可讓人民敬畏天子――天神之子,當君王「天人合一」所有羽化成仙的資格。
儒家分析出這種奧義再添上一番學理,成為一家之學;理論很巧妙,身分很像印度的婆羅門,只是,他們無法跟婆羅門一樣藉宗教(儀式與奧義)取得掌理政治的實權,但擔任大臣同樣可以主導國家政事,君王倘有擅動,就可以立即依經典提出糾正,《易經》及四書都是他們常用的法寶。
《易》是帝王術,也是重要的「臣禮」。「經」這個字有度量、治理之義,它本身為尺度,就已是真理。《易》的文字常被人認為模稜兩可,所以是本很好利用的工具書,怎麼解釋都可以,不同意的人得提出有力的反證,而所謂之反證,基礎還不是得站在所反對的說法上!一點也不自由。《易》的地位雖然崇高,卻從來沒有人能夠真正為它定位,所以常有人藉著它搞神秘,而且逍遙「法」外。因為真相是,姜太公當年與周文王在渭水相會時,做了一件中國思想史上最大的事――建構了六十四卦的模型,中國哲學有了實際依據,但思想因而停滯,可以說是集體退化,有什麼新的論說,其實是來自外邦;因為三皇開始就有的「古八卦」被隱蔽,真相永遠冰凍在北極。
三家《易》留給世人的,只剩下宇宙萬有模型六十四卦,這是古八卦的殘影。
儒家的出世法,主要在於天道,精神上還經常與道家混淆,因為它們的來源及目的也總是不謀而合。雖具有形上,但與佛教大乘的出世法迥異。
建立好儒家文化系統,再建造的文廟,當然與一般寺觀大不相同,所以裡面沒有「賽錢箱」,只有一年一度祭孔時,與天子等級的八佾舞。
孔廟啟發臺灣先民的內涵,當然也不真在八佾舞,而是在――無論你有沒有決定要如何度過此生時,啟示你先做一個人。
即使不識字、不上學,不與名流文士交遊,也該好好體會人應知道的事。
這個「人的事」,已不拘泥於文字,而是儒家最擅長的氣質教化。
去過臺南孔廟的人都曉得――孔廟古木參天,建築莊嚴壯濶,白晝雍容高華,入夜肅穆古雅;尤其是晚間的照明恰如其份,至聖先師的格局,讓人不論何時置身此地,自然覺得自己像個人,至少想好好做個人。
如果走入孔廟的是個壞人,莊嚴的格局會讓他不知不覺地會起慚愧心,若是不能立即改過向善,至少不會水流更下。而天生的壞胚子,就絕不會喜歡這裡,不是想把孔廟的「圍牆」拆掉,就是將建築物敉平(歷史上發生過這麼一件事:
一八九五年四月底,馬關條約議定臺灣割讓日本,內定樺山資紀伯爵為臺灣總督,樺山將臺灣殖民地教育的大任委諸伊澤修二,開始了日本治臺五十年的教育史。以總督府學務部為重心的日本學者所做的臺語研究,竟是臺語研究二百年史最璀璨的五十年。日人編纂了數十本臺語教科書,創刊六種臺語雜誌,編了十數本日臺字典、臺日字典、俚諺典、地方詞典、植物名彙、職業名彙等臺語詞典,為臺語留下汗牛充棟的寶貴文獻,也以專業素養開創學術研究的風氣,但這些漂亮的成果背後的目的,其實是藉著臺語瞭解臺灣,並以臺語教育達到統治目的;當年六月十七日,伊澤抵臺北,次日上書設置「土語講習所」,提出臺灣教育意見書,六月二十六日將學務部遷往芝山巖,開始研究臺語、編輯會話書籍。就在芝山巖「開漳聖王廟」中對所招收的21名日本語傳習生進行三個月的短期速成教育,好讓這些臺灣人擔任曰人與臺人的溝通媒介時,黑旗軍劉永福在抗日戰鬥且戰且退,退到臺南城後,十月十九日逃回廈門;臺南城內大亂,府城大學校長英人巴克禮牧師,依城中紳士之請,率領十四人代表團向乃木將軍投降,日軍在毫無抵抗情況下入城,接收所有政府單位,其中文廟被改成臨時病院,伊澤在日軍佔領臺南後的第三日――十月二十五日隨樺山南下,伊澤去的第一個地方就是孔廟,立刻上報給總督請示恢復原狀,並派兵保護,因為這種污辱文廟的行為,踐踏臺灣人的文化與人格,非常傷害臺灣人的感情,會引起比日軍進城更大的反抗。對孔廟釋出善意的伊澤,為臺灣教育的創制者,被後世稱為臺灣殖民地教育之父,一八九六年創設「國語學校」,落實以日語教育為殖民地教育方針的同化主義;從保護孔廟到養成臺灣人以「本國精神為本旨」不到一年)。
伊澤在日本以宣揚「國家主義教育思想」著稱,打擊自由主義向來不遺餘力;在一八九五年六月之前未曾到過臺灣,不認識一個臺灣人,卻對臺灣教育充滿了野心,內中雖然處處是荒謬和誤會,但對「教育」臺灣人一點也不氣餒。「永遠的教育事業」最大的眼中釘就是孔子孟子,在受到西方文化重大衝擊的日本改革家心中,不把孔孟趕出臺灣人的心裡,「國語」教育不會有成功的一天,但他初期採取懷柔,維護臺灣人的精神堡壘――孔廟,比只會使槍弄礮的關東軍,高明不少。
連一個莫名其妙搭上歷史列車的日本人都看得出來,臺灣人受得是什麼樣的潛移默化,臺灣人只要努力保住傳統,當然會有更大的機會,發展出新的在地文化,使民族更強壯。
――若原住民依此指稱這就是漢人當年之文化佔領,也沒什麼太錯,但定義下得太狹隘,還有商榷的空間。
漢人在島上遍插漢家旗,宣告文化領地,絕對不是只限於臺灣、臺南,影響力遍及所至,所向披靡。歷史上的「外國人」――五戎、蒙古人、女真人、回族,其至於來到中國的猶太人,都因為「致命的吸引力」,融合成一爐。尤其是滿人,大家不妨去看看大清統治末期的科考官方檔案,彼岸的出版社已有完整的整理,有多少文章優於漢人的八旗進士,是早已不會講母語的滿人子弟,殿試時皇帝一問及「媽媽的話」,便急得面紅耳赤。
假如外地人來到北京,若只是會打些「官腔」,立刻要被發現是外人,因為北京大街小巷的普遍人生活中,還在講著辭海上不曾出現的「本土語言」,是外地人完全不能進入情況的柵欄,比如「媽楞」、「蛤什馬」、「玳牡貓」,分別指的是蜻蜓、長白山林蛙卵巢,三色如玳瑁花紋的母花貓。
這些地道、不時冒出一兩句、具有相當份量,代表著北京城生活文化的滿州話,是可證明由關外一路殺進來的滿洲人,強權統治三百餘年之後,沒有了王朝,也不再屬於小族群。
至於更早的、元末南下的蒙古人,在中國南方落地生根,元朝亡了也未回到大漢去,倒像水珠般化進了中國這座大海,充份與當地人融合,不分彼此,也再分不出來彼此。
古老的漢人文化如果不夠好、不夠用、不夠深度,經不起千錘百鍊,就是到處佔領,也必然到處碰壁。至於一些不符時代需求的觀念,「時代」就是最佳改革者。
明鄭時期,除了孔廟、除了歷明鄭三世的沈光文(臺南一中的校歌――「思齊往哲、光文沈公」,可見得人們對這位臺灣開山先賢之懷念)、先民還用了許不同的「故事」、「傳說」,來幫助鞏固漢家領地。
例如――臺中大甲鐵砧山的國姓井、嘉義水上鄉尖山的顏思齊無字墓碑、劍潭投寶劍斬魚精……等等,這些故事不但好聽,也有歷史上考古的價值,不過限於篇幅,此處不多介紹,大家可以上網看一下,因為它們就是臺灣文學的前身。
古文廟在南,老龍山寺在北。
龍山寺香火鼎盛,善男信女眾,對臺灣影層面廣,自廟宇之歷史沿革,便可窺知先民在生活上的奮鬥與經營。
萬華,這個古老的聚落,在意外中建廟,特由泉州晉江安海龍山寺恭請觀世音菩薩像來臺,成為艋舺地區居民之信仰與活動中心與清水祖師祖、大龍峒保安宮,並稱臺北三大廟。二戰時正殿被砲彈擊中全燬,菩薩像卻端坐蓮臺,民眾益信觀音菩薩之靈感;重建後在一九八五年被列為二級古蹟,建築是宮殿式的四合院,正殿供奉佛教崇拜,後殿除地藏菩薩,即是道教神明,方便昔時來自不同地區的移民,同聚在此祭祀「十方圓明、尋聲救苦」的觀音媽,統合地區的宗教、經濟、政治、娛樂、精神生活……;以及自衛力量,所以先民讀書人將心思用在此處確有先見之明,他們的苦心就安排廟中的一百首籤詩。
信眾行禮如儀求得籤詩,定是萬般急切想知道自己所問之吉凶禍福,對於觀世音菩薩所賜與的答案,必然不會等閒視之。
廟中也配合這一點,特設了「解籤處」;倘若解籤人不知道歷史掌故及內中曲折,絕對無法令人滿意。在聽取說明時,善男信女一定會希望有最詳的解讀,甚至意猶未盡,提出一堆問題,這樣一來,即使是文盲,也會對歷史典故產生興趣,而且在探求的過程中,有機會充份了解到,遇事不要只看事相的表面,要學習由絃外之音,更進一步的求索內涵。這種寶貴的教化,同時地令文盲懂得敬重原所陌生的讀書人。
去過一趟廟裡,信徒被各殿的神明庇佑,還得到先民讀書人的諸多照顧,所以,不管後來的日本皇民化(奴化)多麼強烈,中國人心理上仍在拜菩薩、用八卦、看黃曆、打麻將。
這個在二百多年前隨著移民的文學,在本地生根茁壯,就成了臺灣人的文學,非常實用、優美,也不知不覺地用到了今天。
我們不在意唸籤詩時,是用國語、臺語還是客語;因為無論怎樣唸,也改變不了先民的歷史與遺下的寶貴文化。
每當善男信女遇到困難需要解惑,或是來尋求心靈上的安慰,這些籤詩除了應用之外,更蘊涵了讀書人民胞物與的感情。
龍山寺建於乾隆三年,西元一七三八年,迄今一百七十餘年,也就是說,先民之苦心,安然通過了二百七十多個春秋,將近十萬個日子的考驗。
歷史典故、文以載道
為了讓大家了解籤詩,我們先列出百首籤詩的前四首題名為參考:
第一首:〈宋太祖黃袍加身〉,第二首:〈姜太公渭水垂釣〉,第三首〈燕將獨守聊城〉,第四首:〈長樂老歷相五代〉。
只要受過《三字經》、《千字文》、《幼學瓊林》這些啟蒙教育,對這樣的題名必不會陌生,但若是經過慎重選擇的先民讀書人的層次僅此而已,龍山寺的籤詩也就沒什麼好談的了,夫是啟蒙足矣,何必寄情籤詩?
任何學問都需更上一層樓,否則落於僵硬、呆板、教條而已。靈籤之珍貴,正是在於內涵與題名有若干差距,微妙之處,不細心是無法分辨的――
經常有人說,讀史使人明智,不如說――明智的人一定讀史。
但若每一個歷史故事都僅限眾人熟知的內容,熟悉的人物,都被一個「理所當然」的框架給框著――「曹操是白臉、關公是紅臉、張飛是黑臉」,每個時代的每個讀者都不能如此認知,還有誰要看戲,誰要讀歷史?造籤的人、讀籤的人、解籤的人要打破陳舊老套,評論、批判之後,為歷史尋找到一個形上意義,為自己的困難找到一個智慧的方向,不再倚靠一條「大同牌歷史思考生產線」來直通大腦,才是造籤者的使命,求籤者的收獲。
如前面所提求籤者為明瞭聖意,先得對籤詩上的人物、事件、原因、地點、過程與結果產生興趣,繼而求知、揣摩雅意,最後得以昇華,這種用心,其實就是中國人讀史的理想――史家絕唱先千古、無韻離騷澤萬象。
《觀世音靈籤》並不如一般人想像,每一首都是獨立的;當初創作時,不少是由斷代史上打散,其中編年、紀傳均有稽可循,歷史觀照也未特立獨行,所傳承及欲普及之思想文化,常來自儒家。籤詩彼此有的相隔五十首之遙,卻是同一時甚至前因後果環環相扣,又各有各的氣數,各有各的結果,這一點,是繼承了司馬遷寫《史記》的精神。
「欲上肇千秋」是曾隨董仲舒學習《公羊》的司馬遷,在寫作記事上選材、鑑及考訂的標準;也就是「不離『古文』(儒家經典)者近是」,在考證真偽上以儒家六藝為最高準則,最高道德也經常以儒家教訓為尺度,其中奧妙在從容自然,與一般知識份子「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大有分別。
司馬遷以孔子的《春秋》為藍圖,創了中國史學的形式,將史料類比排列、分類解釋,表面上各不相關,事實上史料、篇章間有形、無形之展延、關聯性,將上下三千年之人物、事、言、地、物作為一體之通史。紀中有傳、傳中有紀,使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
儒家最忌迂腐又固執或是不學有術、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解讀者;司馬遷以歷史為己任,不但繼承儒學,還能在自身遭受無比苦難時,昇華出更高的意義,這可由他的〈報任安書〉中的讀書人精神得知一二,文中「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司馬遷還以「俗人」、「智者」區分知識份子與讀書人,文中表達了自己對生命意義持的態度,也教導了馬上要被腰斬(象徵天下受冤屈,不平之心的罪人),在獄中的任安――士大夫面對苦難的生命,靈魂仍有其光明不屈的出路。
龍山寺的籤詩雖是四行詩所濃縮市民版,但仍巧妙因襲太史公的精神,很是難能可貴。
接下來繼續談臺灣先民精神上的需要――儒、釋、道三學。
常有人認為,中華文化的核心,是應用型的哲學,非形上思考;甚至一提到哲學,立從根本上否定中國人有什麼優秀的傳統,只要隨口提一個實際上並不怎樣的西洋人大名,便輕易徹底打敗諸子百家,孔孟被嗤之鼻,老莊亦均極不堪聞問,是無用玄學。
這種誤解,深究起來,除了當事者要增加見識外,其實代表著文化傳承上的悲哀;諸子百家、釋儒道(包括陰陽家)有平易近人的世法,也有深奧的形上學問,更從未自人間消失,不論後人看得懂看不懂,仍好好存在古籍經典中。為什麼出現斷層,「學」與「問」都愈來愈狹窄,值得追究。
偉大、奧妙的中華形上學絕對存在,我們也可以相信,代代都有人自古代典籍發現精華,就算這些讀書人沒有機會發表看法,但依照中國人的智慧,只要因緣和合,一定會大放光明。
*
「觀世音靈籤百首」不只一套版,我選用的是「艋舺龍山寺版」。
透過籤詩,我們不但看到臺灣先民,在成為移民之前,就有的一貫思想,以及其思想方法,還發現不論在廟堂之上,或是最邊陲的民間,中國讀書人藉著釋儒道三學,作文化思考及傳承(佛學雖是外來,但早已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份,反倒在天竺勢微),不論先民或移民最明智的選擇就是把學問藏在廟裡。在統治者經常更換的先民時代,有什麼比寺廟更穩當、更豐富、更方便、更能倚靠的寶庫!
我收集的籤詩還包括有來自淡水助順將軍廟的作品。這座小小的古廟沒什麼香火,原始的供養人是古早的一群碼頭苦力,籤紙均已泛黃,用字淺白,從未引起過什麼注意,但樸實的籤詩,內中充滿禪學奧義,得花心力研究,所以知音更是難尋。
萬華龍山寺籤詩與助順將軍廟系統不同,以儒、道、陰陽家為主(尤其在《哲學歷史》中,陰陽家從姜太公開始,就佔了大多數)。釋的代表作是〈第三十一首。達摩面壁〉,〈第五十四首,呂仙枕黃粱未熟〉(呂洞賓是佛教重要護法),雜項有孝子善士。依歷史年代是夏、周、春秋、戰國、漢、三國、南北朝、唐、五代、宋。元朝則有爭議――〈六十三首黃孝子萬里尋親〉,有兩種考據,第一種以歷史作依據,是載於《二十五史.元史.列傳》的黃覺經孝子。但以老臺灣人對戲劇的喜愛,若用典應是清李玉的作品《萬里圓》(主角明末蘇州人黃孔昭之子黃向堅,一共二十五齣);發生在歷史上明朝滅亡、清兵南下的微妙時空;這對曾經「反清復明」不遺餘力,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的臺灣人有特別的意義。明朝籤詩有海瑞、三寶太監。
〈靈籤〉展開的,就是一部中國歷史,獨缺清史,由於籤詩並非僅為臺灣人所作,但先民也未添加,因為從黑水溝渡臺的中國人,正努力地做好一個臺灣人,這些人離開家後,以自己的性命繼續寫歷史。大冊裡有延續,有開創,在臺灣這塊土地上,連那些沒能度過黑水溝、命喪海峽的人,也在這本史中得到他該有的地位。
龍山寺是我幼時嬉戲的地方,〈靈籤〉是我最早接觸到的文字;我花了一年時間將一百首籤詩全解出來,雖然無法親自踏查其發生地點,但也正因如此,保全了古早臺灣人的「印象中國」。
關於這百首籤詩,我的寫作分兩大系列,其一是哲學歷史,以哲學思想作為歷史的形上意義,其二是歷史哲學。
《哲學歷史》一共有八位代表性人物,順序是姜太公、鬼谷子、范蠡、孫臏、張良、達摩、呂洞賓、西王母八家。
西王母曾是中國人民的共同信仰,在哲學的陳義由於不是一般人能了解,所以有很多地方被熱心人士「委曲求全」,儘管現在已經很難扭轉印象,但我仍希望盡一份棉薄之力。由於她在五帝時代對中國古文化有重大影響,五帝又是我們的根源,需要較仔細的解釋,以致篇幅無法更緊縮。《哲學歷史》雖是由西王母展開,也只好放在後面。
這八位古人,帶動了中國的形上歷史,他們的思想流傳至今,包括成語、典故、思想模式,不論是兩岸,甚至馬來西亞、新加坡、美、加的華人,仍然處在芝蘭之室中。
本書是〈靈籤〉系列的第一本,其中有古人智慧,也同時藉今人的許多努力方能施設完全,若能讓讀者有所收獲,我只是在歷史因緣中,介紹了人類數千年來的思想文化,如果有什麼缺失,那純粹是我個人的不足。
美國人的由來 黃凡
――一則有趣的臺灣文學
一九五○年代冷戰時期,美國會通過援華後,美軍跟澎湖有了近距離接觸。戰爭期間的年輕大兵,舉止自然不夠莊重;開放的態度,在漢人眼中根本毫無體統,更何況原本就在文化、語言、生活習慣上格格不入。最令人不自在的,是他們迥異東方人的長相──金棕色的頭髮,鳥一般的藍眼珠、凸鼻仔,即便穿著整齊,看起來也是毛茸茸的。
保守的澎湖人,表面上完全看不出對這些美國人有任何反應,但不久之後,人類學家到馬公市東衛村田野調查,意外得到一個新故事──美國人的由來。
採集到這故事的,...
目錄
【代序】
美國人的由來――一則有趣的臺灣文學 黃凡
【前言】
釋儒道三學與臺灣先民
第八十九首〈姜太公渭水遇文王〉
天國反撲――姜太公的十字架
第十八首〈鬼谷子演課〉
鬼谷仙蹤
第五十六首〈范少伯泛舟五湖〉
永憶江湖歸白髮的范蠡
第六十五首〈孫臏困龐涓〉
孫臏和他的壞同學
第四十五首〈張良受書圯上老人〉
張子房的小蝴蝶
第三十一首〈達摩面壁〉
達摩為什麼睡不著
第五十四首〈呂仙枕黃粱未熟〉
哮天犬老咬呂洞賓
第八十六首〈西王母獻益地圖〉
人類的終極之秘――西王母
【附錄一】求籤卜卦的源流
【附錄二】鎮靈籤中不分的儒與道
【代序】
美國人的由來――一則有趣的臺灣文學 黃凡
【前言】
釋儒道三學與臺灣先民
第八十九首〈姜太公渭水遇文王〉
天國反撲――姜太公的十字架
第十八首〈鬼谷子演課〉
鬼谷仙蹤
第五十六首〈范少伯泛舟五湖〉
永憶江湖歸白髮的范蠡
第六十五首〈孫臏困龐涓〉
孫臏和他的壞同學
第四十五首〈張良受書圯上老人〉
張子房的小蝴蝶
第三十一首〈達摩面壁〉
達摩為什麼睡不著
第五十四首〈呂仙枕黃粱未熟〉
哮天犬老咬呂洞賓
第八十六首〈西王母獻益地圖〉
人類的終極之秘――西王母
【附錄一】求籤卜卦的源流
【附錄...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