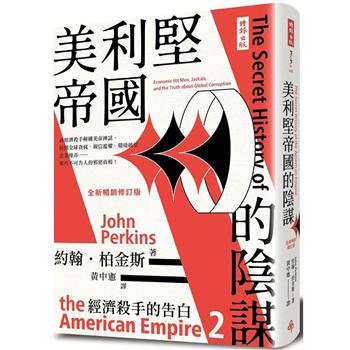緒論
幾年前一個陽光燦爛的初夏午後,我們夫妻倆帶著初生不久的女兒外出野餐。空氣晶瑩剔透,周遭一切如夢似幻。我們坐在草地上,伴著金光萬道的潺潺小溪,餵飽女兒,等她沉沉入睡之後,我拿起裝滿書報雜誌的袋子。在還沒有平板電腦的時代,我總是隨身帶著這個袋子,它裡面裝著許多我沒時間讀的文章,主題包括生態退化、核擴散,還有人人都愛的漫畫。
那天我袋子裡恰巧裝了一本《幻獸辭典》(Book of Imaginary Beings)──阿根廷作家豪爾赫.路易斯.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所著的動物寓言集,也可說是野獸故事集,最初於一九六七年出版。我上一次看到它大約是在二十年前,那天本是無心,順手把它塞進袋子裡,但等我一展卷細讀,卻一發不可收拾。書裡提到舉世最古老詩歌《基爾伽美什》(Gilgamesh)中守護杉樹林的怪獸洪巴巴(Humbaba),形容牠生著獅掌,全身披著堅硬的鱗片,爪如禿鷹,長有野牛角,尾巴和陽具的末端都生著蛇頭。書中也描繪了卡夫卡所想像過的一隻動物,身體如袋鼠一般,但卻長了像人臉一樣的扁平臉龐,只是牠的牙齒表達力很強,卡夫卡覺得牠想要馴服他。書裡還說起智利民間傳說中的「強壯蟾蜍」,生有如龜一般的殼,在黑暗中像螢火蟲一樣閃閃發光,牠極其強健,要殺死牠的唯一方法,就是把牠燒成灰燼;牠瞪眼的威力十足,能吸引或驅逐周遭的一切生物。上面說的每一種動物──再加上其他許多源自世界各地神話傳說,以及一些出於作者本人想像的怪獸,都收錄在小品文中,迷人、怪誕、教人惴惴不安,或是妙趣橫生,有時四者兼具。這本書把人類的想像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呼應並且重塑現實。正如我所說,我沉迷其中,愛不忍釋 ──直到在陽光下打起瞌睡。
等我醒來,不由得想到許多真正的動物其實比想像的動物更奇特,只是我們的知識和了解太狹隘,太片段,沒辦法接納牠們:我們很少去思索牠們。在眼前這個我們要學著稱為「人類世」(Anthropocene)的時代,在這個滅絕和變化一如生命史上任何時刻一樣重要的時代,應該要探究這一點。我腦海裡不斷浮現一個念頭,告訴我:應該在這我只略知端倪的世界裡,更深入探索我們所不熟悉的生命形式,而且我也該把這些探索詳細記錄在一本《Book of Barely Imagined Beings》的書裡。
通常我總會很快就淡忘這種還不成形的念頭,但這回它卻揮之不去。接下來幾個月我陶醉其中,到了不得不採取行動的地步。結果就是各位拿在手中的這本書:可做為二十一世紀動物寓言集題材的素描與研究。
我們很少會想到動物寓言集,即使想到,也僅僅把它們當成中古時代的幻想:寓言集裡盡是怪異而美麗的圖像,用遠道而來的黃金和各色珍貴的顏料,繪製出琳瑯滿目、美不勝收的圖畫。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收藏的十三世紀手稿《艾許摩爾動物寓言集》(The Ashmole Bestiary)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其中一幀圖畫裡,一個紅衣人正注視著他在海中小島上所升起的一小盆火,渾然不知這小島其實是巨鯨的背,同時有一隻巍峨高大的船隻航過,金黃的穹蒼下映著船影。另一張圖片中,許多用黑色勾勒的白頰黑雁以喙垂掛在裝飾藝術的綠、紅、藍喇叭上,這些喇叭其實是樹上的花朵。其說明文字往往和圖畫本身一樣教人浮想聯翩:角蝰(asp,一種毒蛇)會用自己的尾巴塞住耳朵,以免為弄蛇人的笛聲所迷;黑豹是溫和多彩的野獸,牠唯一的敵人是龍;旗魚則會用牠的尖喙戳沈船隻。
不過動物寓言集的內容不僅僅只有如此而已。除了滑稽可笑的圖畫、古怪的動物生態和宗教寓言之外,它們還蘊含了精確的觀察心得:努力了解並傳達事物究竟是什麼模樣。它們無畏(也毫不知覺)於所屬時代知識的限制,只知頌揚各種生物之美。
要徹底說明中世紀盛期偉大動物寓言集的靈感和起源,就不得不提到古代的精彩科學作品,尤其是亞里士多德著於西元前四世紀的《動物誌》(History of Animals),和西元七十七年老普林尼(Pliny)的《博物誌》(Natural History)。另外還得藉助一段稱作《自然史》(The Physiologus)的文字,其中記錄羅馬浩劫(包括一場大概殺死歐洲一半人口的瘟疫)後的動盪歲月。我們必須解釋由這些和其他來源摘錄的文字如何和聖經故事與基督教義合而為一,硬塞進自然史和精神教訓的綱要之中。[一路上還可能會間接提到歐洲黑暗時代的傑作,如約在西元七百年在諾桑比亞(Northumbrian,英格蘭北部)海岸繪製的林迪斯法恩福音書(Lindisfarne Gospels),以北方異教徒編結的動物圖形,融合陽光燦爛地中海東部曼陀羅式的圖案。) ]不過我想探索的卻是其他的事物:一個更古老更持久的現象──比亞里士多德出生前一千多年就已分別出現在埃及和克里特多彩多姿的鳥類和海豚圖像還要更早。
位於南法肖維岩洞(Chauvet Cave)的這些壁畫約有三萬年的歷史,是已知最早的人類壁畫。畫中的野牛、牡鹿、獅子、犀牛、野山羊、馬、長毛象及其他動物,都和當今任何藝術家所畫的一樣唯妙唯肖。我們永遠無法知道這些圖像對它們的創造者究竟有什麼意義,但卻明白這些藝術家下了苦功研究他們的題材,比如他們知道這些動物怎麼隨四時變化。古人類學者伊安.泰德薩(Ian Tattersall)寫道:「這些圖畫描繪野牛在夏日換毛期的毛皮,牡鹿在秋天發情時咆哮的姿態,毛茸茸的犀牛身上有夏天才看得見的皮褶,或者勾勒出鮭魚產卵期間雄魚下顎奇特的突出。的確,對於現在已經絕種的動物,我們只能透過關於牠們的藝術作品來認識牠們。或許和柏拉圖「洞穴隱喻」正好相反的是,我們有時只能在看過動物出現在藝術作品中的影子之後,才能認識真正的動物。而且我們也由印或勾畫在洞穴牆上圖像的手印得知,當時的人不分男女老少,包括嬰兒,都參與了至少一部分發生在此的活動。我們可以看到動物對這些人攸關緊要。同樣的動物種類一再出現,但卻沒有風景的圖案;沒有雲朵、大地、太陽、月亮 、河流、或者植物,地平線或人影也都十分罕見。
這一切都指出一個明顯且重要的事實,我認為即使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那就是在大半的人類歷史中,想要了解並界定我們自己的企圖,和我們怎麼看待和表現其他動物息息相關。表現的手法或許會改變,但對其他生命形式的著迷卻一直持續。比如十六、十七世紀的多寶格就和中世紀的動物寓言集截然不同,它們把真正的動物樣本和奇異動物的片段、植物和岩石結合在一起,為十八世紀更有系統的大自然研究舖路,造就了我們如今依舊在使用的分類系統。但就像動物寓言集一樣,這些多寶格依舊有魅惑我們的力量,它們的德國名稱 Wunderkammern (「珍品收藏室」)就說明了這點。如今我們對珍奇寶貝的喜愛依舊。由Wunderkammern再跨一小步,就來到了網際網路,而後者──幾乎包羅萬象,既是科學的僕人,也是日常的電子動物寓言集。由大烏賊到雙面貓,我們對動物之所知和所不知,牠們能做和不能做的神奇事物,牠們的千奇百怪,都不斷地出現在網路上最常分享的文章和影片上,教我們嘆為觀止。
下面這話似乎有其道理:我們的注意力往往極其短暫,而且雜亂無章,但對於包括動物之內的其他生命形式,卻著迷不已,在每一種人類文化中,這種好奇心都像暗岩下方的泉水一般汩汩湧出。我們或許是恬不知恥的偷窺者,或者熱情的保育人士,或者只是好奇,但卻很少會無動於衷。就像我們的祖先一樣,我們總是有意無意地不斷自問,「這和我,和我的實體存在,和我所期望和恐懼的事物,究竟有什麼關係?」
本書所選的動物,並不是為了要作為世上生物的代表,本書更無意要成為全方位的自然史。在寫作過程中,我雖力求正確,但卻並無意以系統化的概念呈現每一種動物,而是著重在(至少在我看來)牠們美麗有趣之處,以及牠們所象徵、反映,或提升的特質、現象,和問題。 在某些方面,本書的安排就像波赫士想像的中國百科全書《天朝仁學廣覽》(Celestial Emporium of Benevolent Knowledge):
在書中字跡已經模糊的扉頁上寫道,動物分為(a) 屬於皇帝的;(b)經防腐處理的;(c)受過訓練的;(d)乳豬;(e)美人魚;(f)美妙的;(g)流浪狗;(h)包含在此分類之中的;(i)會像生氣那樣發抖的;(j)難以計數的;(k)用極細駝毛筆畫的;(l)以此類推;(m) 剛打破花瓶的;(n)遠看像蒼蠅的。
本書的設想是「aletheiagoria」──就我所知,這是個新造的字,用aletheia這個代表「真相」或者「揭露」的希臘字,來暗示「幻景」( phantasmagoria,在有電影之前的一種幻燈表演)。它意味著(至少對我而言)在更廣大現實中閃爍的「真實」圖像。我嘗試由不同的角度看幾種生存的方式,而且透過「眾多意想不到的並列」,探索牠們和人類(或者我們對自己存在的想法)有什麼雷同或不同之處,以及牠們和我們的異同對人類的能力和問題有什麼樣的啟發。其結果在某些地方有點奇特,而且的確有點勉強。我所追究的一些類比和題外的枝節和動物本身並沒有多少關係.,這是刻意地嘗試,要藉著這些動物來思索,但不只是思索這些動物本身而已。至於所有題外的枝節,也有其主題和脈絡。
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用「眾多意想不到的並列」一語,來描述老普林尼的的《博物誌》,(比如)這書把魚分為「頭上有小圓石的魚;冬天會躲起來的魚;感受到星星影響的魚;某些得付出非比尋常高價的魚。」本書的散文亦然〔約翰生博士(Samuel Johnson)對散文的定義是:隨興之所至的心靈漫步,不合規範、雜亂無序的文章〕。
本書的一個主題是演化生物學(以及它所屬的科學方法)怎麼讓我們得到比光由神話和傳統觀點更豐富更有益的生存本質感受。這不只是費奧多西.多布然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美國遺傳學者)所說的「除非由演化的角度來看,否則一切都說不通」;而且也因為在理解了解釋之後,驚奇和歡喜之情才會油然而生。正如羅伯特.波格.哈里森(Robert Pogue Harrison)說的,「經過了衡量的限制,想像才會發現它真正的自由」;真正測量出華爾騰湖(Walden Pond)深度的,是激進的政治運動人士兼環保先驅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而非他周遭那些只會說湖深見不見底的「實際」人士。梭羅用鉛錘線,確切量出華爾騰湖的深度。用理查.費曼(Richard Feynman)的話來說,「我們的想像力延伸到極限,並不是為了像在小說中那樣,想像並不存在的事物,而是為了要了解真正存在的那些事物。」拜演化理論之賜,這世界終能成為透明的表面,讓人能夠透過它,看到整個的生命史。
書裡的另一個主題是海。各章的標題約有三分之二是海洋生物,這有幾個原因。第一,海洋世界是我們古早的起源,也是到目前為止地球上最遼闊的環境,它覆蓋了地表的十分之七,構成了逾九五%的適居地區。想想美國作家安布羅斯.比爾斯 (Ambrose Bierce)的定義:「海洋,名詞,佔據世界三分之二的水體──而這個世界是為沒有鰓的人類所造。」)然而我們對這片浩瀚的領域之所知,卻遠遜於我們對陸地的了解。要更進一步了解它,是我們的「工作」。一九五七至五八年國際地球物理年,海洋學家表明他們主要的目標就是要研究如何「把海洋深處當作輻射廢棄物的垃圾場」,比爾.布萊森(Bill Bryson)說,再沒有比這話更能說明我們在心理上和海洋的隔閡,至少一直到最近都是如此。近年來,我們才改變了原先視海洋世界為次要的觀點,而逐漸了解它在包括氣候和生物多樣性等地球系統,因此也在我們的命運中,扮演關鍵的角色。也唯有到最近,我們才開始明白,海洋裡充滿了奇形怪狀的生物,牠們並非神話,而是真正的生物,有時甚至意想不到地十分討喜,比如海洋裡有如人一般高而無內臟的生物,生存在只消片刻就會讓我們活活燙死的水域裡,再如海中有酷寒而黑暗的遼闊領域,其中幾乎所有的生物都會綻放光芒,或者海裡生著有意識的智慧生物,可以把牠們的身體擠過寬度只有牠們一隻眼球大小的空間。
人類對海洋影響的規模,結果的嚴重,和未來的希望,請參見卡魯姆.羅伯茨(Callum Roberts)所著的《生命之海》(Ocean of Life)。
貫穿全書的另一脈絡則和人類行為的後果有關。幾年前我赴北極,在暴風雪中的海灘上觀察一群肥嘟嘟的海象。在那次的旅程中,我是勉強夾帶進去的隨員,像偷渡客一樣,混在一群藝術家、音樂家和科學家的考察團裡,乘小帆船前往挪屬斯瓦爾巴群島(Svalbard,英文常以群島中最大的島嶼Spitsbergen為名,稱為斯匹次卑爾根群島),親眼觀察這個地區正在經歷的重大變化,並且思索迫在眉睫的問題 (北極暖化比舉世任何地方都迅速,許多如山鐵證都指出原因在於人類的活動。)
雖然海象在陸地上體型笨重,動作滑稽,但在水裡卻十分靈活而敏感,是我最喜愛的動物之一。說真格的,我女兒之所以能夠降生,歸根結柢,就是靠著當初我在餐巾紙上畫了一頭海象,把她母親騙到手。網際網路上有為數不少的影片,可以看到海象與訓練員一起作體操,或者吹奏低音喇叭,發出非常難聽的聲音,可見得我對這種動物的喜好並非獨有。人們對海象的欣賞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一六一一年就有一隻幼海象被送到英國宮廷裡展示,
國王和許多德高望眾的政要看著牠,嘖嘖稱奇,英格蘭從未見過像這樣奇特的活生物。這牲畜的形狀頗為怪異,而且容易馴服,因此很適合教導。
只是在這種樂趣的背後卻是醜陋的現實。這四百年來,歐洲人先是嘲笑海象,接著又宰殺牠們──出於消遣,但主要也是為了牟利,因此海象(儘管並沒有絕種)遭到趕盡殺絕。英國水手在一六○四年初次見到海象,馬上就發現牠們非但無害,而且富含油脂,還有極好的象牙,這兩者都可賣到好價錢。一六五年,倫敦莫斯科維公司(London Muscovy Company)的船就回到斯匹次卑爾根,整個夏天都忙著殺戮海象,煮沸牠們的油脂製成肥皂,並且摘取象牙。到一六○六年的捕海象季節,他們已經經驗老到,登陸不到六小時,就已經殺了六、七百頭成年海象。
我們這些二十一世紀的遊客,抱著關心環保的胸懷洋洋自得,並無傷害海象之心,真無此意。但在一陣興奮之下,人人都想接近牠們,結果反而使牠們受了驚嚇,紛紛縱身入海,教船長勃然大怒:海象需要休息,而我們卻在搗蛋。雖然我們都出自一番好意(或者我們是這麼想的),但大家卻聯手成了野蠻人,儘管情節還算輕微。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一五七五年寫道:
這裡還可補充一點,是小說家伊恩.麥克伊旺(Ian McEwan) 所述(最先刊在報上,後來收入他的小說集《追日》(Solar) 。記述的是他在次年參加如我們那樣的考察之旅,結果發生的一段混亂。那艘船的寄物處存放了可因應室外嚴寒天候的衣物,結果因為乘客只顧拿自己想要的衣物,而不顧它們屬於誰,使整個寄物處陷入混亂。麥克伊旺問道,如果大家視為靈敏、智慧,而且才華洋溢的人,都不能在寄物處循規蹈矩,那麼怎能指望他們拯救地球?這就如哲學家雷蒙德.蓋斯(Raymond Geuss)所說的,「不要光看人們說什麼、想什麼、相信什麼,而要看他們真正的行動,以及其後的結果。」
是誰說服了[人],讓他以為那穹蒼天體絕妙的運行,那照耀在他頭頂上的永恆燦爛光芒,那教人心驚膽戰而多少世代不斷起伏的浩瀚汪洋,都是為了他的利益,為了服侍他而生?我們能夠如此荒謬地想像這個可憐可悲的生物,連自己的主人都稱不上,暴露在所有事物的攻擊冒犯之下,卻膽敢自稱是這宇宙的主人和皇帝?
只要一想到我們和海象以及我所看過和參與過的其他考察和實驗的經驗,上面這個顯然對《哈姆雷特》有所影響的段落就會浮現在我腦海。它讓我們明白我們對於自己行動的後果是多麼漫不經心,而這也和本書的另一脈絡息息相關。
人類擁有比我們所了解更強力的感官知覺。一個健康的年輕人可以看到三十哩外黑暗中的燭火,人耳可以聽到布朗運動(Brownian motion,一種個別分子的運動)的臨界值。不過,其他生物有遠勝過我們的知覺力量──視覺、聽覺、嗅覺,以此類推。牠們對世界的知覺,在某些方面較我們高明,只是至少在一個方面──意識,所有(或者幾乎所有)其他的動物都遠遠不及我們。難怪我們對人類的意識和認同大作文章。只是如果對於我們與其他動物共有的演化傳承和能力,以及牠們在某些地方怎麼超越我們,能夠有更進一步的體會了解,對於身為人類和其他動物的想法,自當更有貢獻。
侯世達(Douglas Hofstadter,美國學者、作家)說,「我」其實是「幻覺幻想出來的的幻覺」。史賓諾沙則認為「海洋代表上帝或大自然,是唯一的物質,而個人就像波浪,是海的形式。」至少在量子力學的層面,史賓諾沙的直覺可能極其正確:「和你周遭所有事物的連結,就定義了你是什麼人,」物理學家艾隆.歐康奈爾(Aaron O’Connell)如是說。
這裡所提到的這些脈絡,和其他的絲縷,包括我們怎麼理解時間和重視時間的問題,都和一個核心問題息息相關:身為人類世的公民,我們對現代和未來的世代究竟有什麼樣的責任?中世紀的動物寓言集既描繪了真實的動物,也勾勒了我們現在明白是出於想像的動物,故事集裡充滿了寓言和象徵,因為對中世紀的心靈而言,每一種生物都是宗教和道德教訓的表現,至少自休姆和達爾文之後,我們許多人已經不再相信這一套,但在我們透過科學和科技,更不用說藉著我們人類的數量,重塑創世紀之時,真正能繁榮演化的生物,就會越來越符合我們的價值觀和關懷目標。因此啟蒙運動和科學方法使得我們得以創造一個真實的寓言世界,因為我們會以我們的價值觀和優先順序來重塑它。或許哲學家約翰.格雷(John Gray)說的對,唯一真正的歷史法則是諷刺的法則。本書是人類世動物寓言集的一個嘗試,書中所描述的動物都是真實的,都在不斷地變化發展,而且往往已瀕臨滅絕,它要提出的問題是:我們應該重視什麼,為什麼我們沒有重視它們,以及我們該如何改變。
波赫士在《幻獸辭典》中,描繪了阿包阿庫(A Bao A Qu)這種有點像魷魚或烏賊的生物,只有在人類進入牠所住的黑塔,想要奮力爬上塔頂時,牠才會醒來:
……唯有在跳上螺旋樓梯時,阿包阿庫才會清醒,牠緊跟在訪客的腳跟後面,靠在旋轉梯的梯級外緣,被世世代代追尋者踩踏之處。每上一梯級,這生物的顏色就越濃艷,牠的形狀跡近完美,牠發出的藍光也益發明亮。但牠一直要到階梯的最頂級,當攀登者達到涅槃,其行動不再有影子之後,牠才會達到終極的形體,否則阿包阿庫就會躊躇不前,彷彿麻痺了一樣,牠的身體無法完整,藍色光芒黯淡下來。這生物在無法達到完整形體之時就會受到折磨,發出幾乎聽不見的呻吟,就像絲綢的沙沙聲。牠的壽命短暫,因為當遊客爬下來之後,阿包阿庫就翻滾跌下最底下的幾階,在那裡耗盡體力,喪失形狀,等著下一個訪客。
我們可以用許多方式闡釋波赫士的奇特故事,或者根本不去闡釋它。在這裡我稱之為寓言,並且採用我簡略的定義:除非我們發揮想像力,在接納我們自己生存的現實之外,也接納其他生命形式的現實,否則我們就沒有達成主要的任務。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卡斯帕.韓德森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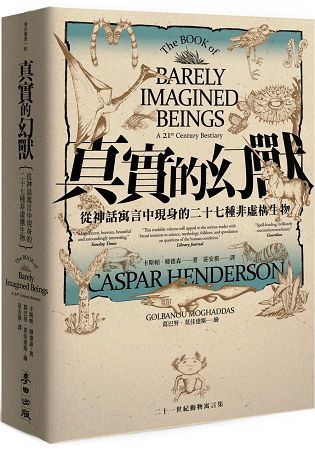 |
$ 190 ~ 540 | 真實的幻獸:從神話寓言中現身的二十七種非虛構生物
作者:卡斯帕.韓德森 / 譯者:莊安祺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17-09-14 語言:繁體/中文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真實的幻獸:從神話寓言中現身的二十七種非虛構生物
作者初試啼聲之作,受波赫士奇作《想像的動物》啟發,有感於動物在演化過程中的奇異之處遠超人類想像,沿用並改造源自古希臘、盛行於中世紀歐洲的「動物寓言」(bestiary)體裁,以地球上真實存在的生物取代神話、歷史、文學中的幻獸,以科學研究取代宗教色彩,以環保與動保意識取代一般道德教訓。在二十七種真實存在的幻形生物面前,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吉爾伽美什》史詩裡獅掌鷹爪、全身覆蓋角質鱗皮的杉樹林守護者洪巴巴、古埃及神話的人面獅身獸、卡夫卡筆下身如袋鼠、扁臉幾似人貌,透過牙齒傳達訊息的《變形記》大蟲,不過是想像力貧乏的拼貼動物。本書依演化生物學的重要性,挑選二十七種代表生物,流暢地從演化生物學漫談歷史、軼事、小說等人文領域,不僅富含與自然史及生物演化相關的科學知識,還有科普書少見的歷史、人文深度。作者以二十七種生物作為知識之窗,用蒙田式的隨筆寫作歌頌生物多樣性,帶領讀者探索人類認識、闡述生物與生命的世界旅程。
作者簡介:
卡斯帕.韓德森Caspar Henderson
作家、記者,文章散見於《金融時報》、《獨立報》、《新科學人》等報章雜誌,定居英格蘭牛津。曾獲路透社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環境新聞獎。二○○九年,以《真實的幻獸》寫作計畫獲英國皇家文學會非小說獎。
譯者簡介:
莊安祺
台大外文系畢,美國印地安那大學英美文學碩士。譯作等身。包括:《人類時代》、《感官之旅》、《Deep Play心靈深戲》、《艾克曼的花園》、《氣味、記憶與愛欲:艾克曼的大腦詩篇》、《愛之旅》、《我的大象孤兒院》、《創作者的日常生活》、《美味不設限》、《巴黎人》、《萬病之王》等近百部。
TOP
章節試閱
緒論
幾年前一個陽光燦爛的初夏午後,我們夫妻倆帶著初生不久的女兒外出野餐。空氣晶瑩剔透,周遭一切如夢似幻。我們坐在草地上,伴著金光萬道的潺潺小溪,餵飽女兒,等她沉沉入睡之後,我拿起裝滿書報雜誌的袋子。在還沒有平板電腦的時代,我總是隨身帶著這個袋子,它裡面裝著許多我沒時間讀的文章,主題包括生態退化、核擴散,還有人人都愛的漫畫。
那天我袋子裡恰巧裝了一本《幻獸辭典》(Book of Imaginary Beings)──阿根廷作家豪爾赫.路易斯.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所著的動物寓言集,也可說是野獸故事集,最初於一九六七...
幾年前一個陽光燦爛的初夏午後,我們夫妻倆帶著初生不久的女兒外出野餐。空氣晶瑩剔透,周遭一切如夢似幻。我們坐在草地上,伴著金光萬道的潺潺小溪,餵飽女兒,等她沉沉入睡之後,我拿起裝滿書報雜誌的袋子。在還沒有平板電腦的時代,我總是隨身帶著這個袋子,它裡面裝著許多我沒時間讀的文章,主題包括生態退化、核擴散,還有人人都愛的漫畫。
那天我袋子裡恰巧裝了一本《幻獸辭典》(Book of Imaginary Beings)──阿根廷作家豪爾赫.路易斯.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所著的動物寓言集,也可說是野獸故事集,最初於一九六七...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卡斯帕.韓德森 繪者: 葛巴努.莫佳達斯Golbanou Moghaddas 譯者: 莊安祺
- 出版社: 麥田 出版日期:2017-09-07 ISBN/ISSN:978986344482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512頁
- 類別: 中文書> 科學> 生命科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