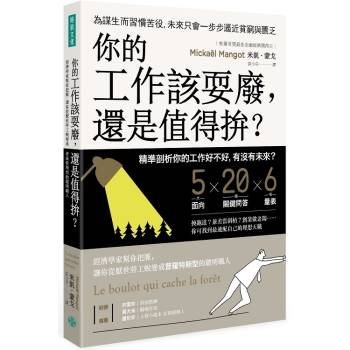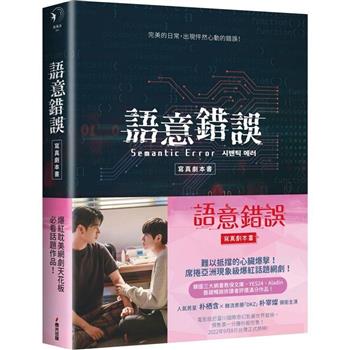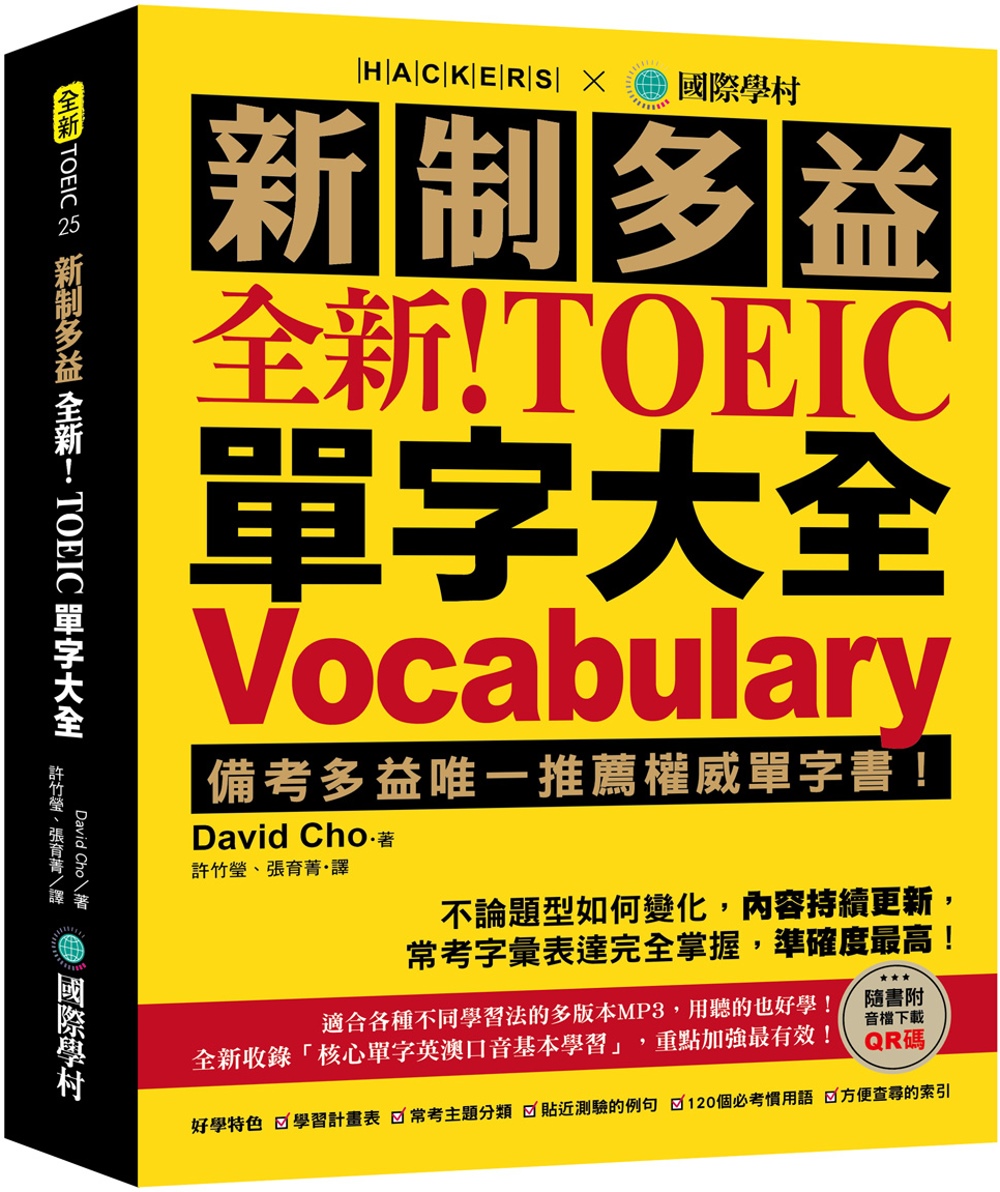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2 項符合
卡洛琳.艾爾頓的圖書 |
 |
$ 336 ~ 379 | 醫生,也是人:資深心理師揭露白袍底下的情感掙扎與脆弱人性 (電子書)
作者:卡洛琳.艾爾頓(Caroline Elton) / 譯者:林麗雪 出版社:木馬文化 出版日期:2025-04-09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普通級/ 初版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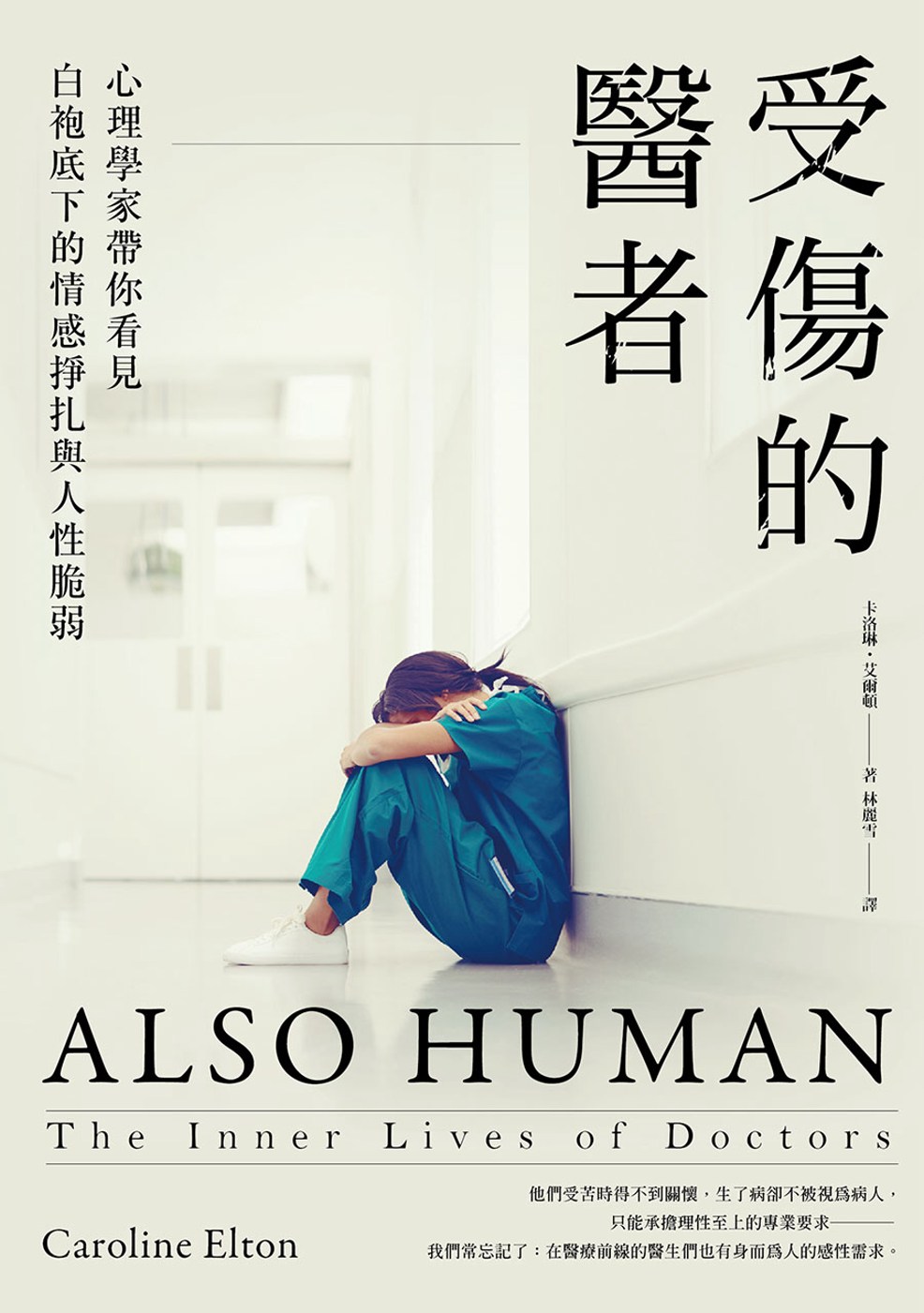 |
$ 160 ~ 378 | 受傷的醫者:心理學家帶你看見白袍底下的情感掙扎與人性脆弱 (電子書)
作者:卡洛琳‧艾爾頓(Caroline Elton) / 譯者:林麗雪 出版社:木馬文化 出版日期:2020-12-30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普通級/ 初版  1 則評論 1 則評論  共 10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0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卡洛
|
 卡洛是愛爾蘭卡洛郡的一個城鎮,為卡洛郡的郡治所在地。總人口23,030人。卡洛位於巴羅河東岸,距首都都柏林72公里。
卡洛是愛爾蘭卡洛郡的一個城鎮,為卡洛郡的郡治所在地。總人口23,030人。卡洛位於巴羅河東岸,距首都都柏林72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