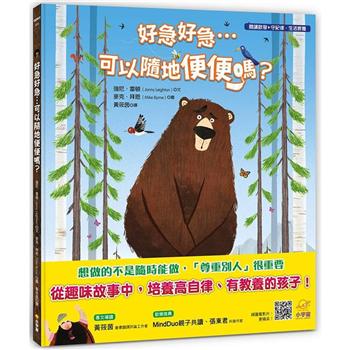就如《西線無戰事》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
《馬特洪峰》是描述越戰最撼動人心的戰爭經典
他們在戰爭這條真實的等高線上集合
並讓血洗去所有殘存的童稚與純真
餘下的究竟是男人
還是殘破的男孩?
***New York Times暢銷書
***AMAZON讀者五顆星佳評推薦
***2010年亞馬遜書店百大選書
***IndieBound-4月推薦榜TOP 2
《馬特洪峰》可能是越戰小說中最富人性與人生哲理的一部。作者卡爾.馬藍提斯是戰爭小說界剛出道的新手,但「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一鳴驚人。
由於作者越戰期間服役海軍;因此,他對書中海軍陸戰隊的各種作戰行動、形形色色的軍人心態、長官與部屬之間的複雜關係自是瞭若指掌。更重要的是,在幾乎以親身經歷與實戰經驗描述戰爭殘酷的同時,他將越戰結束後數十年歲月的人生體驗與對人性的深刻觀察,一併融入此書,終讓此書成為可歌可泣的一部巨著。
《馬特洪峰》是新銳小說家Karl Marlantes的第一部創作小說,自出版後已獲得各界好評,包括《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的封面報導,也榮登「精裝書暢銷排行榜」(hardcover bestseller)第七名。此書除了已在美國出版外, 也將於今年秋季在英國出版,目前並有義大利出版社積極洽談中。
沿襲了轟動文壇的描述二次大戰小說——美國小說家諾曼.梅勒 (Norman Mailer)著作的《裸者與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和詹姆士.瓊斯(James Jones)著作、並改編成電影的《紅色警戒》(The Thin Red Line),《馬特洪峰》是另一部描述越戰歷史、文筆強烈且撼動人心的戰爭鉅著。
這部小說的背景是1969年美國在越戰期間關鍵的三個月,描述一位年輕的海軍上尉Waino Mellas和他同連的戰友們,在越戰中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他們年紀輕輕就被丟置在越南叢林野戰中,被迫在槍林彈雨中展現男子氣概奮戰到底。阻擋他們勇往直前的,不單單只有北越共軍,還有雨季的豪雨和爛泥、吸血的水蛭和凶猛的老虎、疾病和營養失調。除了抵抗這些外來的危險處境,更令人驚駭的是,他們發現最大的阻礙竟然來自戰友彼此:種族歧視、互相競爭的企圖心、和故意欺瞞下屬的上級軍官。但當全連隊員發現已被數目龐大的敵軍圍困且無法逃脫,這群年輕的陸戰隊弟兄身陷這場赤裸裸、消耗殆盡的戰役格鬥中,這驚恐的經歷也殘酷地改變了他們的一生。
《馬特洪峰》是由榮授高階勳章海軍退伍軍人卡爾.馬藍提斯,花費三十年光陰寫下的嘔心瀝血之作。他將越戰可怕、驚駭的作戰經驗,透過深刻而真實的描述,活生生呈現在世人眼前。這部小說,真可稱得上是當代戰爭文學的經典鉅著。
作者簡介
卡爾.馬藍提斯(Karl Marlantes)
畢業於耶魯大學,也是牛津大學羅氏獎學金的研究生(Rhodes Scholar at Oxford University)。他在越戰期間服役於海軍,曾獲頒多項榮譽勳章。《馬特洪峰——一部關於越戰的小說》是Karl Marlantes首部創作的小說。
譯者簡介
高紫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畢業。目前為全職翻譯,從事翻譯工作近六年,熱愛翻譯、閱讀,對戰爭文學與歷史文學更是情有獨鍾。譯有《甘地與我》(左岸文化出版)。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