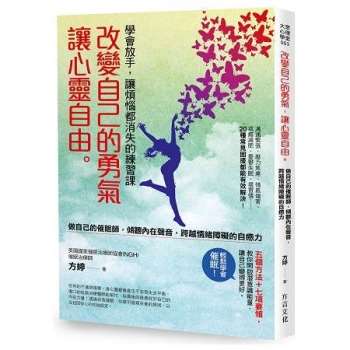她――是老人,也是女人;
而在充滿歧視與壓迫的社會中,她,成了殺手。
韓國女性小說新流派
以犀利筆鋒,一刀剖開「敬老」二字最醜陋的一面――
「老」是什麼?
是身邊的人事物都在消失,只有自己還在原地。
是被大眾遺忘,是受年輕人歧視,是被世界認為無用。
老,是我無法直視的鏡中倒影。
殺手爪角,今年六十五,從事取人性命的工作已過四十載。
從小寄人籬下的她務實地遵守著儉樸的生存守則,並遵照亦師如父的男人「流」的忠告――「不要製造必須守護的東西」,平靜地生活著。
要說殺手最大的危機是什麼?不是失敗,不是樹敵,而是變老。
時間流逝,她開始感到體力的變化,變得易忘事,也逐漸多愁善感。傳奇殺手的利爪變鈍,變得無用。以為身邊一切都會和時間一同消逝,一無所有的她,也將一無所有的走到生命盡頭。
然而,這樣的人生因為一次相遇,產生巨大改變。
為了留住那絕無僅有、特別耀眼的瞬間,她第一次盡全力去活――
因為你是女人,受到侮辱是常有的事,必須置之不理。
因為你是老人,沒有用處,年輕人一定會看輕你。
因為你是女人,又是老人,自然被剝奪了名字,也被抹除了活在世上的資格――
然而,她依舊想抵抗這樣的世界。
名人推薦
文字工作者 臥斧
作家 陳又津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陳佩甄
政大臺文所副教授 崔末順
換日線專欄作家 彭紹宇
作者簡介:
具竝模(구병모)
一九七六年出生於首爾,慶熙大學國文系畢業。曾獲第二屆創批青少年文學獎,三十九屆今日作家獎與第四屆黃順元新進文學獎。在台灣曾出版《魔法麵包店》(天培文化。2013),及短篇小說合輯《致賢南哥》(時報出版,2019)。筆鋒穩健,故事極具張力,劇情流暢。善於描寫社會百態,並以獨樹一格的犀利角度切入問題所在。
原書名為「破果」,取其字典定義,一是指壞了、破掉的果實;一是指十六歲、正值青春年華的少女。書中作者以火花、果實短暫絢爛美好過後消失的瞬間,比喻人生中最燦爛的年華一旦老去,就如黯然失色的煙火灰燼,或腐爛於冰箱、一坨散發酸臭味的果物。然而作者更想藉由爪角控訴這個對年老者――尤是年老女性不友善的社會。
譯者簡介:
馮燕珠
新聞系畢業,曾任職記者、公關、企劃。某天毅然辭去工作,一個人赴韓吃泡菜進修。回國後踏入翻譯界,翻劇也翻書,一切得來不易,所以格外努力經營自己的「譯」界人生!工作聯繫:yenchu18@gmail.com
章節試閱
【爪】
週五晚上的電車通常都是如此,人們有如超越貼合度的軟體動物,用吸盤吸附著彼此。素不相識的身體之間即便只有一張紙的空隙,也夠讓人謝天謝地了。每當有人開口說話或吐氣,夾雜肉的腥膻、大蒜、酒臭的味道,也同時朝頭頂升起,讓人忍不住憋住氣強忍。但是,那氣味道也是昭告著五日的勞動已然結束,現下是可以安心的時間。至於明年或是下個月、甚至下星期的此刻是否也能安然搭上電車的不確定性,此刻暫時都先收起。到了下一站,車門打開,一群勞動者傾瀉而出。他們的臉上堆滿極高的疲憊和苦悶,心裡充滿渴望,只想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家,將溼透的衛生紙般的身體往床上一拋。
這時,她走進來了。
象牙白的毛呢帽蓋住銀灰色的頭髮,身著碎花圖案襯衫,外罩簡樸的亞麻外套,下身是黑色直筒褲。這個女人手上掛著中型的短柄駝色波士頓包,實際年齡六十五歲,但臉上皺紋的數量和深度,使她看起來好似將近八十歲,身型姿態和衣著打扮並未讓人留下特別的印象。在電車上無數的老年人中,會使眾人在一瞬間將視線投向某一人的理由,通常是因為那人抱著一堆收集來的舊報紙,從列車最後一節車廂來來回回打量架上有無遺留的廢紙,不時碰撞站著的乘客的肩膀。又或是那種穿著紫色點點印花老爺褲和橡膠鞋,一進車廂就把散發新榨芝麻油和生薑味的大包袱放在地上,大刺刺妨礙通行,還理所當然就地蹲坐,「哎喲!哎喲!」呻吟,一副馬上就要昏厥的模樣――直到終於有人不得不站起來讓座。還有一種類型相反的老婦人。她們有別於一般年長女性常見的短髮,留著一頭長及腰的直髮,也不戴帽子,皮膚光滑白亮,用過白的粉底不熟練地遮蓋綻放在臉上的老人斑,顫抖的手用力過度畫出的眼線有如波濤。更雪上加霜的是,如果嘴脣還塗了大紅脣膏或穿著粉嫩色調的小洋裝,就更引人側目。也許直到她下車眾人的視線都會聚集在她身上。如果說前者單是存在本身就讓他人立即感到不快,那麼,後者就是因為與現實的不協調而讓眾人困惑。不管哪一種,其共同點都是讓人不想深入了解。
由此看來,她像是人們眼中有風度、有教養、值得尊敬的典型年長者。不會一上車就一手扶著直不起的腰、一手抓住門邊的扶把呻吟,而是直接走向已座無虛席的博愛座。她不會主動挑剔最近年輕人的態度,就像一般的中產階級老人,無過之也無不及的衣著打扮:從頭到腳雖非名牌,但也不顯破舊。多半是在東大門市場或自家附近量販賣場購入,不然就是在百貨公司頂樓特賣會場撈到還可以搭配的單品。這樣端莊的裝扮才不會給年輕人帶來視覺上的汙染。她也不會全身成套的登山裝加各種運動裝備,滿臉通紅、目中無人地放聲高歌。無論在什麼場合,她都能自然融入其中,像是原本就在那個場景中的某第二十名臨時演員。她對於照顧孫子孫女的晚年勞動並無倦意,讓子女成家立業,身體力行勤勞節儉的動作,渾身散發著以養老年金度過游刃有餘的晚年之氛圍。車上的人個個戴著耳機,各自注視自己手機的螢幕,在洶湧的人流中蜷縮著身體。他們很快就會忘了彼此之間曾有個老人出現,就像沒分類的廢紙一樣很快從意識中去除――又或者打從一開始就未曾意識到有那個人存在。
到了下一站,一個拄著枴杖的老人站起身,彷彿要把五臟六腑吐出來那樣邊咳痰邊下車。她馬上坐進空位,拉下帽簷,從包包拿出人造皮革裝訂、附拉鏈的聖經。她把聖經放在膝蓋上,攤開,用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的讀。這種老人的姿態在電車內已是司空見慣,並非異類,也不新鮮,只要別猛地抓住陌生人的胳膊,灌輸什麼不信耶穌者會下地獄的話就好。老年人往往在陸續聽到周遭不幸的噩耗後會開始依附神,在車上讀聖經或佛經是習以為常的景象。不過,若拿出論語或孟子之類的書,感覺就是想展現高尚的知性,或帶給他人與眾不同的衝擊。若一個老婦人手上的書寫了「柏拉圖」或《資本論》,甚至黑格爾、康德、斯皮諾莎之類的書名,想必更會招致人們的驚訝與懷疑:妳真的看得懂嗎?
所以,舉手投足既不特別,也不惹人反感,正符合了眾人心目中的標準值――但與實際平均值無關――不吸引任何人注意的她低著頭,彷彿快碰到膝蓋,像要把放大鏡內擴大的字挖出來似的讀著。突然間,她的視線越過眼鏡,注視著對角線的位子。
一個五十多歲男子的背影看起來似乎在打盹。頭髮猶如錯過染色時機一樣變得半白,他穿著褐色皮外套和黑色西裝褲,手腕掛著一個有提繩的手拿包,裡面似乎裝了各種資料和紙幣,塞得鼓鼓的,黑色Ferragamo皮鞋上的磨損和刮痕十分顯眼。他抓著把手,身體隨列車晃動,而她則目不轉睛地看著他。
站著打盹的男子肩膀突然抖了一下,或許是為了掩飾從睡夢中醒來的尷尬,他竟用手指戳了戳坐在面前椅子上一名女子的額頭。女子眼睛瞪得大大的,抬頭瞥了他一眼,皺皺眉頭,隨即又低頭滑手機。於是男子更用力地戳起女子的額頭,連續不斷地戳。周圍的人起先以為女子是男子的女兒或是妻子,但女子接下來的反應讓大家發現:原來這兩人不認識。
「大叔,您這是在做什麼?」女子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問。
男子則語帶嘲諷的說:「大叔?妳這丫頭眼睛到底有沒有睜開?妳這樣對嗎?在老人家面前還給我裝作沒看到、低頭滑手機。」
周圍頓時起了騷動,年輕女子壓低了聲音說:「老爺爺,不好意思,我懷孕了。」聽到這話,周圍的乘客和讀著聖經的老婦人不約而同,反射動作般將目光射向那女子的肚子,但實在看不出那件娃娃裝上衣裡的肚子是不是真的凸了出來,只能說,從臉部和整個身形來看是浮腫的。
男人乾咳了一下,提高音量,「最近的年輕人連結婚這種事都自動放棄,也不生孩子,懶得履行義務,只有在想要舒舒服服的時候才會說懷孕。不管是桶仔雞還是豬腳,有什麼就吃什麼,胸部和肚子裡的是肥油還是孩子,我看妳自己都分不清楚吧?講白一點,這世上就妳一個人懷孕嗎?就妳一個人要生孩子?」男子每說一句就戳一下女子的額頭,女子甩開頭,想躲避他的手指,但男子沒有停下動作。女子環顧四周,希望有人可以出來幫她,但旁邊坐的中年男子都縮著脖子,低頭假寐。
女子用力揮開男子的手,大聲地說:「為什麼放過其他男人?女人好欺負是嗎?我不是說我懷孕了嗎?」
男子瞄了瞄周圍,沒有一個人出來為女子仗義執言,於是他乾脆豁出去了,「都是妳這女人在說鬼話,誰叫妳要講什麼懷孕了這種唬爛啊?長輩在講話時就要給我恭恭敬敬地回答。」男子加重手指的力道,年輕女子的後腦杓因而撞到車窗,雖然應該不怎麼痛,但她開始啜泣。
坐在對面粉紅色博愛座上一個五十多歲的婦人站起來,拍了拍男子的肩膀,「老先生,您坐這裡吧。」男子假裝拗不過婦人,嘴裡嘟嘟囔囔的,卻過去一屁股坐下,把手拿包抱在胸前閉上了眼。婦人走近滿臉屈辱的年輕女子,輕輕拍著她的肩膀,「小姐……啊不,我說孩子的媽,別哭了,何必為了這種事情哭呢?都是要當媽媽的人了。」說到這裡,婦人刻意把音量壓低,「不是所有老人都那樣,妳也不要太難過了,像那種還不太算老人的大叔只有在需要時才挑……」這時,電車放慢速度,車內廣播說快到下一站,年輕女子拿著皮包,站起來咆哮。
「大家都看到那個人做了什麼,現在才來說不是所有老人都那樣,又有什麼用?」
手拿包男子才剛坐下,應該不可能那麼快就睡著,卻裝作沒聽見似的,依舊閉著眼睛。年輕女子不知是正好要在這一站下車,還是為了擺脫剛才的窘境,總之她不管婦人的安慰,自顧自的下車了。列車關上門,那名五十多歲婦人猶豫了一下,坐在年輕孕婦空下的座位。冷眼旁觀的人們或許會多瞥一眼那個閉上眼睛的手拿包男子,但很快就會忘記剛才的騷動。老婦人也再次垂下眼神,注視著攤放在膝頭的聖經。她的行動和身上的裝扮都不顯眼,這是一切的起點。對剛才的騷亂置身事外,她並沒有罪惡感,就算那個五十幾歲的婦人沒有挺身而出,她也不會站出來,只會默默地看著年輕孕婦狼狽的面容和淚水。
就這樣又經過了五個站,車內響起即將到站及轉乘資訊的廣播,手拿包男子睜開眼,站了起來,老婦人也把聖經闔上,放入皮包內,放大鏡則塞到袖子裡,也一同起身。男子站在車門前,而她在男子身後,保持著不會靠得太近但別人也插不進來的距離。
車門打開,有如掀開充滿了壓力的電鍋活塞。車門與月臺閘門的位置有點錯開。這是轉運站常見的狀況,人們互相推著彼此的背後下車。雙手拎著大包小包的中年婦女們,為了爭奪車上可能有的空位,不顧車內的乘客還沒全部下車,立刻本能地扭動身體,爭先恐後想擠進車廂,結果弄得車門口亂成一團。這時男子突然停下腳步,夾著手拿包的那隻手抱著胸一動也不動,不管下車的乘客或要上車的人都推擠起擋在車門口的男子,他被人們推來推去,最後被推了下車。
喂!搞什麼啊!讓一下!月臺上的人盡可能避開男子,從旁邊經過,但還是有人無可避免地會撞到他的肩膀或背。一名身材高大的青年用單肩背著大大的運動背包,急急忙忙走向轉乘區間。他側身想閃過男子,但運動背包的一角仍「啪!」的一聲撞到男子的頭。「啊!對不起!」青年一邊道歉一邊回頭看著對方,男子卻在瞬間以抱著手拿包的姿勢趴倒在地。背包青年頓時面如死灰,一臉「不是我!」的表情環顧四周。其他人臉上雖然露出些許擔心,也只是瞄一眼就走了,即使有人暫時停下腳步,也並未對青年伸出援手,僅維持一定的距離觀望。他們的目光似乎一致在譴責青年的不小心,要他負起責任。青年面對這突如而來的不幸與災難,別無選擇,只好蹲下來敷衍地問道,「大叔,您還好嗎?」並搖晃男子的身體――這下子他才驚覺事態非比尋常。站務人員和替代役男跑過來,將倒在地上的男子翻過身,他發青的臉上是兩顆擴散的瞳孔,瞳孔內宛如幽暗的隧道,倘若走進去,彷彿將會見到世界的盡頭。
而因為男子的身體被翻轉成正面,臉部朝上,所以大家還沒發現背後皮夾克上兩道乾淨俐落的刀痕。
她在女厠的最後一間,用大量衛生紙擦去約兩根手指大的匕首上殘餘的毒液,接著把變色的衛生紙丟進馬桶裡沖掉。剩下的殘餘物等回到家再戴上手術用手套,徹底清洗一次。因為那是會滲入血液、短短數秒內使人神經麻痺的氰化鉀液體。因此,她在下手時非常小心。尤其最近她患了手抖症,在使用裝備時都必須非常謹慎。她把放大鏡蓋在匕首上,鏡片從兩側被厠所內照明和金屬反射,閃閃發光。在那閃光被門另一頭正在洗手或講電話的女孩發現前,她迅速將之放進包包、緊緊扣上。
從女厠出來後,她走向地鐵的出口,轉身與一群男子驚險地擦身而過,差點被撞倒。兩、三個穿著亮橘色上衣的救護員一次跳下四、五級臺階,飛也似的越過驗票口,經過時揚起塵風的氣勢,讓外套的前襟隨之晃動。
當你在紛擾的場合結束作業、越過轉角時……
放慢速度,不要貼著牆走,要像畫一個實實在在的圓那樣往外繞行。不然,若和迎面而來的人撞在一起,把身上的東西都摔出來,那該怎麼辦?難不成要告訴別人「證物全都在這兒,請拿走」嗎?
她腦海中馬上浮現說這句話的那個人,那人的表情宛如昨日一樣清晰。她隨即勾勒出一條盡可能複雜的回家途徑。出去,經過一個街口,就有個公車站,在那裡隨便坐一輛公車,離這裡越遠越好,再到其他路線的地鐵站下車,一定要繞遠路,畫出最大的軌跡,繞過如掌紋般展開的道路,只要還在體力允許範圍。她以緩慢的步伐走向出口,向著從上降下到地面那燦爛的黑暗前進。
【無用】
大概兩、三個月就會有一次防疫作業,當天早上,一切準備就緒後,她會像執行什麼虔誠的儀式那樣把狗兒無用拉近膝蓋前。
雖然經常忘了餵食或幫牠洗澡,散步的次數明顯不足,但是無用對這樣的生活似乎沒有什麼不滿,還是很聽主人的話,果然跟一般的狗很不一樣。這一人一狗都是上了年紀才相遇,因此對彼此都沒有特別牽掛。主人回來時,無用還是會跑到玄關禮貌地搖著尾巴迎接,但牠不會撲到主人身上。只是連這動作都不做,似乎連同居者最基本的禮儀也失去了。簡單生硬的問候結束,主人身上好像散發著火藥或化學藥品的味道……更別說要是聞到血腥味,牠還會哼哼唧唧。不管藥品的味道是香甜或不好聞,都可能讓牠陷入迷惑、打轉或吠叫。然而無用無念無想,總以達觀的姿態繞著主人打轉。因為不放心上,所以她反而認為這傢伙最適合自己。爪角經常這麼想。不過不管怎麼說無用這個名字好像取錯了,其實牠相當徹底地掌握了主人的心理,知道什麼時候該來、什麼時候該走,維持最適當的距離。這孩子如果被其他人撿到,也許會成為更有用的寵物犬吧。
她摸了幾下無用的頭,讓這傢伙靠近膝蓋坐著,接著轉向東邊,說道。
「看好,窗是開著的。」
無用的頭轉向她手指的方向,洗碗槽前的小窗朝外開著,那個空隙如果硬擠,無用的身體是可以勉強通過的。那個小窗也是在開始飼養無用之後她特別找裝潢師傅加裝的,並未上鎖,所以只要輕輕一推就能打開。如今,或許有人認為她大勢已去,已不算一級防疫者,不會有人想進入家中搜索或是裝設陷阱,但因為她外勤頻繁,雖不會在一個地方停留太久,依舊隨時將門牢牢鎖好,一根針的縫隙都不容出現。這是她長久以來的習慣。
但在與無用一起生活後不久,她開始讓窗戶一直開著,即使暴雨或寒流來襲會暫時關上,但不會上鎖。之前為了提醒自己每天早上要開窗,還特別寫了小紙條貼在冰箱上。如今開窗已成為反射動作。她在無用面前做了好幾次推開窗戶的動作,並再三確認,
「絕對不可以忘記,雖然一直這樣反覆講你聽了會厭煩,但那一天總是會來臨。」
無用坐在不習慣擁抱的主人膝上,鑽進她懷裡看著。
「如果有一天我沒回來,你就從這裡出去。看到了吧?只要輕輕推一下就能打開。如果苦等不會回來的主人,最後餓死,那會很麻煩的。不管是要去找人討食或去翻垃圾充飢,總之你必須出去,並繼續活著,只要別被賣狗肉的抓到就行。」
無用不知是聽懂了或是從她聲調的高低判斷出了什麼,一直抬著頭愣愣地看著她。
「還有一件事,或許比我不再回來還容易理解:如果有一天早上你醒來,發現我躺著不會動,連用腳推我或狂吠我都沒有反應,你就從這裡出去。不是要你出去找人來幫忙,那個時候我應該已經死了,但你要活下去。如果打不開,而你餓了,就吃我的屍體,我不會在意。如果那樣可以對你有點幫助的話。但總有一天屍臭會傳到外面,或是有蟲子沿著排水管爬進來,就會引起別人注意。那些人進來後看到你,會把你抓去安樂死。他們會有很多理由,例如啃食主人屍體的狗不能活著,或是認為你吃了腐壞的肉會把細菌或傳染病傳給人類……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你老了,所以不會有人想照顧你。」
這樣的慣例與平時大同小異,靜靜感受那股平靜在體內蔓延。她的手輕輕地掃過無用的背,無用以溼潤的鼻子湊上她的下巴磨蹭,代替回答。
「其實不一定是狗,對人也一樣。老人是無法以健全的精神度過餘生的……老人容易感染疾病,又經常帶著病走動……誰也不能代替別人承擔,對所有人都一樣。就算不能好好照顧你,我也不希望將你落到那樣的處境,這樣我即使死了也不會安心。因此無論何時,只要到了那時,你就從那裡出去,不管去哪裡都好,知道嗎?活著,在被歸類為難以處理的廢棄物之前,要活著。」
她已經想不起確切是何時把無用帶在身邊、並為牠取了這個名字,只記得第一次見到時牠就並非嬌小可愛的模樣,不是任誰都會二話不說把牠帶走。不過,牠現在的外貌看起來和當時並沒有什麼不同,也許她是認為沒有人會把牠帶走,所以就撿回來了。她無法回溯當時的經過細節,但當時撿回這樣一隻活體動物產生的困惑,以及竟在衝動之下做出毫無計畫的行動的狼狽感,至今仍非常鮮明。
她隨時提醒無用,即使這兩種情況發生的機率都很高,但在實際發生之前,她仍會一如往常與牠應對。睡得好嗎?我去去就回。一人一狗一天說不到十句話,大部分時間只是相互凝視,但不可避免依舊會說這樣的話――不要到處亂尿,到浴室去尿。吃吧,喝吧。去散步回來了嗎?別亂叫,那個不是壞人,是來檢查瓦斯的,是送貨的,送你的飼料來的。她平常會對無用說的大概就是這些。她沒想到家裡除了自己外還存在某種生物,甚至會與牠對話。她也沒料到當家裡有個什麼在等著自己時,回家的腳步會變得急促,甚至還會因擔心回不了家而焦慮。她沒想過這樣的日子會再次出現,在將無用帶回來之前,她完全沒有想到。
我去去就回。
這句話……有人說過不要說這句話,而且是背對著說。
不知道是叫人不用回來,還是因為回來是理所當然,所以無須贅言,她連問的勇氣都沒有。「去去――不回」代表的是防疫失敗的結果,想來對方是不抱任何期望。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釋為有著一去不回的覺悟。不管對方的想法是什麼,對她來說:「去了一定會回來」有助於她確信自己會成功完成防疫作業、平安歸來,所以她無法放棄這離開前的道別。於是她只好望著對方的背影,無聲地說,我……去去就回。神奇的是,明明沒有發出聲音,他卻總是背對著她擺擺手。
【爪】
週五晚上的電車通常都是如此,人們有如超越貼合度的軟體動物,用吸盤吸附著彼此。素不相識的身體之間即便只有一張紙的空隙,也夠讓人謝天謝地了。每當有人開口說話或吐氣,夾雜肉的腥膻、大蒜、酒臭的味道,也同時朝頭頂升起,讓人忍不住憋住氣強忍。但是,那氣味道也是昭告著五日的勞動已然結束,現下是可以安心的時間。至於明年或是下個月、甚至下星期的此刻是否也能安然搭上電車的不確定性,此刻暫時都先收起。到了下一站,車門打開,一群勞動者傾瀉而出。他們的臉上堆滿極高的疲憊和苦悶,心裡充滿渴望,只想以最快的速度回到...

 1 則評論
1 則評論  共 1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