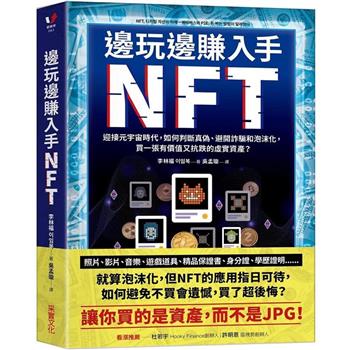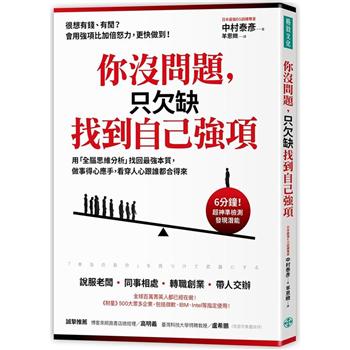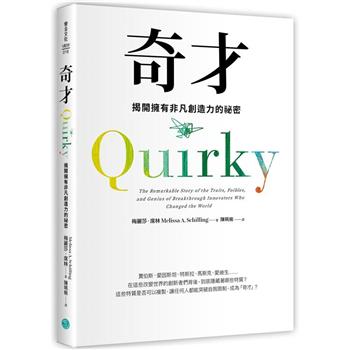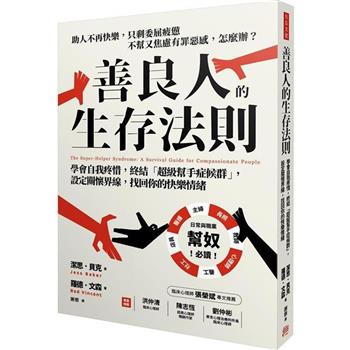背叛一個罪犯不會使人有罪,
我的罪在於我愛過一個罪犯。
奧斯卡金獎電影《為愛朗讀》經典原著
出版25週年紀念,根據德文版重新翻譯
駐德大使謝志偉專文導讀
★第一本贏得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冠軍的德國小說!
★第一本入選全美最具影響力的「歐普拉選書」的外國小說!
★榮獲德國漢斯.法拉達獎、《世界報》文學獎、基督教圖書獎!
★英國衛報「死前必讀的1000本小說」!
★德國ZDF電視台「百大最愛德語好書」!
★改編電影,由凱特.溫斯蕾主演,榮獲奧斯卡金像獎、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女主角殊榮!
在往後的歲月裡,米夏總是不斷夢見那幢房子。
那裡混合著清潔劑的氣味、煎炸食物的氣味,還有,「她」的氣味。
米夏永遠記得,漢娜熨燙衣物的專注神情,年少的他無法把視線移開。「先唸書給我聽。」漢娜總是這麼說,於是米夏便打開書本,領著她進入荷馬、西塞羅和海明威的世界,然後與她同床共枕。
但一個尋常的溽夏午後,漢娜卻突然消失無蹤。面對人去樓空的房間,米夏一直無法直視自己的罪惡感。或許,他不該迴避承認兩人的關係,不該為了學校裡新認識的女孩而冷落她。或許,逼走她的,正是他……
多年過去,米夏終於再次見到漢娜,卻不是在那個熟悉的房間裡,而是在法庭的被告席上。她清麗的容顏並未因落魄而減損,不若其他被告的避重就輕,她始終選擇堅定地辯解,即使觸怒法官也不退讓。米夏無法理解漢娜徒勞的堅持,直到最後,當漢娜緘默的眼神望向米夏時,他才終於明白,那隱藏在她內心深處多年的秘密……
《我願意為妳朗讀》是德國戰後「悔罪文學」的代表作,文學大師徐林克用凝鍊的筆觸,刻寫出一段寧靜卻深邃的禁忌之戀,也將一場罪與罰的思辨攤在字裡行間。漢娜對米夏而言,是童年的告別,也是初戀的嚮往,而這一段若即若離、似遠還近的關係,更象徵著整個世代對大屠殺歷史的反思。個人的小惡,究竟是如何鑄成群體的大罪?體制的無情,又如何摧殘麻痺人性的善念?我們該如何看待曾經犯下的過錯?而當時間更迭,你希望自己留下的,又會是什麼樣的過往?
作者簡介:
徐林克Bernhard Schlink
1944年生於德國北萊茵-威斯伐倫州,在海德堡長大。出身法律世家的他從小就喜愛文學,卻遵循家人的期望而學習法律,後成為柏林大學法律教授,並擔任北萊茵-威斯伐倫州憲法法官。而在法學界的豐富經歷,也讓徐林克對於犯罪和人性有著比一般人更深刻的洞察。
1987年他與瓦特.波普合著犯罪小說處女作《我遺落的那一半》,即榮獲德國「偵探檔案文學獎」、《世界報》文學獎,並被改編拍成電影。
1995年徐林克將自己的親身經歷寫成《我願意為妳朗讀》,一出版即轟動全歐洲,進軍美國則不但成為有史以來第一本榮獲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冠軍的德國小說,也是第一本入選全美最具影響力的「歐普拉選書」的外國小說,將他的寫作生涯推上了最高峰!該書目前已被翻譯成37種語言版本,並被改編拍成電影《為愛朗讀》,由凱特.溫斯蕾飾演女主角漢娜,一舉囊括奧斯卡金像獎、英國電影學院獎雙料影后殊榮。
另著有《愛之逃》、《歸鄉》、《週末》、《夏日謊言》、《奧爾嘉》、《關於寫作的思考》等書,作品量少質精,本本均獲得崇高評價。
徐林克現定居柏林與紐約。
譯者簡介:
姬健梅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德國科隆大學德語文學碩士,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中英文組。從事翻譯多年,譯作包括《反叛,改變世界的力量》、《你的身體,正在洩漏你的秘密》、《不要想藍色大象》、《我知道你在想什麼》、《變形記》、《告訴我,你為什麼殺人》、《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錢買不到的東西》。
章節試閱
1
十五歲那年我患了黃疸。那場病於秋天發作,到隔年春天才好。隨著天氣愈來愈冷,黑夜愈來愈長,我也愈來愈虛弱,直到新年來到,病情才漸漸好轉。一月裡天氣溫暖,母親替我把床移到陽台上。我看見天空、太陽和雲彩,聽見孩童在院子裡玩耍。二月裡的一個傍晚,我聽見一隻烏鶇在歌唱。
我們家住在布魯門街一棟巍峨宅邸的二樓,房子建於二十世紀初。病癒後第一次出門,我從布魯門街走到邦霍夫街。十月裡的一個星期一,我在放學回家途中曾在那條街上吐了。那時我已經連續好幾天感到前所未有的虛弱,每走一步都很吃力。在家裡或學校要爬樓梯時,一雙腿幾乎支撐不住。我也沒有食慾,即使在餐桌旁坐下時飢腸轆轆,沒多久就感到反胃。早晨醒來時口乾舌燥,覺得五臟六腑彷彿都移了位,沉甸甸的在我體內。身體如此虛弱讓我覺得很丟臉,嘔吐時尤其感到丟臉。那也是以前不曾發生在我身上的事。胃裡的東西湧進嘴裡,我試圖嚥下去,閉緊雙唇,用手掩住嘴巴,但是那些東西穿過我的手指從我嘴裡噴出來。我撐著一棟房屋的牆壁,看著腳邊的嘔吐物,又嘔出半透明的黏液。
一個婦人過來關心我,她的動作幾乎有點粗魯,一把抓起我的手臂,帶我穿過那棟房屋的陰暗過道,走進內院。院子上方在窗戶與窗戶之間拉起了繩子,晾曬著衣物。院子裡堆放著木柴,一間敞開的工坊裡鋸子滋滋尖叫,木屑紛飛。在進入院子的門邊有一個水龍頭。婦人扭開了水龍頭,先洗了我的手,再用雙手接了水潑在我臉上,我用手帕把臉擦乾。
「你拿另外一個!」水龍頭旁邊擺著兩個水桶,她拿起一個,裝滿了水。我拿起另一個,裝了水,跟著她穿過走道。她掄起手臂,把那桶水啪地潑在人行道上,把那堆嘔吐物沖進排水溝,從我手裡接過水桶,把人行道又沖了一次。
她站直了身子,看見我在哭,驚訝地說了聲「孩子啊,孩子」,便伸手把我摟進懷裡。我幾乎不比她高,感覺到她的胸脯貼著我的胸,在擁抱中聞到自己嘴裡難聞的氣味和她身上新鮮的汗味,不知道該把手臂往哪兒擺,我停止了哭泣。
她問我住在哪裡,把水桶擱在走道上,送我回家。她走在我旁邊,一隻手拿著我的書包,另一隻手扶著我的手臂。從邦霍夫街走到布魯門街並不遠,她走得很快,帶著一種果斷,讓我自然而然跟上她的腳步。在我們住的那棟樓前,她向我道別。
就在那一天,母親請了醫生來,而醫生診斷出我患了黃疸。後來我向母親提起那個婦人。若非如此,我不認為我會再去拜訪她。但是母親認為我理所應當要去道謝,等我的病好了,就該用我的零用錢買一束花,前去自我介紹並且表示謝意。於是,我在二月底時步行前往邦霍夫街。
2
邦霍夫街那棟屋子如今已經不在了。不知道是在何時拆除的,也不知道為何被拆。我離開故鄉已許多年了。現在那棟房子建於七○或八○年代,有五層樓和一層可居住的閣樓,捨棄了凸窗和陽台,粉刷得光滑明亮。門鈴的數目很多,表示屋裡隔成了許多小公寓。房客遷進遷出,就像租車還車一樣。一樓如今是家電腦商店,從前則開了一家藥妝店、一家食品行和一家錄影帶出租店。
以前那棟房子與現在這棟房子高度相同,但只有四層樓,一樓由金鋼石拋光的大塊砂岩建造而成,上面三層則是磚砌的,嵌著由砂岩建造的凸窗、陽台和窗框。門口有幾級台階通往一樓和樓梯間,下寬上窄,兩側都砌了邊牆,上面嵌著鐵欄杆,下方末端以螺旋形收束。大門兩側有柱子,門楣兩端各刻著一頭獅子,分別望向邦霍夫街的兩端。那個婦人帶我走進內院取水的入口是這棟房屋的側門。
這棟屋子在這一排房屋當中特別顯眼,我從小就注意到。那時我心想,假如它想變得更寬、更重,相鄰的房屋就必須往旁邊挪動,讓出位置來。我想像屋裡的樓梯間有灰泥壁飾,還掛著鏡子,樓梯上鋪著狹長的地毯,織著中東風格的花紋,用擦得晶亮的黃銅桿固定在每一級梯階上。我料想在這樣體面的屋子裡也住著體面的人,不過,由於房子年代久遠,又被火車的濃煙燻黑,我也把那些體面的住戶想像得陰沉古怪,也許聾了或啞了,駝了或瘸了。
在往後的歲月中,我一再夢見這棟屋子。那些夢境都很相似,是同一個夢和同一個主題的變奏。夢中我步行穿過一座陌生的城市,然後在一個我不認識的城區看見這棟房子矗立在一排房屋當中。我繼續往前走,心中疑惑,因為我認得這棟屋子,卻不認得這個城區。接著我想起自己曾經見過這棟房子。但我想到的並非家鄉那條邦霍夫街,而是另一座城市或另一個國家。例如,夢中我在羅馬看見了這棟屋子,想起我在伯恩就曾見過它。夢中的這個記憶令我心安,在異地再見到這棟屋子並不比在異地與老朋友巧遇更令我訝異。我掉個頭,朝這棟屋子走去,走上那些台階,我想要進去,我按下了門把。
如果我是在鄉下看見這棟屋子,那個夢就比較長,或是我在事後更記得夢中的細節。我開著車,看見這棟屋子在我右手邊,然後繼續行駛,起初只是想不透一棟顯然屬於城市街道的房子竟會矗立在空曠的原野上。接著我想起來自己曾經見過這棟房子,於是更加大惑不解。如果我記起曾在何處見過它,我就掉頭往回開。夢中那條馬路總是空蕩蕩的,我能猛然掉頭,使得輪胎發出尖銳的摩擦聲,再以高速往來時的方向行駛。我擔心會到得太遲,於是開得更快。然後我就看見了它。它被田野圍繞,油菜田、黑麥田,或是伐爾茲地區的葡萄園,還是普羅旺斯的薰衣草田。那個地方地勢平坦,頂多微有丘陵起伏,沒有樹木。天氣晴朗,陽光照耀,空氣閃著微光,馬路在豔陽下閃閃發亮。那些防火牆使得這棟屋子看起來與世隔絕,無法進入。那可以是任何一棟房子的防火牆。這棟屋子並不比邦霍夫街上那一棟更陰森,但是窗戶都蒙著厚厚的灰塵,讓人辨識不出屋裡的東西,就連窗簾都看不清。這是棟盲眼的屋子。
我把車子停在路邊,穿過馬路走向門口。看不見一個人影,聽不見一絲聲響,就連遠方的引擎聲、風聲、鳥鳴都聽不見,世界一片死寂。我走上台階,按下門把。
但是我沒有把門打開,我醒了過來,只記得自己剛才握住門把往下按,接著我想起了整個夢境,也想起自己以前就作過這個夢。
3
我不知道那個婦人姓什麼,我手裡拿著花束,站在門口那些門鈴前面猶豫不決。本來我想掉頭回去,但一個男子從屋裡走了出來,問了我要找誰,便叫我上三樓去找施密茲小姐。
沒有石膏壁飾,沒有鏡子,沒有地毯,這個樓梯間原本或許曾有過和這棟房屋的堂皇外觀並不相稱的樸素之美,但這份美早已消逝。梯階的紅漆在中央已被踩得斑駁,黏貼在樓梯旁邊牆上與肩同高的綠色油氈已經磨損,欄杆上缺了鐵條的地方綁上了繃緊的繩子替代。空氣中彌漫著清潔劑的氣味,這一切也有可能是我後來才注意到的。那裡總是一樣寒傖,一樣乾淨,總是有股相同的清潔劑氣味,有時摻雜著甘藍菜或豆子的味道、煎炸食物的味道,或是用沸水煮洗衣物的氣味。關於這棟屋子裡的其他住戶,我所知道的就只有這些氣味,還有各間公寓門前的踏腳墊和門鈴按鈕下方的名牌,我不記得曾在樓梯間裡遇見過另一個住戶。
我也記不得我是怎麼向施密茲小姐打招呼的了,也許是我預先想好了幾句話,關於我的病、她的協助和我的感謝,當著她的面背了出來,她帶我走進廚房。
廚房是那間公寓裡最大的房間。裡面擺著爐灶和洗碗槽、浴缸和熱水爐、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一個碗櫥、一個衣櫥和一張沙發,沙發上鋪著一條紅色絲絨毯子。廚房裡沒有窗戶,光線透過通往陽台那扇門上的玻璃照進來,能透進來的光線不多,只有當那扇門敞開時,廚房裡才是明亮的,這時就會聽見鋸子的滋滋聲從院子裡那間木工坊傳出來,也會聞到木料的氣味。
公寓裡還有一間窄小的客廳,擺著櫥櫃、一張桌子、四把椅子、一張高背單人沙發和一個火爐。這個房間在冬天裡幾乎從來沒生過火,在夏天裡也幾乎從未使用。窗戶面向著邦霍夫街,可以看見舊火車站的站區被挖得亂七八糟,有些地方已經打好地基,準備要建造新的法院建築和政府機關。最後,公寓裡還有一間沒有窗戶的廁所。如果廁所裡有臭味,走道上就也會聞到。
我也不記得我們在廚房裡都說了些什麼,施密茲小姐正在熨燙衣物。她把一條毛毯和一塊麻布鋪在桌上,把籃子裡的衣物一件一件地拿出來,熨過,摺好,擺在一張椅子上,我則坐在另一張椅子上。她也熨燙她的內衣褲,我不想看,卻也無法不看。她穿著一件無袖的圍裙式洋裝,藍底,綴著紅白小碎花。她把及肩的灰金色頭髮用髮夾束在頸後,赤裸的雙臂顏色蒼白。她拿起熨斗,用過之後擱下,把衣物摺好,擺在一邊,雙手的動作緩慢而專注。而她移動身體,彎下腰再站直的動作也同樣緩慢而專注。在我的回憶裡,她日後的面容與她當時的面容重疊,當我在眼前喚出她當時的模樣,所出現的她沒有臉孔,我必須重新建構出那張臉:高高的額頭,高高的顴骨,淺藍色的眼睛,豐滿的嘴唇弧線均勻,沒有凹陷、有力的下巴。一張女性化的臉,臉盤略大,不易親近。我知道當年我覺得那張臉很美,但如今我卻想不起它的美。
4
當我站起來打算離去,她說:「等一下,我也要出門,我陪你走一段。」
我在玄關走道上等。她在廚房裡換衣服。門虛掩著。她脫下那件圍裙裝,穿著淺綠色襯裙站在那兒。椅背上掛著兩隻長襪,她拿起一隻,用雙手交替收拉,把襪子收攏成短短一圈。她用單腳站立,把另一隻腳的後跟頂在這條腿的膝蓋上,彎下腰,把那隻捲起來的襪子套上腳尖,再把腳尖擱在椅子上,把襪子順著小腿肚、膝蓋和大腿往上拉,然後身體傾向一側,用襪帶把襪子固定住。她直起身子,把腳從椅子上放下,再伸手去拿另一隻襪子。
我無法把視線從她身上移開,我看著她的後頸和肩膀,襯裙下若隱若現的乳房,繃緊了襯裙的臀部,當她用腳頂住膝蓋再把腳擱在椅子上,她起初赤裸蒼白的腿在穿上襪子以後閃著絲質的光澤。
她感覺到我的目光,在伸手去拿另一隻襪子時停了下來,轉身面向著門,直視著我的眼睛。我不記得她是怎麼看著我的,是訝異?詢問?了然於心?還是責備?我臉紅了,一張臉熱燙燙的,站了一會兒就站不住了。我衝出公寓,跑下樓梯,跑到了街上。
我放慢了腳步走著,邦霍夫街、豪瑟街、布魯門街,這是我許多年來上學所走的路。我認得每一棟房屋、每一座庭園和每一道籬笆,有的籬笆每年都重新油漆,有的籬笆的木頭已經殘舊腐朽,用手就能捏碎,有些鐵籬笆在我小時候曾被我一邊跑一邊用木棍把鐵條敲得叮叮咚咚響。還有那堵高高的磚牆,我曾幻想牆後面有著神奇美妙和可怕嚇人的東西,直到我爬得上去了,發現牆裡只有一排排平凡無奇、乏人照料的花圃、莓果圃和菜圃。我熟悉街道上的鋪石路面和柏油路面,也熟悉人行道上路面材質的變換,從鵝卵石、鋪成波浪形狀的小塊玄武岩、瀝青到碎石。
這一切都是我熟悉的。當我的心跳不再加速,臉頰不再發燙,在廚房和玄關走道之間那一幕已經遠去。我氣我自己,我像個小孩一樣跑走了,沒有依照我對自己的期許沉著應對。我十五歲了,不再是九歲小孩。然而,什麼樣的反應算是沉著應對?這對我來說仍是個謎。
另一個謎則是在廚房和玄關走道之間那一幕本身,為什麼我無法把視線從她身上移開?她的身體十分強健也十分女性化,比我喜歡看的那些女孩來得豐滿。假如我是在游泳池看見她,我很確定她不會引起我的注意,而她裸露的部位也不比我在游泳池見過的女孩和婦人更多。何況她的年紀要比我夢想中的女孩大得多,超過三十歲?對於我們尚未親身經歷也並非即將邁入的年紀,是很難猜得準的。
多年以後,我想到我之所以無法把視線從她身上移開,並非單純由於她的身材,而是由於她的姿態與動作。我會請我的女朋友穿上絲襪,但我不想加以解釋,不想述說當年在廚房與玄關走道之間那謎樣的一幕,因此對方會以為那是種帶有情色意味的癖好,以為我喜歡蕾絲吊襪帶,而對方若是答應我的請求,就會擺出挑逗的姿勢,但是這並非當年使我無法移開視線的原因。當時她並沒有擺姿勢,也沒有挑逗之意,我也不記得她曾在其他情況下擺出過挑逗的姿勢。我記得她的身體、姿態和動作有時顯得遲鈍,並不是說她有多麼笨重,而是說她似乎縮回了她身體內部,把身體交給了身體自有的平靜節奏,不受大腦干擾,從而忘了外在的世界,這份對世界的遺忘也流露在她穿上絲襪的姿態與動作中。但她在這一刻的姿態與動作並不遲鈍,而是流暢、嫵媚、誘人,誘人之處不在於胸脯、臀部和大腿,而在於它邀請你在身體的深處忘了這個世界。
這一點在當時我並不明白,意思是如果我現在明白了,而不只是勉強找到解釋。然而,就在我當年思索著是什麼令我心旌蕩漾時,心旌就又蕩漾起來。為了解開這個謎,我把那一幕喚回記憶中,先前由於我把它視為謎題而拉開的距離消失了,一切又浮現在我眼前,而我又一次無法把視線移開。
1
十五歲那年我患了黃疸。那場病於秋天發作,到隔年春天才好。隨著天氣愈來愈冷,黑夜愈來愈長,我也愈來愈虛弱,直到新年來到,病情才漸漸好轉。一月裡天氣溫暖,母親替我把床移到陽台上。我看見天空、太陽和雲彩,聽見孩童在院子裡玩耍。二月裡的一個傍晚,我聽見一隻烏鶇在歌唱。
我們家住在布魯門街一棟巍峨宅邸的二樓,房子建於二十世紀初。病癒後第一次出門,我從布魯門街走到邦霍夫街。十月裡的一個星期一,我在放學回家途中曾在那條街上吐了。那時我已經連續好幾天感到前所未有的虛弱,每走一步都很吃力。在家裡或學校要爬樓梯...

 共 11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1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