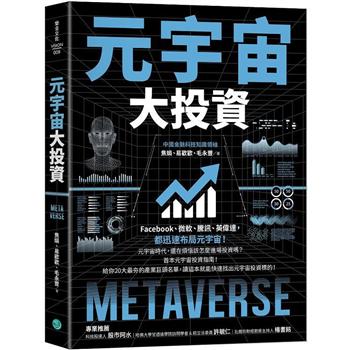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原文 Jean Baudrillar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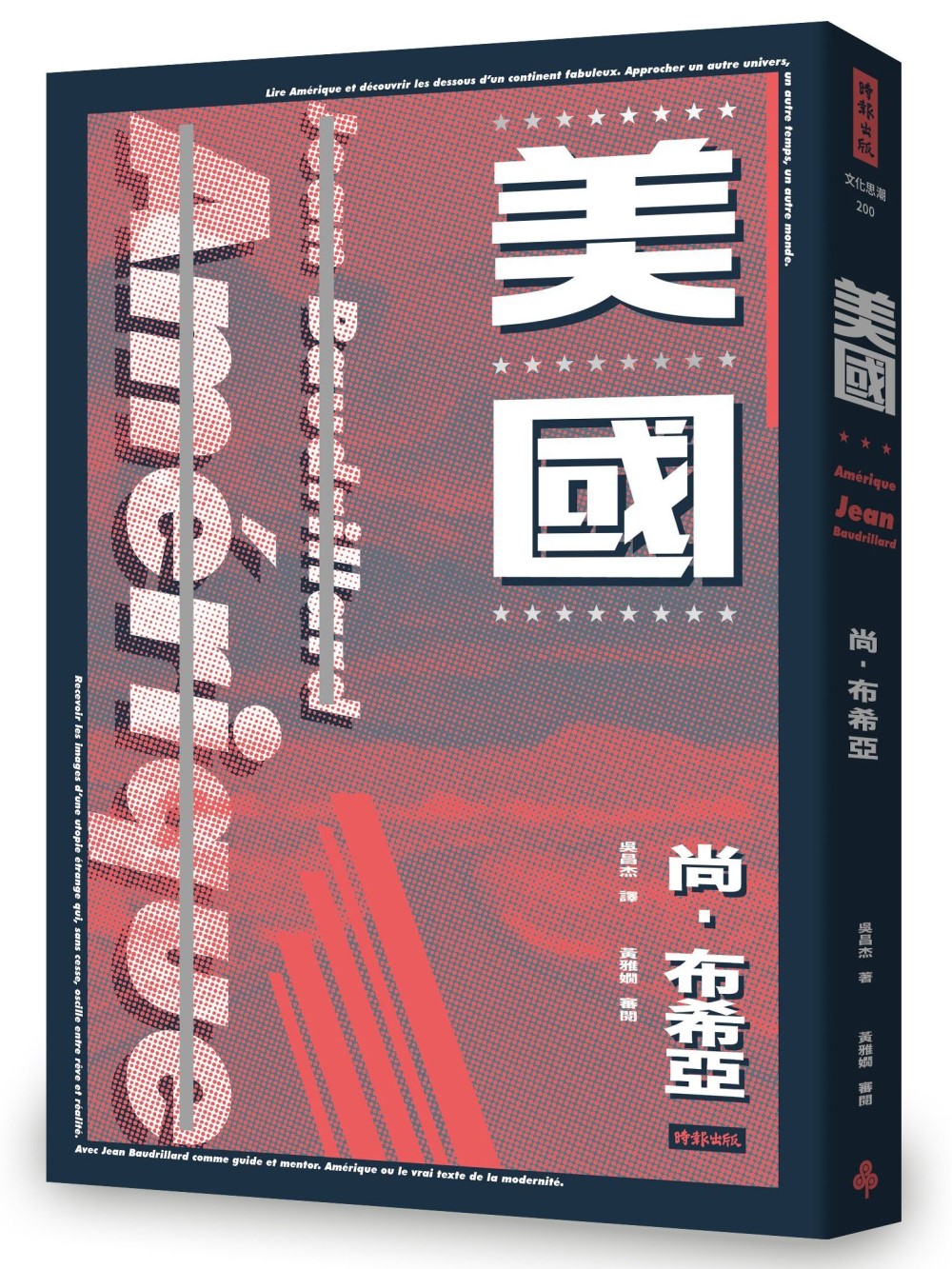 |
$ 220 ~ 288 | 美國
作者:原文 Jean Baudrillar / 譯者:吳昌杰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0-05-26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40頁 / 13 x 19 x 1.2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1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布希亞:
「﹝我﹞要追求的是『星空』的美國……
沙漠與公路,一望無際,曠渺無人的美國……」
法國後現代主義大師--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這本《美國》(Amérique)是他遊歷美國數州,遍覽數大城市的觀訪心得,這趟美國之旅充滿了出其不意的新鮮與驚奇,也是一次從「舊世界」到「新世界」,別緻的文化與自然觀察。全書充滿綿密的抒情力量,不管是美國地理景觀的沙漠、天空或人文景觀的紐約摩天大廈、洛杉磯高速公路,在大師的筆下都有犀利又引人無限省思的新解,值得一讀再讀。
《美國》當年推出英譯本時,激起搶購熱潮,獲《紐約時報》盛讚為不可多得之佳作。《美國》也算是布希亞的後現代主義著作中難得一見的「詩情」敘意,但書中詩情仍與一般風花雪月的詩情有很大的分別。這本書可做為想進入布希亞世界的讀者的入門書,更是中文讀者一親這位後現代大師書寫的最佳切入點。
作者簡介
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1929年7月29日-2007年3月6日)
生於法國漢斯,歿於巴黎,社會學家及哲學家。他被稱為「知識的恐怖主義者、後現代主義牧師、後現代大祭司」。他的思想從1960年代末期的著作《物體系》(Le Système des objets)開始,直到1980年代以降,可被歸納為「現實的消失」(disparition de la réalité)。知名著作除《物體系》外,有《消費社會》(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消費符號》(La consommation des signes)、《擬仿物與擬像》(Simulacres et simulation)、《冷記憶,一到五》(Cool Memories, I-V)等。
審閱者簡介
黃雅嫺
法國巴黎第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現任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領域為法國當代哲學、現象學運動、解構思想與法國存在主義哲學。近期關注領域為臺灣對法國哲學的繼受研究、跨文化翻譯理論以及可塑性概念對主體同一性問題探討等。主要著作散見於各中外學術期刊。
譯者簡介
吳昌杰
台大外文系畢業,師大英語研究所碩士,文字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