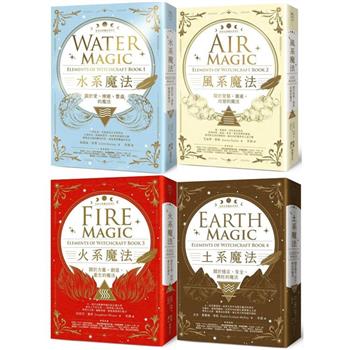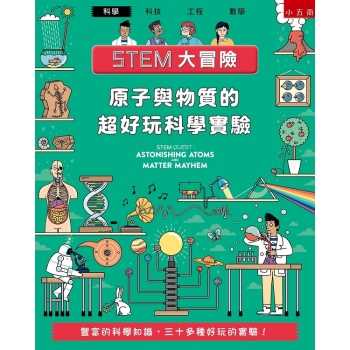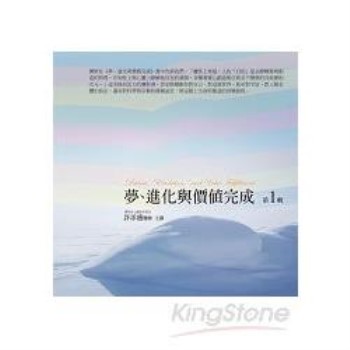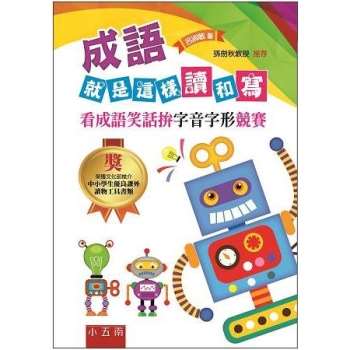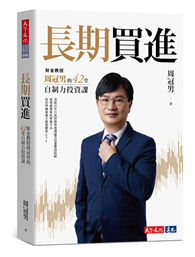1.制裁
2012年1月16日凌晨,華盛頓D.C.
凌晨之際,重案組辦公室的燈光幾乎都已熄滅,只剩不敷照亮走廊任何細節的昏黃燈光,以及三三兩兩的螢幕散發的飄盪光芒。螢幕上的聳動文句早已消失,它留下的抑鬱氣息卻揮之不去。
「讓我搞清楚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喬伊‧德艾勒難掩倦容,一口灌下今晚第三杯濃縮咖啡。「我們遇到一個自稱哥倫布的神經病,他以把玩政府部門跟警局的資訊為樂,還涉嫌殺人重罪。如今,在消聲匿跡一年之後他再度找上我們,到目前為止都還正確吧?」
「正確。」麥康說。
與麥康跟琳西相較之下,喬伊‧德艾勒的資歷非常淺。他不到一年前才調來特區。喬伊被同事們戲稱為「野鳥」,曾在佛羅里達州、麻州、紐約州、南北卡羅萊納、紐約市跟維吉尼亞州的警局任職,足跡幾乎遍佈整個東岸,可從來沒有在一個地方停留超過三年,以他如此顯赫的飄流資歷來說,他待在特區的時間應該所剩不多了。
喬伊翻著哥倫布的檔案,時不時在翻頁前舔一下拇指——就像老牌的警匪片中的老警探的動作,如果他面前擺著一盒撒滿糖霜的甜甜圈就更完美了。
「我瞧瞧......我們有他的案件記錄、犯罪側寫跟軼事記錄......換句話說,我們幾乎甚麼都沒有?」喬伊伸手去拿咖啡壺,替自己斟上第四杯濃縮咖啡。
「哥倫布不曾洩露自己的蹤跡,要逮到這種智慧型罪犯向來不是容易的差事。」琳西同意,哥倫布有那種把所有人玩弄於股掌之間的能耐。
他們當中就屬麥康最不喜歡聽喪氣話,他接過喬伊手上的檔案,不過其實他不需要再閱讀那些資料,他對哥倫布的豐功偉業了然於胸。「哥倫布是在四年前初次現身,當時他侵入了參議員傑許‧賈登海爾的辦公室電腦,將參議院的會議記錄公諸於世。食髓知味的哥倫布又陸續駭進眾議院、白宮國際事務處與各級警局,就連國安局跟調查局都掌握不到這傢伙的行蹤。」
「呃......我想不到更委婉的方式問這個問題,連聯邦單位都拿他沒轍,那我們還玩個屁啊?」
「我們只有一件他們沒有的東西,」馬康也只能點頭同意。「據目前的了解,哥倫布真正感興趣的對象是警局,而不是他一開始找上的那些高層級單位。」
「我差點就要感到榮幸了,不過我們是怎麼知道這件事的?」
「第一,除了警局以外,他從來不曾發過預告信。其次,他對參眾兩院與國際事務處等公部門的攻擊行動可說是漫無目的、不了了之,看起來更像是轉移注意的障眼法。你手上的檔案寫得很清楚。」琳西不禁翻了個白眼,她不懂喬伊為何總是寧可一直丟問題也不願好好看完檔案。
喬伊搔了搔鬍渣,儼然是對琳西的牢騷置若罔聞,轉頭面對一向對人恢宏大度的麥康:「言下之意是,他對警局的攻擊行動有比較『聚焦』囉?」
麥康輕輕地點頭。「他只針對犯罪資料庫中強暴案的檔案下手,共計四名強暴前科犯的身分被他公諸於世。其中最令人感到頭痛是:這四名強暴前科犯中有三人在身分暴露的一週內遭人謀殺;唯一的例外則是因為違反假釋條例而返監服刑的強納森‧史崔。」
「我不知道該說甚麼......我似乎開始欣賞這傢伙了。」
「嘿,你在說甚麼瘋話?你是個警察欸。」琳西難以置信地說,滿臉都是不以為然。
「妳還是個女人欸。」喬伊模仿琳西的語調,不甘示弱地回嘴。「我不敢相信妳竟然會同情那些死有餘辜的強暴犯。我們的法律對那些敗類實在太寬容了,他們服刑頂多三、五年,但是那些被強暴的人呢?他們可能一輩子都走不出這種陰影!」
「嘿!專業一點,別再吵了。」麥康用力地擊了下掌,以一貫就事論事的口吻嚇阻他們爭執下去。「哥倫布給我們出了回家作業,天亮以前我們得徹底地重溫這些快要發霉的案件、找出過去沒找出來的模式,並檢查任何可能有所突破的弱點。」
「好吧,坐在這裏乾等下去也不是辦法。」喬伊揪著五官扮出個鬼臉。
D.C.
同一時間,同一座城市裏的某處,有個跟重案組警探們一樣準備徹夜不眠的人。這間暗房大多數的空間都被嗡嗡作響的伺服器佔據,機台散熱孔不斷噴出大量熱氣,為了確保它們運作正常,屋內有三台二十四小時運轉的空調,足以抑止躍躍欲升的室溫。
他在網路世界化名為「哥倫布」,在他自己建立的圈子中擁有名聲與威望,卻沒有任何人能夠接近他。他愜意地仰躺到椅背上,像是巡禮似地閱覽並列著的三台二十七吋螢幕,最右邊的那個總是被他架設的網站「新世界」的首頁佔據。
這個網站曾被調查局盯上,時至今日都是令他沾沾自喜的過往。在虛擬伺服器與繁複的加密技術輔助之下,那些探員很快就體認到這是件苦差事。然而調查局資訊安全部終究不是省油的燈,僅花不到兩天就打破了重重阻礙,駭入「新世界」的虛擬位址。只不過哥倫布在設計階段就不曾奢望它是個固若金湯的網站——尤其對手是聯邦調查局時,這種想法只是自尋死路。他的替代方案是建立一個內嵌程式,會在網站被侵入後利用釋出的網路封包循著相同的路由反向追蹤,原理跟許多間諜程式類似。這樣類似玉石俱焚的攻擊方式果然奏效了,為保護那些被列為聯邦機密的檔案,調查局搗破「新世界」的行動落得草草收場。
所向披靡的調查局只存在於好萊塢的電影裏。哥倫布懂得這個道理。這裏畢竟是現實世界,「正義」並不總是擁有優先順位,調查局同樣有官僚與科層體制,它自然會決定事情的輕重緩急。
哥倫布摸了摸自己乾燥的手臂,左手指輕輕地挪動滾球,極為吃力地瀏覽網站上的討論串,每篇文章都是一起「案件」——由他來重新審理的案件。舉凡受害者、受害者家屬、甚至只是純粹義憤填膺的網民......這個網站向所有關切強暴案議題的人敞開雙臂,歡迎他們來暢所欲言。他們自成一個社群,彼此慰藉、發牢騷、並將那些警局跟司法部門東遮西掩的資訊公告週知。法律與媒體對強暴犯一向過分寬容,刑責低得離譜不說;還處處掩藏他們可恨的所作所為。唯一聊表欣慰的是:社會輿論對那些敗類的撻伐始終不遺餘力,只可惜沒有人願意將這股勢力凝聚起來。
哥倫布篤信:他就是擔起這個職責的人。他感覺得到自己的胸腔起起伏伏,呼吸伴隨的倉卒感間襲間歇,但這絲毫不足以阻止他。
循著直覺的導引,他的手指陡然停頓下來,點閱其中一篇十一個小時前的文章。他一向仰賴直覺點閱「案件」,接著繼續憑著直覺判定這件案子應不應該受理。哥倫布對自己一連串的直覺判斷很有信心,他相信自己能看出哪些是無病呻吟;哪些是真正需要他伸出援手的人。
派翠莎......。
看著重述案發的經過時,哥倫布幾度失控掩面。他自認不是感情豐富的人,但是這類文字總會勾起對派翠莎的思念、勾起她那慘絕人寰的遭遇。他跳過了大多數不堪入目的文字,很快地來到文章的末端,並判決這則案件符合那些主觀的原則——至少字面上看來已經足夠。接著就進入到最後、也是僅有的理性決策階段:可行性。
在「新世界」裏發表文章都有一項原則:必須公開加害者的樣貌、姓名或任何能鎖定特定嫌疑人的資訊。可惜的是,扣掉極為少數熟人所為的案件,絕大多數的被害者根本對加害者一無所知,此時就必須透過新世界的「人肉搜索」機制,以弭平他與被害人之間資訊不對稱的問題。被害人可以選擇用操作簡單的人像繪圖功能描摹加害者的樣貌;或者是從網站上與犯罪資料庫同步的頭像逐一指認。一旦完成了這道程序,哥倫布便會完成剩下的工作:取得詳細的檔案、確認符合「司法判決失能」條件、調查案件敘述的可信度、擬訂計劃......
以及,制裁。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古琛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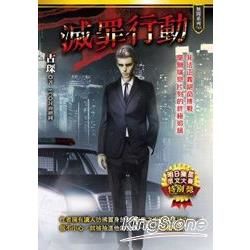 |
$ 43 | 滅罪行動
作者:古琛 出版社:明日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1-02 語言:繁體書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滅罪行動
特色
非法正義絕命挑戰
毫無喘息片刻的終極追緝
明日獵星徵文大賽特別獎 ◎古琛
作者擁有讓人彷彿置身於CSI影集之中的文字功力,一個不小心,就被抽進他的世界——D51 盛讚推薦
內容簡介
我是個默默無聞的導演,為諸位獻上這齣正義的饗宴。
所向披靡的調查局只存在於好萊塢的電影裏。他懂得這個道理,因此架設了「新世界」網站,駭進華盛頓特區警局犯罪系統公佈強暴前科犯資訊,接著發出殺人預告、更公開屠殺影片……不斷將重案組耍著玩的「哥倫布」目的只有一個,他要讓全世界知道:
只有「制裁」才是絕對的正義!
作者簡介:
古琛,本名黃翊瑞,1988年生,就讀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所,現為城邦原創簽約作家。自十六歲起寫作至今,已完成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各六部。寫作主題早期以翻案歷史為主,自2010年起專事寫作懸疑推理小說。
2011年初成為城邦原創簽約作家,以《弱勢暴力》為首的「史特勞斯犯罪推理」為其首部系列小說,現以該系列延伸作品《重案解密:第一季》持續連載中。獲明日獵星特別獎的《滅罪行動》為其第13部小說。
筆耕至今未有太多值得誇耀的成就,除了持續不懈、未忘初衷的創作之外。
更多作品:http://www.popo.tw/users/gouchen18
章節試閱
1.制裁
2012年1月16日凌晨,華盛頓D.C.
凌晨之際,重案組辦公室的燈光幾乎都已熄滅,只剩不敷照亮走廊任何細節的昏黃燈光,以及三三兩兩的螢幕散發的飄盪光芒。螢幕上的聳動文句早已消失,它留下的抑鬱氣息卻揮之不去。
「讓我搞清楚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喬伊‧德艾勒難掩倦容,一口灌下今晚第三杯濃縮咖啡。「我們遇到一個自稱哥倫布的神經病,他以把玩政府部門跟警局的資訊為樂,還涉嫌殺人重罪。如今,在消聲匿跡一年之後他再度找上我們,到目前為止都還正確吧?」
「正確。」麥康說。
與麥康跟琳西相較之下,喬伊‧德艾勒的資歷非常...
2012年1月16日凌晨,華盛頓D.C.
凌晨之際,重案組辦公室的燈光幾乎都已熄滅,只剩不敷照亮走廊任何細節的昏黃燈光,以及三三兩兩的螢幕散發的飄盪光芒。螢幕上的聳動文句早已消失,它留下的抑鬱氣息卻揮之不去。
「讓我搞清楚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喬伊‧德艾勒難掩倦容,一口灌下今晚第三杯濃縮咖啡。「我們遇到一個自稱哥倫布的神經病,他以把玩政府部門跟警局的資訊為樂,還涉嫌殺人重罪。如今,在消聲匿跡一年之後他再度找上我們,到目前為止都還正確吧?」
「正確。」麥康說。
與麥康跟琳西相較之下,喬伊‧德艾勒的資歷非常...
»看全部
作者序
「沒有任何人有罪;然而罰卻加諸在每個人的身上。」這樣的故事主軸出自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深刻地勾勒出古今中外皆未曾與現實脫鉤的議題。對寫犯罪推理題材的筆者而言,「罪罰不等」是遲早得面臨的棘手問題,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找到適切的著力點發揮。
在寓意的另一頭蘊含了另一種可能:當人們都有罪;但罰卻沒有適時予以遏止。很不幸地,這類的事同樣舉目可及,同樣是悲劇的肇端。於是,兩年前筆者決定以強暴案件的形式突顯制度荒謬的寬容,故事的雛形在那時漸漸生成。
強暴犯的犯行足以造成受害人永難磨滅的傷害,不知背後...
»看全部
目錄
序幕
1. 制裁
2. 模式
3. 初識
4. 賭注
5. 心戲
6. 過濾
7. 破綻
8. 攻勢
9. 堡壘
10. 新世界
11. 動線
12. 亡妻
13. 邂逅
14. 陷阱
15. 對決
落幕
1. 制裁
2. 模式
3. 初識
4. 賭注
5. 心戲
6. 過濾
7. 破綻
8. 攻勢
9. 堡壘
10. 新世界
11. 動線
12. 亡妻
13. 邂逅
14. 陷阱
15. 對決
落幕
商品資料
- 作者: 古琛
- 出版社: 明日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1-02 ISBN/ISSN:978986290491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92頁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驚悚/懸疑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