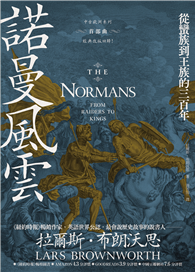酒吧裡經年氤氳著菸燻的味道,「陽光的另一面」的旋律從我指間緩緩流瀉。即使觀眾在短短的幾小節內消失,但我的手指依舊靈活飛舞,內心滿溢了與世界合而為一時所釋放出的無名化學波動……
羅斯‧克里夫頓,一位在五光十色城市酒吧巡迴演奏的鋼琴爵士樂手。午夜前,他如同蜷伏在琴鍵上的貓,在和弦的背後,用冷冽的雙眼逡尋當晚下手偷竊的對象;凌晨後,化身為分發信件的郵差,將竊取所得轉手,散播片刻歡樂予眾人。
公路、酒吧、旅館;巡迴、琴聲、偷竊,在一個個城市間永無止境的移動,像是一連串十六分之一的音符,持續規律迴旋反覆。直到羅斯姪子克雷出現,將所有的規律全部打亂……
《爵色夜迷》以一位爵士鋼琴手從事竊盜副業,在雙面生活與偽造之下,發展出的即興喜劇。作者費屈運用俠盜羅賓漢般的角度,輕快的寫作手法,在煙霧瀰漫的俱樂部與深夜進行的對話中,賦予這部小說黑色電影的氛圍,也間接思索不義之人與正直如何共存。他一針見血地精準切入「施與受」之間的灰色地帶,並探討人們對於自我、人生的種種迷思。史多納犀利的黑色幽默風格,帶領讀者進入了不思議的領域,看見最荒誕的人生百態!
作者簡介:
史多納‧費屈 Stona Fitch
1961年生於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其間曾獲得寫作獎,並擔任普林斯頓報的主編。曾任記者,之後加入次文化地下組織,組過樂團,玩過電音樂、寫歌,錄製唱片。此目前於美國麻薩諸塞州。
出版過兩部小說,已被翻譯成許多歐洲語言。其中《Senseless》講述反全球化的抗爭,曾被改編拍成電影。而本書的出版過程也頗為曲折,起初由非營利的小出版社發行1500冊,但由於一推出讀者便搶購一空,又經美國《洛杉磯時報》及英國《書商週刊》報導後,馬上洛陽紙貴,隨即售出多國版權。
譯者簡介:
簡秀如,文化大學法文系畢業。曾任教師、編輯、雜誌及影片字幕譯者,目前為新竹某科技公司的專案英文寫手,並於輔仁大學翻譯學碩士在職專班進修中。譯作有《365種越玩越聰明的課後遊戲》、《野獸學家》、《一個字也別說》等。
章節試閱
1 克里夫蘭
我將指尖輕按在鮑德溫平台鋼琴的破損琴鍵上,耳際傳來依偎的情侶與銀行家們急切地等待表演而發出的嗡嗡耳語。我那架十呎的貝森朵夫鋼琴正枯守在北好萊塢的一座閣樓裡,但是我不願去想。今晚就只有我和這架略顯憔悴的鮑德溫鋼琴,我們是低矮平台上兩名傷痕累累的酒吧老兵,世界就局限在一小盞聚光燈所灑下的橢圓形光束裡。
從指間緩緩流瀉而出的「陽光的另一面」(Far Side of the Sun),向來是開場的最佳序曲。在短短幾小節之內,我遺忘了觀眾,但我的手指靈活飛舞著,我的心溢滿了身體與世界合而為一時所釋放出的無名化學波動。儘管我能滔滔不絕地敘述彈琴之樂,但是我的至樂卻也是他人的苦事。
今晚的組曲,融合了我從紐約到舊金山各地酒吧巡迴演出的數千首樂曲。我的左手記下固定和弦的進程,右手則以略帶少許裝飾的手法追逐著旋律,這是一種主流風格,既動聽又通俗。
一家位於淺灘區的新酒吧透過我的經紀人馬侃,付了我兩千元做三節各半小時的演出,好教客人點更多藍色馬丁尼、荷蘭進口啤酒,以及用焦黑甘蔗和干貝成串的開胃菜。
我是以保險箱竊賊的思維來看待爵士樂,熟悉的旋律與共鳴和弦適當的組合,就像卡榫喀嚓地轉入正確位置,那道封鎖已久的門便會開啟。我的演奏時光讓觀眾放鬆享樂,導致其情緒色彩產生微妙的轉變,促使他們消費、打賞小費,並推薦其他顧客帶著好胃口、荷包及信用卡來到巴克艾酒吧。
當你探究世界經濟的最底層,你會發現,金錢原來深植在我們的骨子裡。
我以「帕克心情」(Parker’s Mood)作為第二節的序曲,因為酒吧老闆蓋瑞如此要求。一般的規矩是彈奏點歌,除非點選的是一首讓眾人紛紛走避的曲子,例如「月之舞」(Moondance)。在彈奏「證據」(Evidence)這首簡短俐落的孟克曲目一開始,我在低音部分加入八小節左右的新和弦:減七和弦,部分伴以九和弦,是不過分感傷且相當微妙的組合,只是和「證據」毫不相關。
我快速地瞥了一眼,發現觀眾隨意點頭應和音樂,並且以更符合這種夜晚時段的步調喝著酒,情侶則靠得更近了,這是發展到床上的過程。我們販賣的最終商品實際上是肉體色慾。
沒有敏銳音感的聽眾,此時也能聽出低音部分的不和諧了。鮑德溫鋼琴那污漬斑斑的黑色琴殼嘶嘶作響,似在發送出停止這場混亂的微妙警訊。我也開始警覺到像這樣的玩法會導致何種下場。被黑色蘭姆酒及財務困境整垮的傑奇‧摩根,曾是馬侃旗下最出色的樂手之一。他在一年前失控,激昂地重新詮釋咆勃版的「到這裡來吧!」長達一小時之久,因此被永久踢出了巡迴演奏圈,為大家立下殺雞儆猴的榜樣。
我的左手回歸原位,及時和諧地彈完了副歌,在另一小節延宕了一會兒,然後終結。掌聲響起。
我在恍惚的狀態下彈奏了十二首曲子,雙眼微閉,心神猶如夏日迷失的雲彩,在旋律上盤璇。我想像有更不堪的人生,就像冷凍豆子從傳輸帶上滾落,頭戴紙帽的分類員以凍僵的手指從中挑揀。我記得老頭辦公室裡堆疊的文件,看起來有如地質結構。我也想起西瓜藤蔓蜿蜒地穿過塵土,尋求雨水的滋潤。
身穿黑色上衣的女子和她幾位同事同坐,桌面上擺滿了酒瓶和玻璃杯。他們擠坐在一處,討論、歡笑、凝視著。當我彈奏時,她看著我的雙手,隨著「柳樹為我哭泣」(Willow Weep for Me)的旋律輕輕點頭。這是亞特‧泰坦的版本。她聆聽時,手擺放在喉頭處,手指摸索著鎖骨的輪廓。
到了第三節,她的朋友都已離去,只剩下她。這位臉色蒼白,臉上有著雀斑,年約三十五歲的女子,外表頗具吸引力,但神情略顯狂野。喝了一晚的紅酒,促使她在我結束最後一節的演奏時,招手要我去她那一桌,並且對我自我介紹。珍告訴我,她剛升遷為投資者關係部門的副總裁,所以晚上和女性友人出來玩。
「這不是天底下最有趣的工作!」她說,「有趣程度當然不及……」她伸出一隻手,在空氣中彈奏起虛擬鋼琴。
「你一定會大吃一驚。」我敢說她擁有一架好鋼琴。擁有鋼琴是某些女人用來帶我回家—公寓、郊區的理想住家、閣樓—的藉口,好像我需要有個藉口似的。
將近凌晨兩點,酒保把空啤酒瓶摔進塑膠垃圾桶裡,蓋瑞則猛地將燈光擰得白亮,明示大夥兒該離開了。事實證明,他是個乖戾的惡霸、酒鬼,員工對他心生畏懼,整個酒吧都籠罩在他的威脅陰影下。
「喝光吧!」珍說道。
「這酒的味道不怎麼樣。」
「我家有幾瓶上好的紅葡萄酒,」她提議,「還有一架鋼琴。」
當然!
「一架史坦威鋼琴。不過對你來說也許已司空見慣。」
「立型?還是平台式?」我說,彷彿款式很重要。
「平台式,是紫檀木。」
我稍微摩娑了下巴,彷彿取決不下,「我萬分樂意去一看究竟。」我套上西裝外套,將一本厚厚的黑色活頁夾挾在腋下。我的爵士樂譜和我形影不離,這本爵士聖經裡摻雜了各式祕笈,底頁還有一些驚喜。
珍扶住我的肩膀站起來後,踩著高跟鞋搖晃了好一會兒,「你真風趣。」她說,「我的朋友說你看起來就像是這種人。」
「我很風趣,好吧。」既然魅力不再,幽默感倒也能讓人無往不利。
這天晚上,我坐在珍的奧迪車上,沿著湖濱大道疾馳狂奔。她開車的架勢可媲美專業車手。汽車內充滿皮革、咖啡,以及馬丁尼的氣息。她一度將手伸過來,信心滿滿地在我的膝上撫摸著,藉此向我保證一切都不會有問題。
「我通常不會……你知道的。」她輕聲地說。
「帶酒吧的樂手回家?」我說。
「是的,就是這樣。」
我微笑了。我的吸引力和外表並無多大關聯。我並未心存期待,只是聆聽並且專心一志,就這樣,使她們卸下對男人的心防。
珍的公寓位於克里夫蘭高地一棟新大樓的高樓層。我們在電梯裡親吻,珍壓得我往後退到金屬扶手上。電梯門開啟後,我們踉蹌地直接進入客廳,家具是鉻黃色的軟皮革,活動式照明光源調到最低。從這裡臨高俯瞰其他公寓大樓,每扇燈火通明的窗口都流瀉出家的意象。
珍跟在我的身後,雙臂環抱住我。想來這趟到訪是不會有鋼琴獨奏演出了。「你在看什麼?」
「燈光。」我說。
「去年夏天,往北幾個街區的一棟公寓曾發生火警,灰燼一路飄到這邊。屋頂露台積了滿滿一層灰,看起來像是灰色的雪。」她顫抖著,「那場火真的太可怕了!燒毀一棟像這樣的公寓大樓。空中飄浮的有可能是我的骨灰。我根本不敢想。」
我點頭。
「我去給我們倒杯酒。卡本內?」
「好的。」我坐在珍的鋼琴前,它的聲音清亮,機械裝置良好。旁邊一堆琴譜裡有初級琴譜和兩本令人望之生畏的徹爾尼練習樂譜,上面歪扭地塗寫了小孩的名字,也就是珍的女兒,關。這下子在酒吧談到一半的話題就明確了:珍最近剛離婚,夫妻倆共同擁有關的監護權,孩子在週末與先生共渡,珍不想落單。
我以稍嫌過火的強勁節奏彈著帕克版的「可擁抱的你」(Embraceable You)。珍躡足走過我身後的拼花地板,小心地將一杯紅酒擺在鋼琴上。我停止彈奏,轉過身來。活動式照明在她的背後散發光茫,勾勒出她寬厚肩膀的輪廓,金色秀髮放了下來。
「驚喜!」她低聲說。珍一絲不掛,一隻手掌的陰影徹底遮住修長雙腿之間,算是遮羞的意思。
要讓我驚喜可沒這麼容易。我站起來,親吻她,手指摸索著她強壯的背,以及緊繃的肩胛骨。珍把離婚和工作諸事如滿袋石子般地背負在肩上。
她忙著解開我的皮帶,但是我延緩她手上的動作。多數人都會迫不及待,加快節奏,急著解決。我緩慢地把珍放躺在皮沙發上,然後在她身旁坐下。我從她的腳趾開始,手指在她的肌膚上畫圈,將她的皮膚當成黏土般揉捏。
「好有力的雙手。」珍緩緩朝我移過來,任由陌生人的手在她身上隨意漫遊。她的雙足至少應該揉上五分鐘,時間長得足夠舒緩每處關節,但又不至於久到讓珍開始擔心我是不是個有戀足癖的怪胎。
她趾環上的圖案是一條蛇吞噬自己的尾巴。我的手指沿著趾環摸索。「啣尾蛇。」
「你說什麼?」
「妳的趾環稱作啣尾蛇,是一種象徵。我想是埃及人吧!某種關乎生與死的永世輪迴。」
「那說法真讓人覺得沮喪。」
我看著她,「我覺得還好。」
「我看上它只是因為這是店裡唯一用黃金打造的,大多數的指環都是銀製品。蛇眼部分以碎鑽鑲嵌。」
細微的碎鑽捕捉住光線,混合後再反射出去。它們會在我和珍入土為安多年後依然隱約閃爍。如珍所言,這真是令人沮喪的想法。我往上移動,沿著她的腳踝輕柔地揉捏。
珍美麗動人。她的手臂略顯粗壯,肩部斑點在這個注重修飾美化的時代,看起來稍嫌多了些。但是,所有的女人都是美麗的,她們幾乎毫無例外地全具備了某種炙熱的靈魂與魅力。
我沿著珍的腿輕柔按壓,指尖下的脛骨堅硬如石。我順著珍的大腿內側緩慢向上摸索,引發出任何掌聲都比不上的一聲輕嘆。她拱起背抵住皮沙發,雙手高舉過頭,抓住黃色的沙發框架。
「我……」
我伸手觸摸她的唇,她輕舔著我的手指。我以指尖輕壓她窄小的鎖骨,也就是我們在酒吧談話時,她以手護衛的地方。我撫摸鎖骨一處凸起的硬塊,就在小凹陷的前端。
珍僵住了,「我弄斷它了。」她輕聲說道,「或者更精確地說,是我丈夫的傑作。當時我們發生爭執,他在健身俱樂部一把將我推下樓梯。我的頭皮也縫了好幾針,但是被頭髮遮住了。」
「我為此感到難過。」我說。我想到我父母的慍怒爭執,那些彼此交相指責的無解之結,但斷裂的鎖骨,是不同程度的傷害。
在珍的公寓裡,這段介於午夜到清晨的平靜時期,我為我們倆打造出不可告人的交易,我扮演的角色,就是用巧手修補珍所受到的傷害。天色轉為靛藍,星子在克里夫蘭的上空輪轉。珍的肌膚緊緊貼合我的撫觸,彷彿我正以她的血肉為她塑形。蛇吞噬了自己的尾巴。我們有漫漫長夜等待消磨,而且在我們入睡前,還有新旋律,一個又一個的音符,以及有待解決的和弦等待被彈奏。
我裸身,爵士樂譜挾在腋下,悄悄走過灰色的公寓,珍躺在沙發上,身上蓋了條毯子。我們共度的時光讓她精疲力竭,我身上滿是她的香氣,彷彿我曾在珍的胸懷間沐浴徜徉。我身上每吋肌膚都有她的味道,除了你心懷遐想的那一處。那裡依然乾爽,絲毫不曾沾染珍的氣息。插入,不再是我的表演項目。
花點時間看看你的雙手,想像手指是十根長度用途各異的陰莖。它們總是堅挺不已,不需要威而鋼;它們極度靈活又強壯,連續活動幾小時也不會喊累或變小;它們不會使人受孕。靈巧的雙手是最重要的性器官,這是我的獨門理論。
我凝視一間床上擺滿填充玩具,牆上掛著圖畫的房間,好一個歡樂童年的意象。在走道盡頭,筆記型電腦的發亮螢幕讓珍的辦公室充斥著病態藍光。到了臥室,我躡足走進更衣室,從樂譜後面的暗袋拉出一個小金屬工具包。我掏出薄如信用卡的手電筒,打開它,然後叼在嘴裡,讓我在以指關節逐一開啟抽屜時能看個清楚。過往的回憶通常都收藏在最上層的抽屜裡,就塞在襪子和內衣的後面。
果然不出所料,抽屜後面有個紅色的人造絲小袋子,裡面是珍的黃金婚戒和訂婚戒指。我將珠寶鑑識放大鏡嵌入眼窩,檢視它的成色。訂婚戒指的鑽石接近兩克拉,圓形明亮式切割,共有五十八個光滑刻面。顏色良好,亮光不錯,沒有黃或灰的暗影。但淨度就比較難檢視了。凡鑽石都有瑕疪以及程度不等的斷裂,這是它在地底受熱時產生的雜質,肉眼難見,只有在某個角度才得以看見。以珍的鑽石來說,她的鑽石有少許深色雲狀物,但是無甚大礙。
我打開金屬工具包,檢視裡面一排排的盒子,各種形狀、大小及亮度的鑽石閃閃發光。它們是阿達姆斯鑽石,市面上最佳的合成品,是由馬侃向紐約的猶太鑽石商購得的。我從狹槽取出一顆類似珍的鑽石的廉價雙胞胎,然後拿出反轉卡鉗,嵌在戒台鑲爪中間。每根卡鉗末端均包覆一小片柔軟絲絨,讓我在稍微施壓時不致於留下痕跡。最後,珍那顆厄運婚鑽就落入我的手裡。
我把鑽石塞到舌下,這是我多年前學到的招數。當時我正從紐約一位知名卻失眠的脫口秀主持人的多串寶石項鍊上拆下一把老礦鑽石,卻差點在攢在手心時被活逮。我將新鑽石放進去,拿卡鉗稍微夾攏戒台,然後用珍的黑色絲質內衣擦亮戒指,再把它放回小袋子裡。
在珍臥室裡中那間密不通風的更衣室裡,我的動作極快,搜索並竊取鑽石的整個過程要不了一分鐘。熟能生巧。圓形、方形、枕形車工、新舊大小不等,我看過的鑽石比安特衛普的鑽石商要來得多。我從私人財物中盜取珍寶,然後像釋放瓶中精靈般,將它釋放。
珍也許永遠不會得知她的鑽石已成贗品。她未經訓練的眼睛永遠不會注意到,這些珠寶在一夜之間身價暴跌。萬一我在夜裡動的手腳被識破,她八成會怪罪到她前夫頭上。也許四十年後,關要賣掉母親的珠寶時才會察覺此事。假如掉包事件被揭露,保險公司會給付損失,反正沒人會替保險業者感到心疼。
真正的罪犯是鑽石企業聯盟,他們設法說服像珍和她粗暴的前夫那些人,去相信他們會需要一顆豆子般大小的鑽石,然後再精心操控生產和供應,以維持價格居高不墜。鑽石和磚塊一樣尋常,我正在清除那些被過分高估價值及賦予文化內涵的消費項目。一切就從這裡開始,在深夜的陌生人寓所裡,我搜尋亮晶晶的東西,然後帶著它遠走高飛。
微光在客廳蔓延開來,提醒我該下樓去搭計程車,回到市中心的下榻旅館。我從地上撿起黑色西裝套上,用手撫平上頭的縐褶,然後俯身親吻珍的前額。她稍微動了一下身體,臉上露出微笑。我已圓滿達成這場交易的任務。至少在我輕輕帶上身後的門,走向電梯時,心裡是這麼盼望的。
沒錯,我偷竊,但我無意致歉。偷竊不是重點,如何處理到手的財物才是關鍵。
1 克里夫蘭
我將指尖輕按在鮑德溫平台鋼琴的破損琴鍵上,耳際傳來依偎的情侶與銀行家們急切地等待表演而發出的嗡嗡耳語。我那架十呎的貝森朵夫鋼琴正枯守在北好萊塢的一座閣樓裡,但是我不願去想。今晚就只有我和這架略顯憔悴的鮑德溫鋼琴,我們是低矮平台上兩名傷痕累累的酒吧老兵,世界就局限在一小盞聚光燈所灑下的橢圓形光束裡。
從指間緩緩流瀉而出的「陽光的另一面」(Far Side of the Sun),向來是開場的最佳序曲。在短短幾小節之內,我遺忘了觀眾,但我的手指靈活飛舞著,我的心溢滿了身體與世界合而為一時所釋放出的無名化學波...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