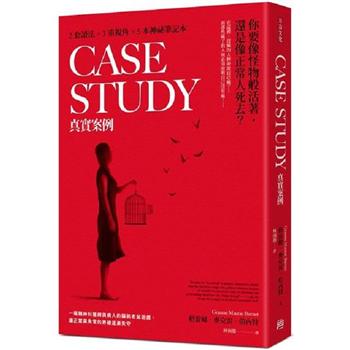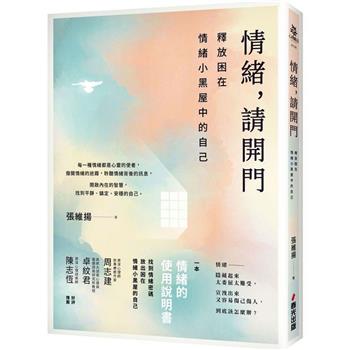你知道托斯卡尼人的口頭禪是什麼嗎?
per ora和per piacere,意思是及時行樂及隨你高興,
這樣你知道他們是如何輕鬆過生活的吧!
現在我們邀請你,一起來享受美好人生……
如何在自己家裡營造出托斯卡尼式的浪漫休閒風格喔!
我做過許多次白日夢,設想每個曾住在這些房間裡的義大利太太──她在那裡剝四季豆,搖孫兒的搖籃,剪下三十年無人照顧卻依舊盛放的粉紅色野玫瑰插在花瓶裡。現在我想邀請那些女人中的一個去我在加州的家,給她看巴摩蘇蘿如何搖身變到美國,在那裡生根,看那間房子如何迎接來自北方環舊金山灣的微風,坐擁宛如神聖不可侵犯的泰馬爾帕斯山的景色;看我花園裡的花草如何蓬勃的生長;看我桌上的餐飲如何變得多樣化……
繼風靡全世界的《托斯卡尼艷陽下》之後,托斯卡尼的吟遊詩人──芙蘭西絲.梅耶思,這次要教你將托斯卡尼風格的帶進生活各個面向:舉凡裝潢、美酒、美食、園藝、購物、娛樂中。書裡收錄有上百張全彩照片、二十五道全新的食譜,以及給旅行者與購物者的推薦清單,讓你輕鬆涵泳於托斯卡尼風情中。
如何創造托斯卡尼的風格:
◎ 活用杏黃色、古董藍等托斯卡尼色調於家中;把門畫上富有想像力的門框;使用與眾不同的彩繪家具;替牆壁抹上生動的壁畫。
◎ 開墾屬於你的托斯卡尼花園,在香草和花卉之間加入噴泉、葡萄藤架涼亭、和赤陶甕。
◎ 選擇最好的義大利酒,在托斯卡尼式的葡萄園享用午餐,活用芙蘭西絲傳授的美酒佳餚搭配祕訣。
◎ 到當地的古董市場尋找物超所值的寶貝,參考書裡的托運方法和幾個托斯卡尼城鎮的市集日。
◎ 運用琺瑯陶器和上等織品的桌巾,擺設極具托斯卡尼風味的餐桌。
◎ 嘗試易做且具有獨特風味的托斯卡尼料理。從橄欖油和聖酒,到傳統的手工麵條和麵疙瘩,芙蘭西絲親自獻上獨門菜單和食譜。
◎ 營造令人無法抗拒的環境,任何時候都好客的「開放之家」。
作者簡介
芙蘭西絲.梅耶思 Frances Mayes
成長於美國喬治亞州費滋傑羅城。除了暢銷兩百萬冊的《托斯卡尼豔陽下》之外,也是《美麗托斯卡尼》和《在托斯卡尼》、小說《天鵝》、讀詩者的教科書《詩歌的探索》,以及其他五本詩集的作者。其詩作與自傳性隨筆亦大量發表在歐美各重要文學期刊上,如《大西洋月刊》、《新英格蘭評論》、《詩刊》等,也定期為《紐約時報》、《美宅》、《食物與酒》撰稿,並任教於舊金山州立大學(文學創作)。
愛迪.梅耶思 Edward Mayes
六本詩集的作者。現與妻子芙蘭西絲.梅耶思在舊金山與義大利的科爾托納兩地輪流居住。
攝影者簡介
史提芬.羅斯菲爾德 Steven Rothfeld
住在加州的納帕谷。攝影作品除了每年出現在芙蘭西絲.梅耶思的「托斯卡尼樂趣」桌曆裡外,也曾刊登在許多其他書籍和月曆。著有《法國夢》、《義大利夢》、《愛爾蘭夢》和《請進》。他的個人網站:www.stevenrothfeld.com。
譯者簡介
林淑娟
台北市人,文字工作者。出版過二十幾本小說,譯作包括《美麗的哀傷》(臺灣商務)、《包法利夫人》、《小婦人續集》等逾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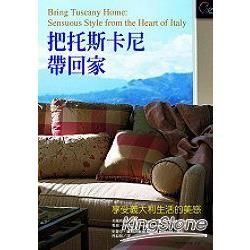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