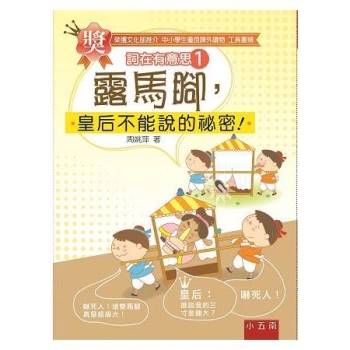◆一次療癒一顆心,我們終能療癒盧安達,以及我們的世界。
西元一九九四年,非洲中部的盧安達境內掀起腥風血雨,執政的胡圖族展開滅族大屠殺,三個月總共屠殺了約一百萬圖西族人,導致屍橫遍野,生靈塗炭,國家停擺。伊瑪奇蕾與其他七名圖西族婦女幸得一位胡圖族牧師收留,藏匿在窄小的衛浴間,度過漫長驚恐的九十一天……
˙我聽到那群殺紅眼的劊子手在呼叫我的名字,「伊瑪奇蕾在這裡……我們知道她就躲在某個角落……快把她找出來。」
「我已經殺了三百九十九隻蟑螂,殺了伊瑪奇蕾就剛好湊成四百,好極了。」
˙我的名字叫伊瑪奇蕾.伊莉芭吉札。這本書講的是我在這場史上最血腥的種族大屠殺期間,如何體悟到上帝的故事。
作者簡介:
伊瑪奇蕾‧伊莉芭吉札(Immaculée Ilibagiza)
生於非洲國家盧安達。在一九九四年盧安達種族滅絕大屠殺中,失去了大部分親人,四年後,她移民美國,服務於紐約的聯合國機構。目前全時間奉獻於公眾演講及著書,分享信仰與饒恕如何能夠療癒傷痛以及改變世界。二○○七年,她成立Left to Tell慈善基金會,幫助盧安達的孤兒,並獲頒「聖雄甘地國際和解與和平獎」(Mahatma Gandhi International Award for reconciliation and peace)。
史蒂夫‧艾文(Steve Erwin)
《紐約時報》暢銷書作者、得獎的新聞記者,與人合著七本書,目前正在撰寫第二部小說;他與擔任記者及作家的妻子住在紐約市。
譯者簡介:
傅振焜
東海大學哲學系畢業。曾任職時報出版、Discovery頻道。譯有《後資本主義社會》、《黃金的魔力》、《經營大師的22堂課》、《獵人之心》、《孤獨的呼喚》、《加拿大》、《鐵達尼號》、《佛洛伊德的近視眼》等書。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伊瑪奇蕾所經歷的恐怖、堅忍、療癒與寬恕的故事,使我對她非凡的靈性感到謙卑。身為盧安達人,我以我們能夠超越錯誤的差異觀點為榮,這個錯誤在一九九四年造成無數孩童及成人被殘忍地謀殺。伊瑪奇蕾的種族屠殺倖存者告白令人驚心動魄,給予我們希望去克服那些因著自私自利、毫無人性的人所製造出來的分裂。每個人都應該讀這本書──不論是倖存者或加害者。我盼望每個人都能體驗伊瑪奇蕾深刻的靈性轉化歷程,成為使國家合一、永續的鼓舞力量。
──盧安達第一夫人珍妮特.卡加米(Jeannette Kagame)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斷氣之前,替那些將他釘上十字架,並且在十字架下面嘲諷他的敵人向上帝禱告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路23:34)今天我們在本書的作者伊瑪奇蕾身上,又再一次看到這種饒恕敵人所發出的永恆愛的光芒。
──蔡茂堂(台北和平長老教會牧師,現已退休,積極於宣道服事)
二二八的陰影長期困擾台灣社會。或許是因為我國沒有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寬恕傳統,才會希望先有真相及道歉,再談和解及寬恕;但從伊瑪奇蕾的親身經驗中,我們看到的卻是她在加害者尚未道歉、要求寬恕時,就先選擇原諒對方,不讓仇恨在她身上停留生根,這才是本書中最寶貴的信息。
──嚴震生(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名人推薦:伊瑪奇蕾所經歷的恐怖、堅忍、療癒與寬恕的故事,使我對她非凡的靈性感到謙卑。身為盧安達人,我以我們能夠超越錯誤的差異觀點為榮,這個錯誤在一九九四年造成無數孩童及成人被殘忍地謀殺。伊瑪奇蕾的種族屠殺倖存者告白令人驚心動魄,給予我們希望去克服那些因著自私自利、毫無人性的人所製造出來的分裂。每個人都應該讀這本書──不論是倖存者或加害者。我盼望每個人都能體驗伊瑪奇蕾深刻的靈性轉化歷程,成為使國家合一、永續的鼓舞力量。
──盧安達第一夫人珍妮特.卡加米(Jeannette Kagame)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斷氣之...
章節試閱
序幕
我的名字叫伊瑪奇蕾
我聽到那群殺紅眼的劊子手在呼叫我的名字。
我們之間只隔著一道不及一吋的灰泥木板牆,他們的聲音冷酷、刺耳、堅決。
「伊瑪奇蕾在這裡……我們知道她就躲在某個角落……快把她找出來。」
現場有很多殺戮者,聲音吵雜。我想像得出那些向來愛護我的朋友、鄰人,正手持長矛、開山刀(大砍刀)在屋子裡四處穿梭,並不斷呼叫我的名字。
「我已經殺了三百九十九隻蟑螂,」其中有一人說,「殺了伊瑪奇蕾後,就剛好湊成四百,好極了。」
我一動也不動地蜷縮在一間隱密的小衛浴間角落,與另外七名為保命而躲藏的女子一樣,全都屏住氣息,以免這群殺人狂魔聽見。
他們的聲音撕裂我的軀體,我彷彿臥在通紅的煤堆上,即將焚身;又像有無數看不見的針尖刺穿了我,陣陣痛楚席捲而來。我從沒想過恐懼會造成身體如此極度的痛苦。
我試著吞嚥一下,但喉嚨堵住了,因為我口裡比沙漠還乾燥,完全沒有唾液;我閉上眼睛,祈望自己可以隱身,但他們的聲音愈來愈大。我心裡明白,他們抓到人絕不會手軟,因此腦子裡重複迴盪著一個念頭:一旦被抓,他們必會殺了我;一旦被抓,他們必會殺了我;一旦被抓,他們必會殺了我……。
殺戮者就在浴室門外。我知道他們無時無刻不在找我,不曉得開山刀砍進皮膚、深及入骨,會是什麼感覺?我想起哥哥、弟弟及爸媽,不知他們是生?是死?或許我們很快就會在天堂相聚。
我雙手合十,緊握父親送我的念珠,開始默禱:「主啊,求祢幫助我,別讓我這樣死去,千萬不要!別讓這群殺戮者找到我。祢在聖經裡說,我們祈求便得著……主啊,我現在就向祢祈求,求祢讓他們快快離去,別讓我死在這間浴室。主啊,求求祢救我!救救我!」
殺戮者終於走出屋外,我們這時才敢呼吸。他們是離開了,可是在往後的三個月,他們還返回搜查了好多次。我相信是主赦我不死,但在這九十一天裡(我和七名同伴心驚膽顫地躲藏在這衣櫃般大小的衛浴間),我也領悟到倖免於死與獲救是不一樣的事……而這個在大屠殺期間領悟的道理,教我要如何去愛仇視、追殺我的人,如何去寬恕殺害我親人的人;它影響我一生。
我的名字叫伊瑪奇蕾‧伊莉芭吉札。本書講的是,我在這場史上最血腥的種族大屠殺期間,如何體悟到上帝的故事。
第二章
圖西人起立
「圖西人,起立!」
我就讀的四年級班上,有六個小朋友聞聲起立,六張椅子往後刮過地板。我不知道怎麼回事,因為之前我一直是跟著母親上課。我十歲了,升級到小學中年級,今天是我第一天上學,而眼前的騷動令我困惑,因為我從未見過老師按種族點名。
「圖西人全都起立!」布霍洛老師大聲喊著,並用一根粗大的鉛筆在點名簿上一一核對打勾,輪到我時,他停下來,目不轉睛地瞪著我。
「伊瑪奇蕾,我說胡圖人起立時你沒有站起來,我說特瓦人(Twa)起立時你也沒有站起來,我剛剛說圖西人起立時你又沒有站起來。這是怎麼回事?」布霍洛老師臉上雖堆著笑容,但語氣不大好。
「老師,我不知道。」
「你是哪一族?」
「我不知道,老師。」
「你是胡圖人,還是圖西人?」
「我……我不知道。」
「出去!馬上離開教室,不知道你是哪一族人就別回來!」
我收拾課本,很丟臉地遮頭離開教室。就這樣在毫不知情的狀況下,經歷了盧安達族群分裂的第一堂課。那真是一記當頭棒喝!
我跑到校園,躲在矮樹叢後面,等待著達瑪辛下課。適才強忍的淚水,現在終於潰堤,我放聲哭泣,直到藍色制服逐漸被淚水浸濕為止。我並不明白方才是怎麼回事,實在很想回到班上,請我最好的朋友珍妮特解釋給我聽;方才老師喊胡圖人起立時,她有站起來,或許她明白老師為何會對我這麼凶。不過,我依然蹲在矮樹叢後面啜泣,直到達瑪辛發現我。
「誰欺負你了,伊瑪奇蕾?」我二哥以其十三歲的威信問道。達瑪辛一直是最保護我的人,若有誰欺負我,他就準備找對方理論,於是我把方才的事告訴他。
「布霍洛不是好人,」我二哥說,「別擔心,你就照我的話去做,下次他點名,你就跟著朋友一起起立。你朋友珍妮特起立,你就跟著起立。」
「他喊胡圖人起立,珍妮特就站了起來。」
「那老師喊胡圖人起立時,你就起立。假如我們的朋友是胡圖人,那我們應該也是。我們都是一樣的人,沒有什麼分別,不是嗎?」
我當時年紀小,不可能懂,但達瑪辛對盧安達的族群問題也同樣一無所知……這是很奇怪的事,因為我們是當地受到最好教育的小孩,居然不知道自己是哪一族人。每天放學後,我們有九十分鐘的自由時間,然後就在母親的監督下,進客廳做功課;吃晚飯前一個鐘頭,父親會接替母親,並在客廳中間豎起一塊大黑板,然後詢問數學、文法、地理上的問題,要我們以粉筆作答。
然而,父母親從不教我們有關盧安達的歷史,所以我們不知道盧安達有三大族群:胡圖族占多數,圖西族占少數,還有極少數的特瓦族分布在森林地帶,他們的體型較矮小。父母親也從不讓我們了解,當初先後殖民的德國及比利時政府,把盧安達既有的社會結構(圖西國王統治下的君主政體,為盧安達提供了數世紀的和平與和諧)轉變成一個不公平、依種族劃分的階級體系。比利時殖民政府偏袒較少數的圖西貴族,讓他們獲取統治階級地位,因而,圖西人能獲得較好的教育機會,以便把國家管理好,為比利時統治宗主帶來較大的利益。比利時殖民政府還推行身分證加註種族別的政策,以便於區別這兩大族群,卻也加深兩族間原有的裂痕。這些魯莽、愚蠢的錯誤政策,引起胡圖人長期的忿忿不平,也種下日後血腥屠殺的禍根。
後來,圖西人要求更高程度的自治,比利時殖民政府為了抵制他們,便在一九五九年鼓動胡圖人發動血腥叛亂,一舉推翻了圖西人的君主體制。在接下來幾年當中,約有十萬名以上的圖西人,死於胡圖人的復仇殺戮。到了一九六二年,比利時人退出盧安達,胡圖人建立穩固的政權,圖西人自此淪為次等公民,面臨胡圖極端分子的迫害、暴力與殺戮,並在數十年間,屢屢發生種族屠殺,導致成千上萬的人喪生。暴力殺戮是隔一陣子才發生一次,但不平等對待則時時刻刻都在發生。胡圖政府沿襲比利時統治時期的作法,在身分證件上加註種族別,在在使得種族區隔得更明顯,也更方便為之。
但是,父母親並不想讓我們了解這些歷史──至少在我們年紀還小時是如此。他們從來不跟我們提起有關種族歧視、大屠殺、種族清理或身分認同的話題──這些事都不屬於我童年世界的一部分。
我們家對任何種族、宗教的人都十分歡迎。對我父母而言,對方是胡圖人或圖西人,跟他是個怎樣的人一點關係也沒有,只要你是好人,他們便會張開手臂歡迎。不過,父母親曾受過胡圖族極端分子的驚嚇……現在回想,我還依稀記得其中一二。
當時我才三歲,並不了解怎麼回事,但我記得火光照亮夜空,母親緊緊抱住我逃離家園。那是發生在一九七三年軍事政變的時候,當時很多圖西人或遭受迫害,或被迫逃離家園,或橫死街頭;而在我們那個地區,胡圖族極端分子把圖西人的房子一家接著一家放火燒毀,當火苗竄上山丘往我們燒過來時,我們全家正一起站著俯瞰下方的基伏湖。於是,我們趕緊逃到鄰人魯塔卡米茲家裡,他雖是胡圖人,但跟我們家交情很好,所以他把我們藏匿起來,直到殺戮與放火平息下來。事後我們回到家時,發現只剩一片廢墟餘燼。
父母親著手重建家園,但絕口不提這件事,至少不曾對我們小孩提起過。即使早在一九五九年,發生類似的反圖西族運動時,他們也成為箭靶,但我從未聽過他們說過一句貶損胡圖人的話。他們對胡圖人並無偏見;相反地,他們相信受邪惡力量驅使而行惡的人,無種族之分,不論哪個種族都會有人著魔似地犯下罪行。為了不想讓子女在成長過程中,因為自己是圖西人而有執念妄想或自卑感,父母親決定不理會社會與政治實況,教導我們人人生而平等的道理。
話說至此,你應該不難理解,當布霍洛老師因我不知道自己是哪族人而大發脾氣時,我為何會茫然不知所措了。
那天,達瑪辛扶著我的肩膀,陪我走回家。我們兩人都感受到某種令人不安的力量,但不知道它是什麼。吃晚飯時,我告訴父親學校裡發生的事。他變得沉默,然後問我,被趕出教室後,蹲在矮樹叢裡哭了多久?
「幾乎一整天,爸爸。」
父親放下叉子,不再進食──每個人都感覺得出他內心的氣憤。「我明天會去找布霍洛談。」他向我保證。
「可是,爸爸,我到底是哪一族人?」
「哦,現在別煩惱這個問題。明天我跟你的老師談過之後,我們再來討論。」
我很想問他,為什麼不現在就告訴我是哪一族人;但我們不能質問長輩,假如父親要迴避問題,我想一定有他的理由。只是我相當受挫,無法理解為什麼一談到種族問題,每個人便憂心忡忡!
翌日,父親去找布霍洛老師理論,但他並未告訴我結果為何,也未如先前所言,跟我討論種族的歸屬問題。直到下一個禮拜,布霍洛老師再次進行種族點名時,我才有了答案。我想,父親的話必定令他感到羞愧,因為在點名前他召喚我到他的桌前,說話的語氣比上週溫和多了。
「伊瑪奇蕾,等會兒我喊到『圖西人』時,你就起立。」
我開心地回到座位,心想:「那我就是圖西人囉,好極了!」我對圖西人毫無概念,但無論如何,我以身為圖西人為榮。班上的圖西族同學極少,我想這使我們變得很特別,而且「圖西族」聽起來很可愛,說起來也很令人愉快。只是,我依然看不出圖西人與胡圖人之間有什麼確切的不同;倒是特瓦人身材非常矮小,很容易一眼就認出。不過,特瓦人的小孩很少上學,所以我很少看到他們。
圖西族與胡圖族的差異比較難以辨認。很多人總以為圖西人的身材較高,膚色較白,鼻子較窄;而胡圖人的身材較矮,膚色較深,鼻子較寬。其實不然,由於兩族通婚已有數世紀之久,基因早就相互混和了,加上胡圖人與圖西人都說盧安達語(Kinyarwanda),擁有共同的歷史,所以文化也幾乎相同:我們唱同樣的歌,耕作同樣的土地,上同樣的教堂,信奉同樣的神,生活在同樣的村落、街道及大致相同的房子裡。
在孩子的眼中(至少在我眼中),我們似乎都相處和睦。我到胡圖族好友珍妮特家裡吃晚飯的次數,,跟她到我家吃晚飯的次數都難以估算。在小女孩的年代,只有每星期一次的種族點名時間,我才會想到盧安達有不同種族,但這也不至於太困擾我,因為我還不需要了解種族間的差別待遇。
也就是說,等我要上高中時,才了解什麼是種族差別待遇。
十五歲時,我讀完八年級,在班上六十名學生當中,我的成績名列第二,平均九十四分,大幅領先其他同學,只比第一名(一位圖西族男孩)低兩分。憑這麼優異的成績,要拿獎學金進一流的公立高中就讀,絕對綽綽有餘,因此在學期結束返家時,我夢想著自己穿新制服,離家到一所全部法文授課的好學校求學的生活。
接著我計畫上大學,然後呢?誰曉得?或許我會當飛機駕駛、教授甚或心理學家(此時,我幾乎已放棄當修女的童年夢想)。父母親一直教導我,即使是出身於馬塔巴這樣小村落的女孩,也可以成為有成就的人物。
孰料我的壯志不過是一場空夢。我不知道每週進行的種族點名,原來暗藏一個惡意的目的:對圖西族孩童進行種族隔離;是所謂「族群平衡(配額)」計畫的一部分。
這項名為族群平衡,實為種族歧視的計畫,是由哈比里亞馬納(Juvenal Habyarimana)總統所推動,這位在一九七三年軍事政變中取得政權的胡圖人宣稱,政府必須依據國內各種族的組成比例來訂定學校與公務機關的種族配額。由於胡圖族大約占盧安達總人口的八五%,圖西族佔一四%,特瓦族佔一%,所以大部分的工作與就讀機會都保留給胡圖人。這項計畫的真正目的是不讓圖西人進入高中、大學與好的工作單位,讓他們永遠淪為次等公民。
準備上高中的前幾個禮拜,才終於明瞭「族群平衡」的真正用意。有位我們視如家人的鄰居來家裡晚餐,告訴我們,獎學金名單剛張貼在社區中心,可是上面沒有我的名字。雖然我的成績優異,還是被刷了下來,只因為我是圖西人,就連那位成績最好的圖西族男孩,命運也和我相同;所有名額都留給胡圖族的學生,即使他們的成績落後很多。
父親把椅子推離餐桌,緊閉雙眼許久。我知道家裡供不起我讀私立學校,因為所需的學費比公立學校貴上十倍之多,而我的兩位哥哥又在外讀書,家裡手頭吃緊。此外,跟經費充裕的公立高中相比,私立高中的辦學遜色許多,不但師資、教學較差,校舍也較簡陋。
「伊瑪奇蕾,別擔心,我們會另外想辦法供你念書。」父親終於有反應了,但隨後他便藉故離席,沒吃完那頓飯就進了房間。
「別放棄希望,」母親抱著我說,「我們會向上帝祈禱。現在你趕快吃飯。」
晚飯後,我把自己鎖在書房內哭泣。沒想到我一心向學,到頭來受更高教育的夢想,卻在一夕間破滅,一思及將來,我就不禁顫抖,因我已經預見一個未受教育的單身女子,在盧安達社會裡會受到的對待:沒有權利,沒有希望,不受尊重。如果連高中都沒讀,我除了乖乖在家等著某個男人娶我為妻之外,別無選擇。我的未來黯淡無光,而我才十五歲!
翌晨,全家吃早餐時,父親並未出現在餐桌上。
「他出去尋找奇蹟!」母親解釋說,「他去查訪一些私立學校,看看能否幫你註冊入學。」
「可是,媽,學費很貴呢!我們恐怕……。」
「噓,」她打斷我的話,「我不是告訴過你,永不放棄希望嗎?」
後來我才知道,為了供我上私立高中,一大清早,太陽都還未升起,父親就出去賣了兩頭牛;而在盧安達,牛是身分地位的表徵,極具價值──賣一頭牛是奢華過度,賣兩頭牛則是自尋絕路。然而,父親還是決意讓我受教育,他拿著賣牛的錢,往南開了三個鐘頭的車程,風塵僕僕地前往一所新籌設的私立高中,繳了我第一學年的學費。父親雖然不善表達,但他對我的愛毋庸置疑。
數星期後,我打包行李,準備前往就讀。珍妮特擁抱著我,兩人哭成一團,最後彼此相約要常寫信聯絡。母親強忍淚水,一遍遍地親吻我;維雅納則因我走後,家裡只剩他一個小孩,所以躲進房間,不肯跟我道別。父親開車送我離開時,許多鄰人都出來揮手告別。離開馬塔巴,我感到傷心失落,但也渴望展開新生活……
數月後,我放暑假返家,有天達瑪辛連跑帶跳地跑回屋內,大聲叫喊:「伊瑪奇蕾!伊瑪奇蕾!我剛看榜單,你通過甄試了!非洲聖母中學(Lycée de Notre Dame d’Afrique)錄取你了。它可是盧安達的一流學校,從我們學校一路走下去就到了!」
當時全家人都坐在客廳,一聽到達瑪辛的話,每個人都樂瘋了。我從座椅上一躍而起,大叫著:「感謝上帝,感謝上帝!」然後邊用手在胸前劃十字,邊跳著勝利之舞。母親的眼中泛著淚光,父親則高聲說:「這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喜悅!兩年來我每天都跪下祈禱,祈求你能進入那所學校就讀。現在上主應允了我的禱告!」
「你一定很聰明,雖然你是女生。」艾瑪伯嘲笑我,但我看得出來,他很替我高興。
達瑪辛露出燦爛的笑容,替我驕傲得快滿爆了。
那晚,我們開了家庭派對,那是長久以來我們最開心的慶祝會之一。聖母中學是一所卓越的女校,國內很多政治人物的女兒都在該校就讀。上了這所學校,不但可接受最好的教育,我的父母也不用再為學費煩惱;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它遠在吉塞尼(Gisenyi)省,從馬塔巴到那裡要花四個鐘頭的車程,而且沿途頗危險,所以父母親恐怕無法經常去探望我。再者,它位於胡圖族佔優勢的地區,當地胡圖人對圖西人的公開敵視眾所周知。
「別擔心了,它是女子學校,」達瑪辛說。「設有高牆及許多警衛,可以保護你的安全。而且,我的學校就在附近,每個月我都可以去探望你。」
我一見到聖母中學就愛上它了。校舍寬敞優美、明亮乾淨,教室也漆得明亮鮮豔,校園裡更種滿五顏六色的花,同時,高聳的安全圍牆還繞整個校區,讓我很有安全感。在這裡念書我很開心,我知道父親也會很開心,尤其當修女告訴我們在飯前飯後都必須禱告時。
莎拉是我在這裡最先認識的朋友之一,她是胡圖人,但我們情同姊妹,她還邀請我到盧安達的首都吉佳利(Kigali)和她的家人見面。對我這個鄉下女孩來說,到大城市一遊真是大開眼界,尤其是第一次近距離看到飛機;莎拉和我在晚上到機場,只見跑道在螢光下閃閃發亮,當巨大的飛機從天而降時,著陸燈閃爍著紅、白、綠光,聽到這些巨無霸轟隆作響的引擎聲,我頓時張口結舌。
「哇,你瞧!」我驚呼,莎拉笑得彎下腰。「我想我現在見過世面了。」
克萊曼婷也是我入學第一天認識的朋友,她是一位亮麗的女孩,皮膚光滑細緻,還有雙美麗的眼睛,外貌就像美國雜誌的模特兒。她在一大群新同學當中發現我時,就直直朝我走來。雖然我已比大多數的同學高,但她比我還高,至少有六呎;我們是從身高判斷彼此為圖西人。
「圍牆外面遍布著不友善的胡圖人,像你這麼漂亮的圖西女孩大老遠地跑到北方來,該怎麼過活喲?」她笑著說。「那我們以後可得攜手扶持、相互照顧囉。」我們立刻就相處融洽。
克萊曼婷說得沒錯,學校的圍牆外面遍布著不友善的面孔,所以走出校門相當冒險,常讓人卻步──每當我冒險出去時,總覺得有很多雙眼睛在注視我,同時聽到他們語帶威脅地竊竊私議著「圖西人」。管理學校的神父與修女們都相當謹慎,絕不讓學生與當地居民在同一時間上教堂作彌撒,他們還嚴格規定,若沒有人護送,不得擅自外出。雖然學校外頭總讓我心驚膽跳,但在學校的圍牆內,我從未感受到絲毫的種族歧視,老師們從來不會進行種族點名,而大部分的女同學雖都是胡圖人,但我們相親相愛,宛如一個大家庭般。
我一直窩在學校用功讀書,努力避免思鄉想家的情緒;不過,我真的很想念爸媽、哥哥,甚至懷念起維雅納的糾纏黏人。講到小弟,在我負笈離家幾個月後,他寄來一封讓我既感動又苦惱的信,上面寫道,他非常地想我,我離家後,他經常睡不著,有時夜裡會看到鬼在各個房間走來走去,嚇得他趕緊跑出屋外。這封信簡直讓我心碎。沒錯,以前在家我經常和維雅納爭吵,如今我才了解自己在他心中有多重要;留他孤單一人,我很內疚,但願以後能做個好姊姊。
達瑪辛真的信守承諾,每個月都來看我一次,我們會一起坐在草地上,一聊數個鐘頭。他總會給我不錯的建議,特別是有關學習方面。
「禱告吧,伊瑪奇蕾。做功課前或準備考試時,你就禱告,然後盡力而為。」我遵行他的話,尤其在準備數學考試時,禱告得更勤奮,而我的成績也一直相當優異。
達瑪辛來探望我時,我的女伴們都想知道,那位跟我談話許久的帥哥是誰。
「是我哥哥,達瑪辛。」我驕傲地回答。
「不是吧,沒有人會跟哥哥相處得這麼好,你看來很陶醉的樣子。」
我很幸運生命中有摯愛的達瑪辛相伴……
序幕
我的名字叫伊瑪奇蕾
我聽到那群殺紅眼的劊子手在呼叫我的名字。
我們之間只隔著一道不及一吋的灰泥木板牆,他們的聲音冷酷、刺耳、堅決。
「伊瑪奇蕾在這裡……我們知道她就躲在某個角落……快把她找出來。」
現場有很多殺戮者,聲音吵雜。我想像得出那些向來愛護我的朋友、鄰人,正手持長矛、開山刀(大砍刀)在屋子裡四處穿梭,並不斷呼叫我的名字。
「我已經殺了三百九十九隻蟑螂,」其中有一人說,「殺了伊瑪奇蕾後,就剛好湊成四百,好極了。」
我一動也不動地蜷縮在一間隱密的小衛浴間角落,與另外七名為保命而躲藏的...
推薦序
二版序
〈選擇寬恕,重獲自由〉
文/嚴震生
《我的名字叫伊瑪奇蕾──種族滅絕倖存者的真實告白》的新版即將問世,我在第一版的中文譯本在台灣問世時,有幸能為該書寫序,這次出版社再度邀約,我也同作者在新版中加上後記一般,想將這些年在臺大及政大政治系擔任非洲政治課程的一些心得,以及對作者伊瑪奇蕾.伊莉芭吉札一路走來將愛傳播的感染力,做出回應,並介紹給讀者。
幾乎所有上過我非洲政治課的學生,都有機會觀看《盧安達飯店》這部記載盧安達種族滅絕悲劇的好萊塢電影。這是因為我的教科書中有一章是討論非洲的認同及族群問題,而盧安達的胡圖(Hutu)與圖西(Tutsi)族間的矛盾與衝突,則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案例研究。或許是因為想要忘記這段悲劇,或許是想要將此陰影完全從民眾的心目中抹去,盧安達在種族滅絕十週年時,將族群(ethnicity)從教科書中刪除,胡圖與圖西都不再被使用,全國都是盧安達人。這是因為執政者相信如果人民對族群的認知來自於學習,那也可以透過學習將這個族群的概念除去。真的嗎?這會不會是一種鴕鳥心態,沒有真實地面對問題,因為長期以來就存在的標籤,不是能靠政府的政策宣示及學校教育就可以改變的。
伊瑪奇蕾在她的書中,不僅敘述她如何在種族滅絕的屠殺行動中倖存,也一再強調因為她篤信上帝在主禱文中所說:「赦免我們的罪,如同我們免了人的罪」,讓她選擇饒恕那些讓她失去家人的加害者。這本書曾經榮獲暢銷書的第一名,也被許多教會學校挑中,成為必讀的課外讀物。由於故事感人,伊瑪奇蕾也被邀請到學校演講,分享她從父母的愛中所得到愛人的力量,及如何在虔誠的信仰中認識到什麼是饒恕。雖然她的母語是法語,但上帝讓她在躲避大屠殺的三個月期間,學習到英語,也因為有英語的表達能力,伊瑪奇蕾成為一個勵志演講者(motivational speaker),讓上帝使用她幫助無數過去活在仇恨、無法饒恕的人,走出他們的困境。
我在本書第一版中提到二二八事件六十年的一些感觸,如今七十年已經過去了,但該事件所造成的傷痕似乎還無法完全消除。我們社會當中並非沒有饒恕加害者的案例,上個世紀九○年代初期在「台北神話KTV」縱火案中喪失弟弟的杜花明,選擇原諒加害者湯銘雄,還帶領他相信上帝,讓他在走上死刑前能夠坦然面對自己的罪,這個故事還拍成紀錄片「回家」,感動不少受刑人及受害人家屬。或許因為杜花明並不是一個勵志演講者,或許這僅是一個刑事案件,因此饒恕的力量還沒有在台灣社會生根。
個人祈禱,希望過去白色恐怖受害者,或是二二八受害者的家屬,特別是有知名度的公眾人物,願意做出像伊瑪奇蕾一樣的選擇,協助我們弭平過去的傷痕。伊瑪奇蕾在新版的後記中,提到她如何重建家園,並在落成時邀請對她遠房親戚加害的胡圖族人與會,然後宣布這個充滿愛及饒恕的地方,是屬於該村落的,當地的圖西族及胡圖族則是共同在上帝面前祈求和平、寬恕與祝福,這是一幅多美的圖畫,而這一切都是因為伊瑪奇蕾拋棄報復,選擇饒恕,因為她對加害者的態度,有如《聖經》〈路加福音〉耶穌向上帝的禱告一般:「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如果我們選擇仇恨,就可能永遠活在想要報復的轄制中,但若能選擇寬恕,或許能夠脫離枷鎖,重新獲得自由。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初版序二
〈父啊!赦免他們〉
文/蔡茂堂
我在淚水與讚嘆中一口氣看完《我的名字叫伊瑪奇蕾》》。這本書是關於於一九九四年四月六日到七月中旬約百日期間,發生在盧安達由胡圖族激進民兵殘殺圖西族約百萬人的滅族大屠殺慘案。伊瑪奇蕾當時是二十四歲的大學生,在這慘絕人寰的大災難中,她的父母、兄弟以及許多親友都被暴民殘殺。她也因為身為圖西人而被鎖定為追殺對象。
伊瑪奇蕾將自己在這樁慘案中的苦難遭遇以及心靈轉化過程,在本書娓娓道來。大屠殺開始時,她的父親勸她投奔一位胡圖族的基督教穆林齊牧師,接受他的藏匿與保護。穆林齊牧師冒著生命危險收容了八位圖西族婦女,把她們藏在家裡一間隱密的小浴廁中。伊瑪奇蕾與她們擠在這個動彈不得的黑暗浴廁中,常常遭受暴民反覆搜察追殺的恐懼與害怕。在這樣的死蔭幽谷陰影中,伊瑪奇蕾的天主教信仰帶給她無比的安慰與盼望。她養成長時間以默禱與上帝親近的習慣以及積極正面的思想。
當伊瑪奇蕾發現她的父母與兄弟都被她所認識且熟悉的浮圖族鄰居凌辱並且殘殺時,她幾乎完全崩潰,內心被強烈的仇恨與報復的衝動所煎熬。上帝用幾個神奇的夢境來撫慰她的哀傷與絕望,上帝也用主耶穌十字架上那赦免敵人的大愛來轉化她的心靈。她在冥想中似乎聽見上帝親自對她說:「你們都是我的孩子,殺人者與被殺者都是上帝所疼愛的孩子。」經過內心長久的掙扎,她終於戰勝心中愁恨報復惡靈的影響,能夠當面向那位殘殺她父母兄弟並且一直要追殺她的費利先說出:「 我原諒你。」這句感人肺腑的話。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斷氣之前,替那些將他釘上十架以及在十架下嘲諷他的敵人向上帝禱告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路23:34)教會歷史上首位殉道者司提反在被暴民用石頭打死前,也為那些暴民禱告,他跪下大聲喊著說:「主啊,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徒7:60)今天我們在這本書的作者伊瑪奇蕾身上,再次看到這種饒恕敵人所發出來那永恆愛的光芒。
(本文作者為台北和平長老教會牧師,現已退休)
二版序
〈選擇寬恕,重獲自由〉
文/嚴震生
《我的名字叫伊瑪奇蕾──種族滅絕倖存者的真實告白》的新版即將問世,我在第一版的中文譯本在台灣問世時,有幸能為該書寫序,這次出版社再度邀約,我也同作者在新版中加上後記一般,想將這些年在臺大及政大政治系擔任非洲政治課程的一些心得,以及對作者伊瑪奇蕾.伊莉芭吉札一路走來將愛傳播的感染力,做出回應,並介紹給讀者。
幾乎所有上過我非洲政治課的學生,都有機會觀看《盧安達飯店》這部記載盧安達種族滅絕悲劇的好萊塢電影。這是因為我的教科書中有一章是討論非洲的認同及族...
目錄
二 版 序 選擇寬恕,重獲自由 嚴震生
初版序一 不再讓仇恨生根 嚴震生
初版序二 父啊!赦免他們 蔡茂堂
序 言 在神,凡事都能!
序 幕 我的名字叫伊瑪奇蕾
第一篇:風起雲湧
1. 恆春福地
2. 圖西人起立!
3. 進階學習
4. 離家上大學
5. 返家
6. 無法返校
7. 牧師的家
8. 手足離別
第二篇:銷聲匿跡
9. 藏身衛浴間
10. 面對憤怒
11. 寬恕與仇恨間的掙扎
12. 無友可依
13. 孤兒不孤
14. 語言天賦
15. 意外的救星
16. 堅定信念
第三篇:邁向新生
17. 自由的代價
18. 達瑪辛的最後一封信
19. 營地的舒坦
20. 投奔反抗軍之路
21. 奔向吉佳利
22. 上帝的安排
23. 埋藏亡者
24. 寬恕生者
後記 新愛情,新生活
二○一四年版後記
二 版 序 選擇寬恕,重獲自由 嚴震生
初版序一 不再讓仇恨生根 嚴震生
初版序二 父啊!赦免他們 蔡茂堂
序 言 在神,凡事都能!
序 幕 我的名字叫伊瑪奇蕾
第一篇:風起雲湧
1. 恆春福地
2. 圖西人起立!
3. 進階學習
4. 離家上大學
5. 返家
6. 無法返校
7. 牧師的家
8. 手足離別
第二篇:銷聲匿跡
9. 藏身衛浴間
10. 面對憤怒
11. 寬恕與仇恨間的掙扎
12. 無友可依
13. 孤兒不孤
14. 語言天賦
15. 意外的救星
16. 堅定信念
第三篇:邁向新生
17. 自由的代價
18. 達瑪辛的最後一封信
19. 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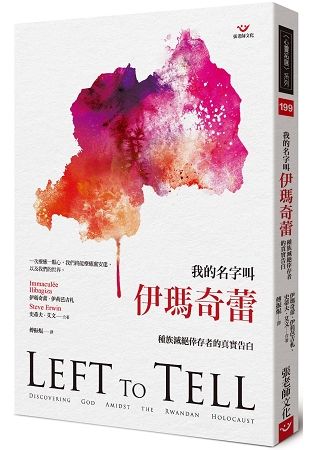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