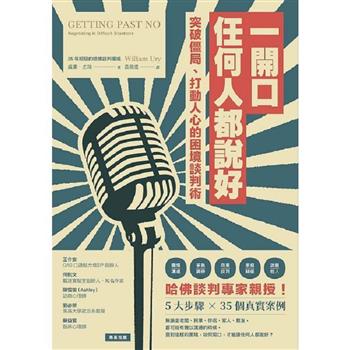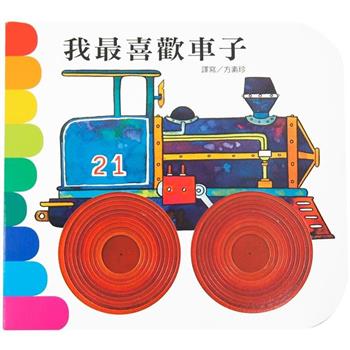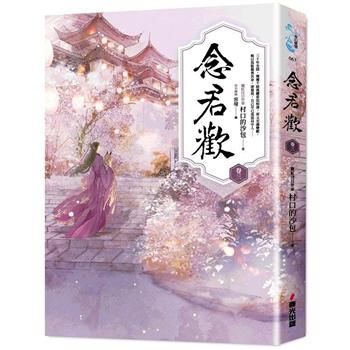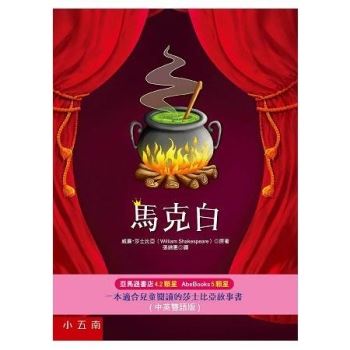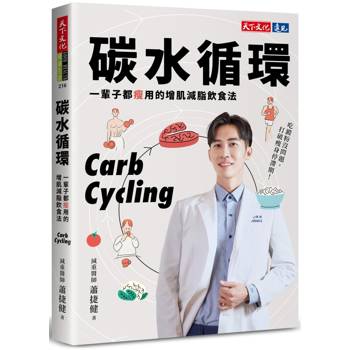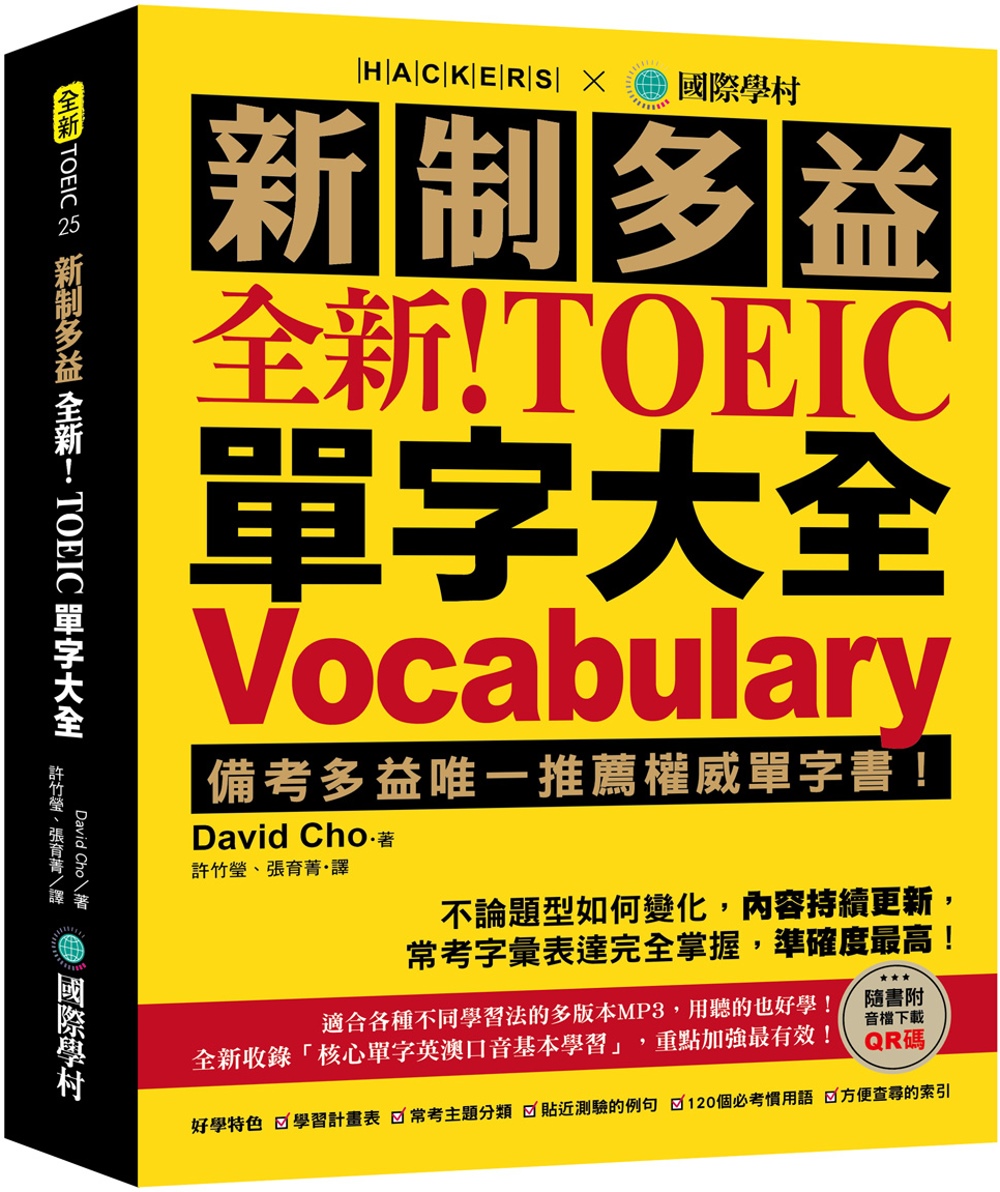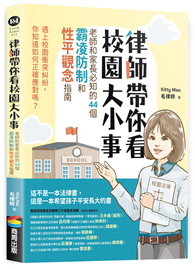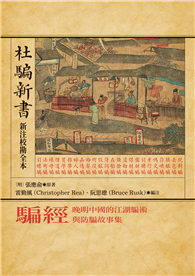書寫植物之餘,
以美學與知識為文字上妝。
百餘張圖鑑與引人入勝的植物研究史記述,
近七百年來的植物插畫流變,
十五世紀至今的植物藝術歷史,
藝術性、科學性與印刷技術的交流與整合。❶植物分類工作者暨彭鏡毅博士紀念獎得主——林哲緯 審定
➋植物插畫家 王錦堯.字耕農 古碧玲.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副教授 林政道.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館暨臺灣大學生態演化所教授 胡哲明.野花亭植物繪畫 粉專版主 紀瑋婷.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洪廣冀.生態插畫家暨作家 黃瀚嶢.生物繪圖師 葉書謹.植物學家 董景生.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助理教授 楊智凱.生態藝術繪者 鄭杏倩.作家 劉克襄——驚艷推薦
每位藝術家的選擇和妥協都反映了他們所處的時代、觀眾和科學假設:「植物插圖、是過渡點,插圖畫家是生物體與我們所認為的對該生物體的了解之間的過濾器。」
❁❉✤
「《妝花》有著引人入勝且精心挑選的植物插畫,並巧妙地結合了明晰易讀的植物學研究及科學分析。作者哈里斯在剖析藝術、科學和出版之間的關聯時有獨特的優勢,他的書涵蓋了過去五百年來大家知之甚詳的領域,也觸及讀者並不熟悉的範圍。本書內容豐富,將吸引各類讀者,無論他們關心的是植物、花園、歷史或這些主題之間錯綜複雜的關聯。」——馬克.內斯比特(Mark Nesbitt),邱園(Kew Garden)—英國皇家植物園跨領域研究的資深研究主管
⚘
「引人入勝、研究細緻,全面考察了植物插圖透過藝術和科學的歷史歷程。哈里斯使用罕見圖像,憑藉對主題的深刻理解,清楚展示了他對植物的熱愛。」 ——瓦萊麗.奧克斯利(Valerie Oxley),謝菲爾德植物園(Sheffield's Botanical Gardens)植物學學會主席
⚘
「本書具有令人震撼的視覺效果和驚人的範圍,是一部植物插畫史,具備經典參考書的所有要素。」——克麗斯坦.芮比(Kristen Rabe),「foreword review」
⚘
「科學植物插畫在文藝復興時期蓬勃發展,在十八世紀欣欣向榮,在十九世紀因攝影術興起而式微。如今,植物插畫普遍被視為藝術的一環,但牛津大學植物標本館館長哈里斯認為它依舊是『有科學用途的藝術』,其存在是為了記錄、展示和傳遞植物的科學資料。這本有關植物學歷史的著作點綴著了專業文獻以外並不常見的精緻插畫,將藝術和科學巧妙整合在一起。」——《自然》(Nature)期刊
⚘
「哈里斯是傑出的文字匠人,他寫作充滿知識、智慧和熱情。本書除了對主題極其博學和全面的描述之外,還帶給人一種愛的勞動的感覺……《妝花》是對植物插圖藝術和科學的一次迷人、真實的植物學探索。」——《Plant Cuttings》
⚘
「科學植物插圖是藝術家、科學家和出版商之間的合作。本書探討了自十五世紀中葉以來它們的演變、它們如何被用來傳達有關植物的科學思想以及人們對植物圖像的看法如何變化。」———《Garden Answers》
❁❉✤
妝花∣人們對於圖像的解讀會隨時間而改變,但植物插畫作為一種準確觀察和記錄而來的資料,可以是永存不朽的科學紀錄。然而,植物插畫演進歷程與科學觀念之間的互動豐富、複雜且微妙。藝術家和科學家的工作都會受到當下時空環境所影響。透過十五世紀中期至今的植物插畫,本書探討科學和藝術之間的交流,揭示植物插畫如何用於傳遞與植物相關的資訊,以及人們對植物學圖像的看法如何發生改變。從探討繪師和印刷師在呈現科學資料與理論時運用的手法,乃至近東地區的植物插畫起源,以及寫實畫作與理想形象的差距、繪師先備知識的作用,圖像與文字的整合。繼之為植物學簡史,著眼於插畫如何在植物的命名和分類、生理學和實驗以及演化和遺傳方面呈現重要觀察結果。不一樣的繪師與野外實察方式,對於發掘生物亦有多樣性貢獻。最終,將之用於教育,提升植物插畫在植物科學理論傳播中的角色。書中收錄的圖像凸顯植物插畫的科學用途,挑戰將植物插畫視為一門美學的既定觀念。不同時期的植物插畫繪師都積極運用當下的技術優勢,例如,光學技術的發展帶來了更清晰的視野,化學技術的進步催生了新的顏料,而工程技術的突破則與新的印刷工藝有關。如今在全球課題中,植物圖像和植物本身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包括不斷膨脹的糧食需求、地球生物多樣性的保存以及環境韌性的培養。對於二十一世紀的植物插畫繪師與共事的科學家而言,他們的考驗是要結合傳統插畫和攝影技術的優勢,以便在捕捉和儲存資料時發揮加乘效果,成功將精確的植物資訊傳達給形形色色的受眾。
作者簡介:
史蒂芬.A.哈里斯∣牛津大學植物科學系副教授兼標本館館長,著有《向日葵》(Sunflowers,2018)、《從根到種子:牛津植物學四百年》(Roots to Seeds: 400 Years of Oxford Botany,2021)等書。其研究聚焦於分子標誌(molecular marker)在進化生物學和保育生物學上的應用,特別是雜交、多倍體、人為介入的植物運動對演化的影響以及保育遺傳學。此外,哈里斯關注在演化研究中,以標本室的植物標本作為DNA來源所產生的問題,他也對植物學的歷史深感興趣。
譯者簡介:
王立柔∣臺大中文系及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畢業。自二○一三年起從事文字工作,至今探索過的領域包括新聞、翻譯、創作及口述影像撰稿,期盼未來能在每項專業上都持續精進。
林庭如∣畢業於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口譯組,目前從事英、粵語自由口筆譯工作,以藝術文化與行銷內容為主。近期譯作包含 《麥肯錫:競爭者的下一步》、彭定康《香港日記》 、《改變未來的100件事:2023年全球百大趨勢》等。譯作賜教:ryeryelin@gmail.com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妝花》有著引人入勝且精心挑選的植物插畫,並巧妙地結合了明晰易讀的植物學研究及科學分析。作者哈里斯在剖析藝術、科學和出版之間的關聯時有獨特的優勢,他的書涵蓋了過去五百年來大家知之甚詳的領域,也觸及讀者並不熟悉的範圍。本書內容豐富,將吸引各類讀者,無論他們關心的是植物、花園、歷史或這些主題之間錯綜複雜的關聯。」——馬克.內斯比特(Mark Nesbitt),邱園(Kew Garden)—英國皇家植物園跨領域研究的資深研究主管
⚘
「引人入勝、研究細緻,全面考察了植物插圖透過藝術和科學的歷史歷程。哈里斯使用罕見圖像,憑藉對主題的深刻理解,清楚展示了他對植物的熱愛。」 ——瓦萊麗.奧克斯利(Valerie Oxley),謝菲爾德植物園(Sheffield's Botanical Gardens)植物學學會主席
⚘
「本書具有令人震撼的視覺效果和驚人的範圍,是一部植物插畫史,具備經典參考書的所有要素。」——克麗斯坦.芮比(Kristen Rabe),「foreword review」
⚘
「科學植物插畫在文藝復興時期蓬勃發展,在十八世紀欣欣向榮,在十九世紀因攝影術興起而式微。如今,植物插畫普遍被視為藝術的一環,但牛津大學植物標本館館長哈里斯認為它依舊是『有科學用途的藝術』,其存在是為了記錄、展示和傳遞植物的科學資料。這本有關植物學歷史的著作點綴著了專業文獻以外並不常見的精緻插畫,將藝術和科學巧妙整合在一起。」——《自然》(Nature)期刊
⚘
「哈里斯是傑出的文字匠人,他寫作充滿知識、智慧和熱情。本書除了對主題極其博學和全面的描述之外,還帶給人一種愛的勞動的感覺……《妝花》是對植物插圖藝術和科學的一次迷人、真實的植物學探索。」——《Plant Cuttings》
⚘
「科學植物插圖是藝術家、科學家和出版商之間的合作。本書探討了自十五世紀中葉以來它們的演變、它們如何被用來傳達有關植物的科學思想以及人們對植物圖像的看法如何變化。」———《Garden Answers》
名人推薦:「《妝花》有著引人入勝且精心挑選的植物插畫,並巧妙地結合了明晰易讀的植物學研究及科學分析。作者哈里斯在剖析藝術、科學和出版之間的關聯時有獨特的優勢,他的書涵蓋了過去五百年來大家知之甚詳的領域,也觸及讀者並不熟悉的範圍。本書內容豐富,將吸引各類讀者,無論他們關心的是植物、花園、歷史或這些主題之間錯綜複雜的關聯。」——馬克.內斯比特(Mark Nesbitt),邱園(Kew Garden)—英國皇家植物園跨領域研究的資深研究主管
⚘
「引人入勝、研究細緻,全面考察了植物插圖透過藝術和科學的歷史歷程。哈里斯使用罕見...
章節試閱
〈第一章:植物與版面〉
若不將花卉描繪下來,很難以恰如其分的眼光欣賞它們的美麗;而要在花朵變化之前,逼真地畫出它們的面貌又更顯困難。──《普羅瑟碧娜:路邊野花研究》(Proserpina, 1875)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
十八世紀的全球探險家正為大自然多樣性和經濟潛力歡欣鼓舞之際,商人、醫師、軍人和殖民官員紛紛將大量植物送往歐洲各重要城市。這些植物有的被種植在花園裡,有的被壓製成乾燥標本,保存進植物標本館,並在十八世紀逐步發展成植物學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一七○五年,曾擔任英國女王瑪麗二世御用植物學家的雷納德.普拉肯內特(Leonard Plukenet)出版了《植物大全》(Amaltheum botanicum),由至少六位雕版師為數百種植物製作了一百○四幅蝕刻銅版畫。這些扁平畫作看起來像簡易的示意圖,難以表現植物的自然面目。問題或許出在這些植物太過新奇,而製畫的藝術家並不熟悉植物的基本結構,也不太了解構造之間的關係,甚至可能受他們所參照的植物標本來製畫影響。
在《植物大全》的最後一幅插畫中,右上角是巴西東北部某種馬鈴薯的嫩枝,有著三片葉子、幾朵花和幾個花苞,更重要的是,有一根皮刺從左下那片葉子上方的莖冒出來。包括這幅畫在內,共有二十幅畫是根據威廉.丹皮爾(William Dampier)採集回英國的植物標本所創作;他曾是一名有私掠許可的海盜,在一六九九年至一七○一年間,由政府資助的環球航行中蒐集到這些標本。這些來自澳洲、巴西和東南亞的標本被丹皮爾「博學的好友」借給普拉肯內特和他的工匠,這位好友就是博物學家約翰.伍德沃德(John Woodward)。
普拉肯內特書中這幅巴西馬鈴薯的畫作,有整整一百多年都未受到外界注意,直到一八一三年才被法國植物學家米歇爾.杜納(Michel Dunal)正式列為新的物種,學名是Solanum brasilianum。不過,這種植物只在普拉肯內特的畫中出現過,經過數十年的搜尋都未發現活體植株。
解讀丹皮爾的標本時,杜納仰賴的是一位陌生繪師的筆下功夫,但連他自己在內,無人去調查過用來作畫的標本。杜納將這種植物列為新物種的兩百多年後,有人在牛津大學植物標本館重新找出這個標本,同時找出丹皮爾蒐集的其他乾燥植物,重新檢查才發現當初的繪師搞錯了,那根皮刺其實是畫錯位置的花苞,這個標本實際上是巴西最常見的茄屬(Solanum)植物。杜納所描述的「新物種」並未滅絕,而是根本就不存在。繪師無意間犯下錯誤,而杜納又假設這幅畫非常精準,結果就變成眾「眼」鑠金的謠傳。
什麼是植物插畫?
植物插畫是一種如實反映植物外觀的作品,仔細描繪了轉瞬即變、有時還很脆弱的植物構造。十九世紀的法國藝術家安東.帕斯卡(Antoine Pascal)在著作中探討比利時繪師皮埃爾.約瑟夫.雷杜德(Pierre¬ Joseph Redouté)所運用的植物插畫技法時表示,「花卉繪畫有三種用途:直接應用於工業、用來展示植物學知識,或本身就是一種藝術品。」
成功的植物插畫,繪師需透過仔細的第一手觀察,以不假修飾的自然主義風格精確描繪植物。作品繁多的十九世紀蘇格蘭植物繪師沃爾特.胡德.菲奇(Walter Hood Fitch)特別強調這幾點:
「嚴謹的植物繪畫通常只會呈現一兩株植物,而且每株都必須準確描繪和著色。然而,在花俏的繪畫或包含多株植物的圖畫中,繪師可能會因為觀眾的眼睛無法明辨秋毫,便機巧地略過一些細節以節省力氣。我可以說繪師經常濫用觀眾的疏忽,這種做法不僅不吸引人,還時常令人反感;另外,許多花卉繪畫教授的作品不利於提升社會大眾對植物的品味。」
有鑑於此,一個直接衡量植物插畫品質的標準是:我們能否單靠畫作就輕易辨認出這種植物。
義大利畫家朱塞佩・阿爾欽博托(Giuseppe Arcimboldo)以鮮花、果實和種子入畫,完成了匠心獨運的〈四季〉系列油畫(The Four Seasons, 1563, 1572-3),這些作品就符合前述標準。阿爾欽博托對每個元素的描繪如此精確,讓人得以辨識畫中的蔬果。相較之下,文森.梵谷(Vincent van Gogh)的〈向日葵〉(Sunflowers, 1880s)系列畫作,或克勞德.莫內(Claude Monet)繪製的〈睡蓮〉(Water Lilies, 1890s-1920s)系列作品,則都沒有達到這個標準。在梵谷和莫內的畫中,雖然能大概看出植物的類別,但看不出細微而重要、通常極為毫末的特徵,那卻是不同物種之間的決定性差異。
在古希臘、古埃及、亞述帝國和古中國文化裡,人們都曾創造能長期留存的植物圖像。早在西元一千年以前,忠實呈現中藥藥草外觀的圖畫就已出現,不過,「可識別性」的標準其實與西方科學的發源地——東地中海地區——以及人文主義的興起息息相關。植物圖像花了一段時間才慢慢被納入西方世界研究大自然時的科學方法,與此同時,跨文化的交流無可避免地影響了西方植物插圖的實踐。比方說,拜十七和十八世紀的耶穌會傳教士所賜,中國和歐洲的植物插圖在東西方世界之間相互傳播,而十八世紀的印度本土繪師也對歐洲的植物分類學貢獻良多。
光是憑著高超的技法精準畫出植物的外觀,尚不足以創造出具有科學用途的植物插畫。圖書館和檔案室有許多精美的植物插畫,卻不見得有科學價值,原因是缺乏詮釋資料(metadata),也就是解讀這些插畫的脈絡:它們是在何時何地由誰創作?另外,未出版的插畫永遠不會被納入經由同儕審查而產生的科學論文中。一幅插畫要發揮完整的科學價值,除了要精確描繪植物、附上資料和用來佐證的實體標本之外,還要在科學界擴散、流傳,供科學家研究、審查和評論。
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博物學家理查.史布魯斯(Richard Spruce)花了十五年,在南美洲北部的亞馬遜河流域探索山巒與森林。他一邊旅行,一邊採集標本和文物,這些珍品日後都歸入了歐洲和北美洲的文化收藏。史布魯斯尤其對小而嬌嫩的蘚類植物(liverwort)感興趣,這些植物生長在森林的地面、樹幹、溪流和池塘的邊緣,與苔類植物(moss)有著親緣關係。回到英國後,史布魯斯立即投入多年的時間,以維多利亞時期慣用的科學格式來分類與記錄發現。比方說,他在一八八四年出版的《亞馬遜河流域與安地斯山脈的蘚類植物》(Hepaticae Amazonica et Andinae)共收錄數百個物種,用來說明的石版插圖共用掉二十二塊圖板。這些插畫的作者是頂尖苔蘚學家羅伯特.布雷斯維特(Robert Braithwaite)與英國真菌學家兼植物學家喬治.愛德華.馬西(George Edward Massee),兩人都與史布魯斯密切合作。布雷斯維特和馬西擁有深厚的自然歷史素養,但史布魯斯也有他的優勢:他實地考察過這些活生生的植物,不只是靠著乾皺標本從熱水中恢復的模樣來認識它們。因此,不出意料,在他跟布雷斯維特來往的信件裡,他特別指出「蘚類植物畫得很好」,但同時強調他原本可以提供更多協助——「如果我當時就在你們附近,或許就能幫你們挑選目標。」但若真的這麼做,史布魯斯恐怕很快就會認為根據標本製作的插畫在「反覆浸濕和乾燥的過程中」已然失真,他甚至可能會阻止他們創造這些插畫。
最具科學價值的植物插畫誕生於科學家、繪師和印刷師的緊密合作,正如十八世紀的瑞典博物學家卡爾.林奈(Carolus Linnaeus)強調:「要創造一幅值得讚賞的畫作,畫家、雕版師和植物學家同樣不可或缺;如果有任何一員出了差錯,畫作就會有缺陷。」科學家可能會提供受描繪的物件或闡述要表達的概念,再由繪師承接這個願景,運用活生生或死去的植物作畫。要讓繪師的作品被納入科學界的討論,則須將它們轉化成可以流通的媒介;在過去,這就意味著印在紙上。有位優秀的植物學家兼植物插畫繪師直截了當地表示:「畫一幅素描,跟畫一幅可供雕版印刷的圖畫,是兩個很不一樣的概念。」然而,兩者(或它們在現代的對應技術)都同樣不可或缺。科學家、繪師和印刷師可以是同一個人,舉例而言,在十九世紀的倫敦,有一間專攻自然歷史作品的印刷店屬於索爾比家族所有,而詹姆斯.索爾比(James De Carle Sowerby)可能是整個家族最有才華的成員,他曾獲倫敦地質協會讚美:「他透過繪畫和雕刻,為我們帶來化石、貝殼和植物的畫作,相當精準且真實地表現了它們的特徵——唯有科學藝術家才能達到這種成就。」在更多時候,科學家、繪師和印刷師是各自獨立的角色,因為他們仰賴的技能是互補的,很少人可以集所有能力於一身。因此,植物插畫的出版向來是合作的結果。
重點是,出版過程中的每個步驟,都會不斷修改草圖,根據插畫的用途、收錄這幅插畫的作者意圖和能夠運用的技術,來消除、旋轉、填補、模糊和凸顯植物的一些特徵。修改過程中的每一步都可能削弱或強化植物的細節。一幅插畫在科學上能如何解釋,以及會衍生什麼樣的結論,都取決於插畫的製作目的,以及繪師和印刷師的技術。
儘管有上述疑慮,我們仍能從十五世紀以來的植物插畫觀察到幾個主要趨勢。這些趨勢與繪師使用哪些技法、在何種表面繪製圖像、彩色顏料的種類和來源、為了凸顯或揭露新細節而運用的放大技術、題材的多樣性,以及植物插畫的受眾息息相關。
審美權威也許會認為植物插畫只是有著嚴格框架的技術繪圖,缺乏藝術表現空間,有時更諷刺只需要熟練且機械性地操作畫筆。對於這種「繪師」與「藝術家」的二分法,有位植物插畫繪師的觀察是:「為出版繪製的畫作通常被稱為『插畫』,這個詞時帶貶義,彷彿『插畫』終究屬於比『藝術』次等的類別。」另一位植物插畫權威則表示,繪師的處境是「受委託繪製插畫,但過程中沒有任何自由——不可能自我表達──且像相機一樣運作。」
自十五世紀歐洲使用印刷機以來,有各式各樣高品質的植物插畫獲得出版,從中可以發現,儘管受限,科學植物插畫仍有藝術表現的自由。繪師駕馭媒材的功力以及創作上的種種選擇,都大幅提升了插畫的整體吸引力、視覺效果和科學用途。在技藝高超的繪師筆下,即使是最神祕難解的植物也能被描繪得既美麗又啟人深思,不僅讓人目眩神迷,還能提供豐富的資訊。
為什麼要畫植物?
基本上,植物插畫與科學資料的保存、資訊展示及知識傳播有關。重要的是,植物插畫保存了用傳統博物館技術可能很難保存的植物資料。舉例來說,一旦經過壓扁和乾燥的程序,圓形仙人掌的多汁外形、蘭花的複雜形狀、鳳梨的細緻色彩和相思樹的立體結構就都消失了。植物科學的許多領域都吸引繪師一展長才,這些領域包括:發掘野生植物和栽培植物並加以描述與分類、剖析植物體的組織結構,以及探索植物的生長和分布,當然,還有教學。除了這些領域,十九世紀的博物學家兼藝術家威廉.伯切爾(William Burchell)更強調,欲造訪陌生國度或人跡罕至之處的人⋯⋯(應該要)最重視繪畫這門藝術,不只是為了與朋友分享所見所聞,也是為滿足自身。在重溫往日印象時,畫作是比遊記更生動的媒介,讓人樂在其中。
伯切爾的評論預示了照片在今日的用途。至於植物插畫,作為一種科學證據,它必須奠基於客觀的個人觀察,精準呈現出樣本的外觀。在希荷尼穆斯.博克(Hieronymus Bock)的《德國植物與常見命名法》(De stirpium, 1552)中,有一幅叫作「水堅果」(Wassernuß)的木刻版畫,是一個富有想像力的綜合體,與任何已知植物都不相符。儘管畫中那顆分離的果實看起來就是菱角,這幅插畫和圖說都無法讓不熟悉菱角的讀者辨認出這種植物。同樣地,在閱讀蘇格蘭外科醫師兼植物學家威廉.羅克斯堡(William Roxburgh)的《科羅曼德海岸植物》(Plants of the Coast of Coromandel, 1819)時,除非是專業的植物學家,否則讀者必須端詳插圖才能明白作者對菱角的敘述:
「葉子具葉柄,簇生於莖端,呈腎臟般的菱形,下半部平整,上半部有鋸齒。葉面光滑,呈深綠色,背面有絨毛,呈紫色;寬度是三至四英寸,長度通常短於葉寬。具絨毛的葉柄會隨著葉齡增加而變長,靠近頂端的部分最為膨大,因為這裡有許多氣囊,為整株植物提供浮力。」
植物插畫如同其參考的標本,往往不會是個純然的物件,可能揭露出錯綜複雜的社交關係、贊助和權力模式。如同其他藝術家和科學家,植物插畫的繪師和生態學家往往仰賴著政府、貴族或商業機構的資助。在一八三○年代,植物學家約翰.林德利(John Lindley)在出版弗朗茲.鮑爾(Franz Bauer)的蘭花插畫時,引起了讀者對此類議題的關注:
「透過能傳達原作之美的版畫,將所有如此輝煌的藝術作品都公諸於世,是慷慨的君主和開明政府值得追求的目標;對民間人士而言,高昂的費用必然會成為無法跨越的障礙。像我這樣卑微的小老百姓,至多僅能選擇那些最能表現植物形態的作品來出版。但即使如此,由於這類事業極少受到支持,我不得不耗費多年為之。」
鮑爾在十八世紀晚期從奧匈帝國來到英國,自那時起便一直受到約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的資助,他是打造英國皇家植物園(別名邱園)的幕後功臣。
一七九五年至一八一九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從數千幅由蒙兀兒藝術家在羅克斯堡指導下創作的植物插畫中,挑選了三百幅來出版,最後成為《科羅曼德海岸植物》(Plants of the Coast of Coromandel)書中,對開大小的手工上色銅版畫。東印度公司此舉有兩個動機,一是「促進印度的科學發展」,二是「鼓勵公司海外雇員在閒暇時間進行有益的研究,作為向上級推薦自己的手段,並且在祖國贏得應有的聲譽。」
一本書若加上插圖,尤其是彩色插圖,可以變得更引人入勝,但有時這樣做需要很高的成本。在圖文並茂的植物書籍中,《科羅曼德海岸植物》(Plants of the Coast of Coromandel)這類奢華的限量版作品位於高價的一端,低價的一端則是教科書、辨識圖鑑和教學輔助工具,它們的插圖是實用取向,旨在讓內容變得清楚易懂或提升銷售量。以蘇格蘭植物學家約翰.赫頓.巴爾福(John Hutton Balfour)的《植物學手冊》(A Manual of Botany, 1875; 1st edn 1848)第五版為例,這本書是英國植物學的標準教科書,書背上寫著「九百六十三幅插圖」,字體跟作者名字差不多大;扉頁並未寫出黑白插圖的確切數量,僅模糊表示「超過九百張插圖」。這件事顯然代表有插圖就能提高銷量。
〈第一章:植物與版面〉
若不將花卉描繪下來,很難以恰如其分的眼光欣賞它們的美麗;而要在花朵變化之前,逼真地畫出它們的面貌又更顯困難。──《普羅瑟碧娜:路邊野花研究》(Proserpina, 1875)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
十八世紀的全球探險家正為大自然多樣性和經濟潛力歡欣鼓舞之際,商人、醫師、軍人和殖民官員紛紛將大量植物送往歐洲各重要城市。這些植物有的被種植在花園裡,有的被壓製成乾燥標本,保存進植物標本館,並在十八世紀逐步發展成植物學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一七○五年,曾擔任英國女王瑪麗二世御用植物學家...
作者序
審定∣林哲緯∣植物分類工作者,任職於林業試驗所;專注於東南亞的熱帶植物,特別是秋海棠及野牡丹科植物,目前已累計發表一百二十餘新種,論文曾獲數屆彭鏡毅博士紀念獎;亦專長繪製科學發表之線描圖及商業插圖,作品可見於多本商業書籍及教科書上。
審定∣林哲緯∣植物分類工作者,任職於林業試驗所;專注於東南亞的熱帶植物,特別是秋海棠及野牡丹科植物,目前已累計發表一百二十餘新種,論文曾獲數屆彭鏡毅博士紀念獎;亦專長繪製科學發表之線描圖及商業插圖,作品可見於多本商業書籍及教科書上。
目錄
作者序
第一章:植物與版面
什麼是植物插畫?─為什麼要畫植物?─植物插畫出自何人之手?─植物是在哪裡畫的?─製作插畫─複製插畫──凸版印刷──凹版印刷─平版印刷─自然印刷──添彩上色
第二章:主題和趨勢
古代世界─植物插畫:單一個案及典型型態─仿製插圖的挑戰─比例尺和放大倍率─空間經濟學─發表或湮滅─曠世巨作─物換星移
第三章:科學與插畫
自然與奇觀─科學思維─活體實驗室與乾燥花園─命名與分類─黃銅與玻璃─生理學與實驗─演化與遺傳學
第四章:鮮血與寶藏
採集生物─一帆風順─火山攪動的大地─熱愛大自然之人─焚香與龍血之島─探勘珍稀植物─樹皮和橡膠─準確性、精細度與惻隱之心
第五章:花園與樹林
記錄歐洲花園─與貴族的關聯─展望東方─秋菊與春蘭─推銷植物世界─果園和葡萄園─花園的變遷
第六章:裡裡外外的世界
繪製顯微鏡下的物體─看不見的世界─盒子做成的枝杆─外形與功能─永無止盡地修改─莖上的生殖器官─畸形植物─顯微鏡下的黴菌
第七章:習性與棲地
尋找混雜在種種迷思中的真相─化驚豔為平凡─眾目睽睽之下─圖畫與文字
第八章:觀察與試驗
認識植物性別─達爾文的蘭花─條條大路─為生命加點調味─重建稀有植物的形象──掌握幾何學
第九章:汗水與淚水
王公貴族的會客室─視而不見─文字和圖片─讓植物學大受歡迎─植物掛畫─立體植物模型
作者序
第一章:植物與版面
什麼是植物插畫?─為什麼要畫植物?─植物插畫出自何人之手?─植物是在哪裡畫的?─製作插畫─複製插畫──凸版印刷──凹版印刷─平版印刷─自然印刷──添彩上色
第二章:主題和趨勢
古代世界─植物插畫:單一個案及典型型態─仿製插圖的挑戰─比例尺和放大倍率─空間經濟學─發表或湮滅─曠世巨作─物換星移
第三章:科學與插畫
自然與奇觀─科學思維─活體實驗室與乾燥花園─命名與分類─黃銅與玻璃─生理學與實驗─演化與遺傳學
第四章:鮮血與寶藏
採集生物─一帆風順─火山攪動的大地─熱愛大...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