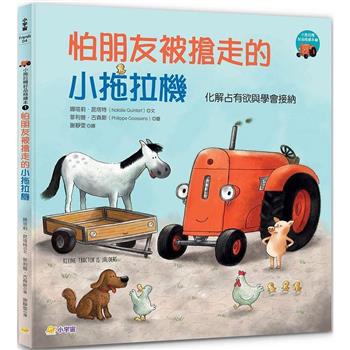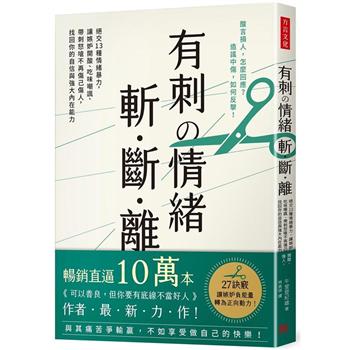一萬年前,第一位農夫在肥沃月彎播下種子,
彷彿掀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從此,人類這個物種在生活方式上做了根本的改變:
放棄狩獵採集、進入農業生活,
啟動了一連串無法預見的改變。播下潘朵拉的種子,讓人類擁有了食物供應的控制權,將我們推向現代文明,
但是這種劇烈轉變也帶來了後遺症:
◇ 人口擴張,競奪有限資源,造成了階級劃分與社會不公。
◇ 想要控制大自然的慾望,改變了宗教的觀念,神祇的數目變少,影響力變大,點燃了宗教狂熱。
◇ 畜養牲畜,使得人類與動物有親密接觸的機會,長期下來,演化出可以在人類與動物之間交流的疾病。
◇ 逍遙自在的生活被沉重的工作壓力給取代,是百萬現代人焦慮與憂鬱的根源。
結果是:地球變得更擁擠,我們變得四體不勤,愈來愈不健康。
知名遺傳學家與人類學家韋爾斯走遍世界各地,檢視人類文明與傳承,帶領我們進行一趟跨越萬年的時空之旅。他不僅找出種子如何征服世界的過程,發現讓人類走上通往今日之路的轉捩點,最後還提供「希望」處方:
我們必須改變方向,才能存活下去。
作者簡介:
史賓賽・韋爾斯
美國國家地理學會的常駐探險家,康乃爾大學的羅茲講座教授。他是「基因地理計畫」(Genographic Project)的負責人,該計畫正在蒐集並分析世界各地數十萬人的DNA標本,想要解開人類祖先當初如何遍布全球之謎。
韋爾斯於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並曾在史丹福大學及牛津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在這本書之前,他寫過兩本書:《人類的旅程》(The Journey of Man)及《遠祖》(Deep Ancestry)。
他目前與紀錄片導演妻子住在美國華府。
★如果想與作者直接討論,請上Facebook《潘朵拉的種子》粉絲頁 http://www.facebook.com/pandorasseed
譯者簡介:
潘震澤
台灣大學動物系所畢業、美國密西根韋恩州立大學生理學博士,洛克斐勒大學、密西根州立大學、密西根大學等校研究,專長為神經內分泌學。
曾任陽明大學生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長,並獲慶齡基礎醫學獎、國科會傑出獎、特約獎等榮譽。現任教於美國韋恩州立大學及奧克蘭大學。
近年關心科普讀物譯介,譯有《人體生理學》、《天才的學徒》、《誰先來?》、《幹嘛要抽菸?》、《為什麼斑馬不會得胃潰瘍》、《睡眠的迷人世界》、《基因組圖譜解密》、《器官神話》、《DNA圖解小百科》、《生命的線索》、《夢的新解析》、《虛擬的解剖刀》、《死亡也可以治療》、《蛋白質殺手》、《小生命》、《愛上中國的人:李約瑟傳》等書,著有《科學讀書人》、《生活無處不科學》,並擔任《科學人》雜誌編譯委員。
★潘震澤教授有一個很受歡迎的部落格「生理人生」(blog.chinatimes.com/jenntser/),裡面有很多精采的文章。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集探險家、遺傳學家、地理學家與作家於一身的韋爾斯,帶領我們走了一趟精采旅程,探尋人類過去一萬年的歷史,目的是為了警告我們在接下來的五十年間將會碰上什麼問題。——普立茲獎得主 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及《大崩壞》作者
韋爾斯的寫作結合了他對人類演化史的深刻了解,以及鮮明、有趣的風格,使得整個故事栩栩如生。
《潘朵拉的種子》用上引人入勝的見聞,以及動人的個人故事,明確指出人類這個物種正面臨某個關鍵的轉捩點;人類在此停下腳步,回顧漫長的演化軌跡之餘,還要正視其黑暗面及代價。——亨利・路易斯・蓋茲(Henry Louis Gates, Jr.)哈佛大學弗萊契大學講座教授
韋爾斯的及時訊息引人矚目,他認為人類正處於關鍵時刻:我們的文明有可能摧毀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他的文章論據充分且深思熟慮,並帶給我們希望,以及未來的藍圖,而他所看到的未來,或許要師法某些仍過著遠古生活的現代人。任何關心人類前途的人,都應該讀這本書。——布萊恩.費根(Brian Fagan)《歷史上的大暖化》與《克羅馬儂人》作者
名人推薦:集探險家、遺傳學家、地理學家與作家於一身的韋爾斯,帶領我們走了一趟精采旅程,探尋人類過去一萬年的歷史,目的是為了警告我們在接下來的五十年間將會碰上什麼問題。——普立茲獎得主 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及《大崩壞》作者
韋爾斯的寫作結合了他對人類演化史的深刻了解,以及鮮明、有趣的風格,使得整個故事栩栩如生。
《潘朵拉的種子》用上引人入勝的見聞,以及動人的個人故事,明確指出人類這個物種正面臨某個關鍵的轉捩點;人類在此停下腳步,回顧漫長的演化軌跡之餘,還要正視其黑暗面及代...
章節試閱
與虎共餐五年情
如果有人問「在英國小獵犬號軍艦上的自然學家是誰?」,絕大部分的生物學家一定會說︰「當然是達爾文了!」但他們可全都錯了。我並不是在故作驚人之語。沒錯,達爾文的確曾待在小獵犬號上,而且他也投注全副精神研究大自然;但他是因為各種其他的理由上船的。事實上,船上的外科醫生麥可密克(Robert McKormick),才是官方指派的自然學家。
這個有趣的故事,還不單是學術史上的一個捫虱小注腳,反而是個頗為重要的小發現。人類學者葛陸博(J. W. Gruber)於一九六九年的《英國科學史雜誌》所發表的〈誰是小獵犬號的自然學家?〉一文中提出了全新證據;而在一九七五年,科學史家伯斯丁(H. L. Burstyn)更想回答進一步的問題︰達爾文既然不是小獵犬號正式的自然學家,那他為什麼上船?
雖然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正式的官方紀錄,指出麥可密克是船上的自然學家,但卻有其他很充分的證據可以說明這一點。按照當時大英帝國海軍的傳統,同行的軍醫還得同時兼任自然學家。事實上,麥可密克也很努力地充實自己在這方面的能力。也許算不上非常傑出,但麥可密克確實還算是一位稱職的自然學家;而且在其他的探測航行中,屢屢證明他的工作表現頗為得體。例如,他曾經參與了一八三九年到一八四三年由羅斯船長所率領的南極洲探險,目的是想要找出地球的南磁極所在。
此外,葛陸博還很幸運地找到一封愛丁堡大學自然學家傑米生(Robert Jameson)寫給「小獵犬號的自然學家」的信。信中對收件人的稱呼是「我親愛的閣下」,然後談了許多蒐集和保存動植物標本的各種要訣。依照傳統的看法,我們一定會認為這封信的收信者必然非達爾文莫屬了。但巧的是,原來的信封還在,而收信人明明白白指名是給麥可密克的。
■達爾文上船之謎
咱們就別賣關子了,直接揭開謎底吧。事實上,達爾文之所以跟隨小獵犬號航行,原本的功能是要當船長費茲羅(Robert Fitzroy)同行的友伴。那麼,為什麼這位英國船長會想要這個認識才一個月的人,來當他五年航程的同伴呢?其實,這是因為在一八三○年那個時代,英國海軍有兩個特別的航行特性,讓費茲羅不得不這麼的做。
首先,海軍每趟航程長達好多年,而且離港時間動輒數月,其間與家人朋友聯繫的郵件幾乎完全遭到隔絕。其次,英國海軍傳統要求船長不能和下屬有任何的社交活動。這點雖然從我們現代開明的角度看起來,似乎非常奇怪,但當時的船長不但必須獨自吃飯,就算接見下屬軍官時,也只能談船上公務,而且得用最官式、最正確的語態往來。
當年費茲羅與達爾文啟航時,才剛二十六歲,但他已經深知,長期缺乏社交、不與人群接觸,對一位船長的心理折磨很大。小獵犬號的前一任船長就是因精神崩潰而舉槍自殺的;那是在一八二八年冬天發生的事,當時那位前任船長在南半球遠航了三年。此外,費茲羅也自知(在達爾文給姊姊的信中證實了此事),費氏家族中有遺傳性的精神異常傾向。他那極有名的舅舅凱塞瑞(Viscount Castlereagh)子爵,就是在一八二二年切喉自殺而死的(凱塞瑞在一七九八年擺平愛爾蘭叛變,在擊敗拿破崙的時代是英帝國外相)。
事實上,在航行過程中,費茲羅的確曾因精神崩潰了一陣子,而暫時交出他的指揮權;這時,達爾文也在南美的凡帕雷索(Valparaiso)臥病在床。
既然費茲羅不能和船上的軍官們有任何社交,因此只得靠他自行在工作人員體制外,安排其他的旅客上船,才可以有點交際談話的機會。海軍司令部當然不能允許私客上軍艦,事實上甚至連眷屬或太太都不可以。如果沒有特別目的就讓一名紳士朋友上船,當然就更絕對不行了。雖然,費茲羅已經帶了好幾位額外的人上船,包括一位製圖員及一位儀器工。但這些人並不能當他的友伴,因為他們的社會階級比較低;費茲羅是貴族,他的祖先可追溯至查理士國王二世,所以,只有紳士階級的人才有資格與他共餐。剛好,達爾文也確實具有紳士的身分。
■陪船長吃飯
可是,費茲羅要怎麼樣才能吸引一名紳士和他一起航行五年呢?只有讓他有機會從事獨一無二、別處難覓而有價值的工作了;而算來算去,就非從事博物研究的人員莫屬。雖然船上早有官方的自然學家,但多一位非正式的亦無妨啊。於是費茲羅就透過他的貴族朋友,希望招攬一位兼具紳士資格的自然學家。以這種名義來召募,當然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一方面可以解釋他為什麼要一位紳士,另一方面也以這項工作為釣餌,以便吸引有興趣的紳士赴船遠航。
達爾文在劍橋的老師,植物學教授韓士婁(J. S. Henslow)很明白這項企圖,因此他在給達爾文的信中說︰「費船長不單是要個蒐集家,事實上更想為自己找個伴。」
後來,達爾文和費茲羅見面了,兩人還蠻投緣的,於是一言為定。所以達爾文就成了費茲羅的同桌夥伴,要在船上陪他吃每一頓飯。除此之外,費茲羅也同時是個野心勃勃的年輕軍官。他想在這次的航行任務中,為海軍的探測之旅,創下一個最高品質、最具科學價值的範例。〔達爾文曾經寫道︰這次航行的目標,是完成對巴達哥尼亞及火地島內陸及海岸的測繪,也順及智利、祕魯、太平洋諸島海岸,還有全球一系列的時刻測量。〕因此,費茲羅真可說是極盡所能地利用自己的財富及權位來達成目標。諸如,自掏腰包僱請了一隊技術員和工匠,並且多邀聘了達爾文這位自然學家,來擴大船上科學家的陣容。
■告假返鄉
但是可憐的麥克密克,他的命運就此注定了。起初他還和達爾文一起合作,但不久就分道揚鑣了。達爾文有各項優勢,他不但是船長跟前的紅人,身邊還有一個專屬的傭人。每到一個港囗,他還有錢上岸組織探險隊,雇請當地的蒐集者。而可憐的麥克密克受到他的行政職責所限,不能任意離船大肆採集,所以沒有多久,達爾文收藏的動植物數量,就遠超過了麥克密克的努力了。一心不能二用的麥克密克當然遠居劣勢,於是一怒之下決定稱病回家。一八三二年四月在里約熱內盧,他以身體虛弱為由,撘上英國軍艦泰河號(H.M.S. Tyne)返回英國。達爾文也知道內情,在寫給他姊姊的信中說道︰「麥克密克所謂的虛弱病,其實就是跟船長不合,被送回去了。」
其他事先不談,這件「私客上船」的故事,至少極度突顯出社會階級對科學史的重要性。如果達爾文出生於工匠之家,而非有錢醫生的兒子,那麼各位看官想想看,生物學在今天會是什麼樣子呢?達爾文繼承巨額的財產,可讓他專心做研究,無後顧之憂;而且他中年以後怪病纏身,每天只能工作兩三個鐘頭,如果他得賺錢養家的話,就絕對不可能做任何研究了。
而我們現在又知道另一個祕密︰達爾文的社會階級在他職業生涯起點,發揮了最關鍵的轉捩作用。費茲羅所看重的,是他餐桌伴侶的社會地位,而不是這個人的專業能耐。
■餐桌上的風波
在達爾文和費茲羅無數次的餐桌閒聊中,是不是有什麼趣事可供發掘呢?科學家們偏向於將偉大科學家的創見,拘泥於實驗證據所能發揮之處。因此往往認為加拉巴哥群島(Galapagos Island,位於東太平洋,地屬厄瓜多爾)的大陸龜和鷽鳥是改變達爾文物種觀點的主要媒介。因為當初他剛上小獵犬號時,還是個百分之百虔誠、又傻楞楞的神學生,只準備當個鄉村小牧師。可是下船不到一年,他就開始私下記錄他對「物種轉變」各項離經叛道的臆測。但依我的意見來看,費茲羅反而才應該是促成達爾文變心的強力催化劑!
達爾文和費茲羅的友誼其實只能用矯飾和緊張來形容。嚴格說起來,一切只因紳士該有的禮貌和當時喜怒不形於色的社會習慣,讓這兩個人的關係還能維持在一種尚佳的程度。但還是有個問題,費茲羅是個嚴肅軍人,也是一位熱心的保守黨員,而達爾文則是同樣投入的自由黨員。達爾文曾很仔細地設法避免和費茲羅討論當時國會中熱烈辯論的改革法案。不幸的是,蓄奴問題還是搬上了飯桌,成了他們公開爭執的導火線。
有一天晚上,費茲羅說他看過一個證據,證明蓄奴是最仁慈的︰當時巴西最大的一個奴隸主人把他的囚犯們都聚在一起,問他們想不想自由,而全部的奴隸都異囗同聲說「不!」這時,達爾文不知怎麼地鼓起了他的愚勇回說︰「在主人面前,奴隸敢說真話嗎?」費茲羅聽了立刻暴跳如雷,告訴達爾文︰「誰懷疑我的話,就不適合跟我一起吃飯!」說畢,達爾文竟然真的立刻就搬出去和其他軍官們撘伙。撐了幾天後,費茲羅的態度還是軟了下來,並送了一封正式的道歉信給達爾文。
我們知道,達爾文並不喜歡聽費茲羅強烈的主張,私底下也一定很氣他的謬見;但他是費茲羅的客人,從某個角度來看,也是費茲羅的下屬。在他那時代,每艘軍艦的船長在海上是絕對至高無上、不容質疑的專制君主。所以達爾文在海上的這些日子,時時忍受著不能公然反對之苦。想想看,這位有史以來天資最聰穎的年輕人之一,有整整五年的時光得在吃飯時三緘其囗,是什麼樣的滋味?
■無聲的叛變
費茲羅心中至愛的,還不只是保守的政治主張。宗教,是另一個他熱中談論的話題。雖然費茲羅有些時候也會懷疑「聖經到底是不是每個字句都對?」但他的確把摩西看做是個貨真價實的歷史學家和地質學家。他甚至曾經真的下了工夫,去計算諾亞方舟到底有多大。費茲羅在晚年最喜歡的主意,便是「從設計的角度來證明上帝」的論證。他相信,從生物的完美構造,就可推演出上帝的大愛。
然而達爾文卻正好相反;雖然他承認生物有完美的設計,但卻提出一個和費茲羅的主張南轅北轍的理論,來解釋大自然的現象。達爾文所發展出來的演變理論,是基於生物隨機的變異,還有外界環境所施於生物族群的天擇。這個學說可以說是相當嚴格的唯物論,也是一種無神論的演化說。但其他在十九世紀所流行、五花八門的各種演化學說,倒還不至於與基督教如此格格不入。譬如說,當時的宗教領袖至少還比較能接受「生物內部自生的完美趨向」這種論調,而無法忍受達爾文那種沒有妥協餘地、純粹機械掛帥的自然觀點。
那麼,達爾文逐漸改變的哲學觀點,有沒有可能是因為實在受不了費茲羅日日堅持他「從設計的角度來證明上帝」的武斷說法,而想出來的破解之道呢?所有的證據都指出,達爾文在海上航行這五年當中,一直是位信仰虔誠、標準的好基督徒。他對宗教的懷疑和抗拒,是下了船、回到倫敦以後的事。在航行的中途,他寫信給一個朋友說︰「我一直在猜想,以後的我到底會變成什麼樣子?如果願望都能實現的話,我真希望當個鄉村牧師。」他甚至和費茲羅一起齊起草了一篇名為〈大溪地島民的道德狀態〉的聲明,希望英國民眾能支持教會派員到太平洋各島傳播基督教福音。但是,懷疑的種子一定也是他在船上冥然沈思時,就開始靜靜地播下及滋長的。
■鬱悶的達爾文
在這裡,讓我們設身處地的想像一下他的環境︰每天要和獨裁的船長吃飯,而這個人的話又絕不能反駁。他的政治宗教觀點和貴族身段,也跟達爾文截然不同;況且費玆羅基本上又不是達爾文所敬愛的朋友。天知道,這五年不停的疲勞轟炸,對達爾文的腦子產生了多少化學反應,發酵了多少反抗的烈酒!或許,費茲羅的一言堂高論,對達爾文哲學思想和演化學說中的唯物及反神觀點,所扮演的催化刺激功效,要遠大於加拉巴哥群島上的那一群鷽鳥咧!
事實上,費茲羅在日益癲癇的晚年,已經開始責怪自己不該帶達爾文上船,使得自己成了達爾文異端邪說的始作俑者,無意中培育了「演化」這反宗教的思想。(的確,我認為費茲羅這個從反面促成的功效,甚至比費氏本人所想像的更多。)因此,他心中燃燒著渴望,想解脫自己在這方面的大罪惡,重振聖經至高的尊榮。
在一八六○年那次有名的英國科學促進會年會中(也就是在該會中,赫胥黎奚落了牛津大主教——「肥皂山姆」韋伯福,對科學假內行、凶猛的攻擊),精神恍惚的費茲羅把一本聖經舉在頭上,到處追趕著人群,高叫︰「聖經,聖經!」
五年後,他割喉自殺了。
(摘自本書第2章)
與虎共餐五年情
如果有人問「在英國小獵犬號軍艦上的自然學家是誰?」,絕大部分的生物學家一定會說︰「當然是達爾文了!」但他們可全都錯了。我並不是在故作驚人之語。沒錯,達爾文的確曾待在小獵犬號上,而且他也投注全副精神研究大自然;但他是因為各種其他的理由上船的。事實上,船上的外科醫生麥可密克(Robert McKormick),才是官方指派的自然學家。
這個有趣的故事,還不單是學術史上的一個捫虱小注腳,反而是個頗為重要的小發現。人類學者葛陸博(J. W. Gruber)於一九六九年的《英國科學史雜誌》所發表的〈誰是小獵犬...
作者序
前言:該是停下來思索的時候了
誠然,西方社會在物質生活上要比四十年前好上太多,
但社會上為什麼還是有那麼多的犯罪、破壞以及塗鴉呢?
離婚率為何居高不下?公民參與及信任卻反而下降?
為什麼肥胖及抑鬱症多到成為流行病的程度,就算孩童也未能倖免?
為什麼在多數最進步國家所做的研究,都指出人們變得更不快樂了?
——湯姆金斯(Richard Tomkins),二○○三年十月十七日《金融時報》
寫這篇前言時,人在阿拉伯海上方一萬一千公尺高空,一面啜飲著葡萄酒,一面在我的筆記型電腦鍵盤上打字。我參加了由印度理工學院主辦的一場科技慶典活動,並給了場演講;如今則坐在從孟買起飛的返家客機上。我花在來回旅途的時間,是我停留在印度當地時間的兩倍;再加上十個半小時的時差,我人在印度時還不只是有一點點的精神恍惚。饒是如此,印度是我喜歡的國家之一,利用一個長週末來回奔波半個地球、忍受時差的鞭打,還是值得的。
邀請我前往演講的印度理工學院學生,希望聽我在遺傳學及人類遷徙方面的研究,那也是占據我過去二十年來大部分時間的工作。這項由我和同事共同執行的研究,清楚顯示了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源自二十萬年前非洲的一位共同祖先;而人類離開非洲遍布全球各地,也只不過是過去六萬年間發生的事。我花了一個小時講述這領域裡的新資料,討論了一些還沒發表的新發現,大致給我們這個物種刻畫了一幅遺傳的歷史圖。
演講結束後,我也按一般常規,接受聽眾的發問,內容從實驗室分析人類DNA的技術細節,到一般性的問題都有。而最後一個問題是我之前被問過好幾次的,將來肯定還會再被問到,也就是:你的研究工作有什麼更廣泛的價值與意義?
我的回答是:研究人類遙遠歷史的神祕細節,乍看起來確實有些難以讓人理解,但那一向讓我著迷;只要有正確的樣本加上少許的統計,就有可能釐清我們這個物種如何遍布全球的細節。學生繼續問道:「但是這種研究為什麼重要呢?」
一開始我站在科學家的立場解釋:不講求特定實際應用的基礎研究為什麼重要。我說政府在許多不同的主題上資助這樣的研究,是因為有些新發現可能會在較實用的領域裡非常有用,譬如說醫學。再者,界定我們這個物種的是我們擁有的複雜文化;為了要了解我們在這個世界當中扮演的角色,科學研究本身就是重要的。我還說,如果我們碰上了某個來自地外行星的智慧生命,那麼在這種千載難逢的機會裡,我們要跟對方談的究竟是最新的電視遊戲如何操作的單調細節呢?還是專注於我們這兩個高度演化的物種是如何變成現今這個模樣的問題?我們必須了解自己的歷史,才能夠了解自己是誰、以及預測我們將往哪裡去。如同法國哲學家亞蘭(Alain)所言:歷史是對現在的宏觀,而不只是關於過去。
不過這種研究之所以重要,還有另外一個理由,我解釋道。目前人類生活在高度全球化的世界,我們所接觸的人在一世紀之前是從來也不會碰上的。由非洲人與歐洲人、亞洲人及美洲原住民混在一起所形成的社會大雜燴,可是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情況。這樣的接觸加上語言及文化的差異,也就構成具有變化多端潛力的配方。我們非常清楚這種差異的存在,因為這種差異有助於給自我定位。只不過我們的遺傳學研究也顯示:在表象之下,亦即在DNA的層次,這些差異有多麼微不足道;基本上人類是完全相同的。我解釋道:我的研究帶來的更廣泛意義,在於我們都應該試著看穿區分人種的表象,認清我們都屬於人類這個大家庭。只要我們能認識到在基因的層次,大家都彼此相連,這樣才有可能克服部分的偏見。
對在場聽眾來說,這種看法似乎有特別的意義,因為大多數人在不久之前才目睹了一場恐怖份子的殘忍攻擊:來自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好戰份子在孟買南區好些地點進行了爆炸及槍殺行動,四天內殺死了一百六十四名無辜百姓(恐怖分子也死了九個);他們甚至還控制了兩家具有歷史意義的旅館:泰姬酒店和奧拜羅酒店。對印度社會而言,這場事件的衝擊性等同美國的九一一事件,還好死亡人數沒那麼多。經過這樣的事件,就算印度人會感到氣憤,心存報復,為進一步的暴力行動找藉口,也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根據邀請我與會的主人所言,印度人並沒有沉溺在負面的情緒當中。在我抵達當晚於車陣中穿梭前進時,他告訴我:「這個事件讓我們團結起來,我指整個印度。」
我那次造訪印度的經歷,以及本章一開頭引述湯姆金斯的話,都彰顯了這本書的主題。在我身為遺傳學家及人類學家的生涯中,有幸與全球許多人共事,從資深政治家與大企業老闆,到偏遠蠻荒地區艱苦求生的採食部落族等等;但一再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不論這些人生活在何處,都可以看到當今世界的巨大變化。
這些變化裡有些是好的,好比整體貧窮的程度減少了,開發中國家的出生率下降了;但其他一些變化,譬如九一一事件及孟買的恐怖行動,就不讓人滿意。無論身在何處,我們都可感覺到世界在不斷變動之中;人類正處於歷史的轉捩點,在接下來的幾個世代中,世界將出現根本的改變。科技創新的腳步正在加快,我們也都置身其中,遭其席捲。我們只要想想過去十年左右學會使用、如今已離不開手的一些東西就可以知道;我馬上想到的有電郵、Google、即時簡訊與行動電話,此外還有油電混合車科技、路邊資源回收,以及像臉書這樣的社交網站。這些新產品都是在一九九○年代中葉以後才廣為流行的,但如今我們已無法想像沒有它們的日子。如果要我們想像二十一世紀結束時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然而隨著驚人科技進步而來的,卻有一些附帶的包袱。慢性疾病在西化社會中史無前例的大幅上升,可能是最顯著的例子了。我說「西化」而非「西方」社會,是因為在印度與中國這樣的開發中國家,心臟病、糖尿病以及單純的肥胖病例也不斷增加。隨著這些社會愈來愈與西方看齊,他們也承受了許多我們最糟糕的屬性,像抑鬱與焦慮等心理疾病也逐漸增多;目前在美國,治療這類毛病所開立的藥物處方籤,數量是最多的。
這種朝西方不健康社會邁進的腳步,似乎難以阻擋,讓我不禁好奇那最初是怎麼開始的。是否在西方文化與我們的生物組成之間有某種致命性的不搭調,而讓我們生病?如果說這種搭配不當確實存在,那我們目前的文化當初又如何取得了優勢?我們理應是自己命運的掌握者,也創造了最適合自己的文化,而不是受文化的驅策,不是嗎?
我花了很長時間才得出這個問題的答案,讓藍燈書屋與企鵝出版社耐心等待的編輯們頗為煩惱。有鑒於人類正面對演化上另一個明顯的轉捩點,因此我在全球展開探索,比較幾千年前與現在發生的事,尋找相似之處。我在為頭一本書《人類的旅程》(The Journey of Man)進行研究之際,發現一萬年前出現於中東的農業生活方式對人類存活產生的影響,而讓我感到十分訝異。我在第一章裡會談到,早期農人的健康狀況要比環繞其外圍的狩獵採集族群來得更差。既然如此,那為什麼農人還會取得如此巨大的「勝利」,以致於今日地球上幾乎沒有人以狩獵採集的方式生活?本書接下來的部分,是嘗試從當今的「考古」紀錄裡發掘,以了解促使農業轉型的動力,以及該決定如何創造了我們現存的複雜世界。如果說《人類的旅程》談的是人類如何在世界各地立足的故事,那這本書則是談論在發生那些巨幅改變的階段,人類如何在心理以及生理上產生適應,而在世上存活。這兩本書就像人類歷史宏觀的前後兩個書鎮,在我們飛奔深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帶著我們從人類這個物種的最早期起步,一路走向未來可能的去處。
布蘭德(Stewart Brand)在一九六八年第一期《全球目錄》(Whole Earth Catalog)的開場白說得好:人類好比諸神,這回該是我們扮好這個角色的時候了〔這是改寫自李區(Edmund Leach)的話〕。人類在過去五萬年歷史當中出現的最大革命,不是網路,也不是從啟蒙時代播下的種子萌發的工業革命,或是發展出遠距航行的現代方法,而是生活在世界上好些地方的少數人決定不再受大自然所限、只從大地上採集物品,從而開始種植自己的食物。
這項決定對人類這個物種造成的影響,比其他任何決定都來得深遠,也促成了許多事件的發生,本書接下來的章節將一一檢視。由於該決定所造成的改變,促使人類發展出莫大的能力,但人類也要學習謙遜。在今日的世界,一小撮恐怖份子就可能對整個國家的人民心理造成持久性的傷害,看似簡單的決定也可能對未來好些世代的生物遺傳造成影響,我們的一些作為還可能引起許多物種的消失,速率比過去六千萬年來任何時期都快。目前是停下腳步評估現況、體認事實的時候了:愈大的慾望將帶來愈大的後果。
前言:該是停下來思索的時候了
誠然,西方社會在物質生活上要比四十年前好上太多,
但社會上為什麼還是有那麼多的犯罪、破壞以及塗鴉呢?
離婚率為何居高不下?公民參與及信任卻反而下降?
為什麼肥胖及抑鬱症多到成為流行病的程度,就算孩童也未能倖免?
為什麼在多數最進步國家所做的研究,都指出人們變得更不快樂了?
——湯姆金斯(Richard Tomkins),二○○三年十月十七日《金融時報》
寫這篇前言時,人在阿拉伯海上方一萬一千公尺高空,一面啜飲著葡萄酒,一面在我的筆記型電腦鍵盤上打字。我參加了由印度理工學院主辦的一...
目錄
前言 該是停下來思索的時候了
第一章 地圖裡的奧祕
追尋人類的過去
基因珠鏈上的時尚珠粒
人類獨霸世界舞台的關鍵時刻
天擇青睞的基因
為什麼人類會選擇農業生活?
第二章 培植新文化
正在進行中的新革命——水產養殖
漁業大崩潰
冰壩融化,寒冬再度來臨
作物馴化中心
繁殖自己的食物
政府、宗教、軍隊的興起
第三章 疾病浪潮
肥胖成為流行病
儉約的基因,揮霍的口味
三波奪命潮:外傷、傳染病、慢性疾病
改變自然景觀之際,也種下瘧疾的種子
碳水化合物與蛀牙
新石器革命啟動的疾病潮,至今仍無可避免
第四章 精神病、語言、創新能力
精神病與藝術
尼安德塔人會說話嗎?
火山爆發與創新能力出現
世界愈來愈擁擠,我們愈來愈不快樂
走向美麗新世界?
第五章 基因革命
訂做一個嬰兒
趨勢持續加速中
基因本身並不能提供所有答案
許願時要小心
病毒、螞蟻及惹人嫌惡的事情
第六章 氣候危機
氣候難民
為日益惡化的環境奮鬥
溫室氣體排放標準仍有爭議
人類已經啟動了全球暖化
沒有夏天的一年
危機愈強烈,解決的動機愈強大
臨海洋而居
第七章 邁向新神話
現代世界中的狩獵採集族
囚犯困境、道德起源及貪婪
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基本教義派的形成
臉書,奇異的國度
從過去思考未來
誌謝
譯後感 人類未來的希望 潘震澤
延伸閱讀
前言 該是停下來思索的時候了
第一章 地圖裡的奧祕
追尋人類的過去
基因珠鏈上的時尚珠粒
人類獨霸世界舞台的關鍵時刻
天擇青睞的基因
為什麼人類會選擇農業生活?
第二章 培植新文化
正在進行中的新革命——水產養殖
漁業大崩潰
冰壩融化,寒冬再度來臨
作物馴化中心
繁殖自己的食物
政府、宗教、軍隊的興起
第三章 疾病浪潮
肥胖成為流行病
儉約的基因,揮霍的口味
三波奪命潮:外傷、傳染病、慢性疾病
改變自然景觀之際,也種下瘧疾的種子
碳水化合物與蛀牙
新石器革命啟動的疾病潮,至今仍無可避免
...

 共
共  韋爾是德國北萊茵-威斯伐倫州的一個市鎮。總面積76.35平方公里,總人口32018人,其中男性16173人,女性15845人,人口密度419人/平方公里。
韋爾是德國北萊茵-威斯伐倫州的一個市鎮。總面積76.35平方公里,總人口32018人,其中男性16173人,女性15845人,人口密度419人/平方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