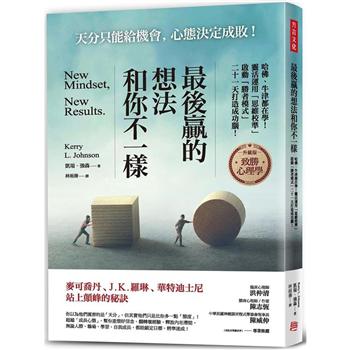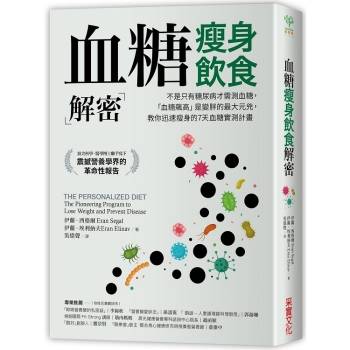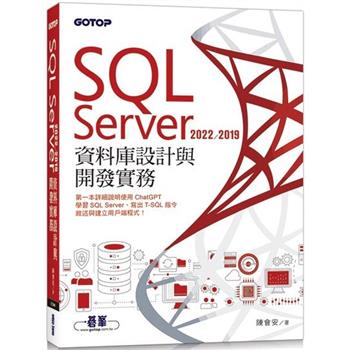巨大衝突中看見完美協調
悲劇的土地、悲劇的人物、悲劇的連結。
然而,吉姆.伍頓所成就的並非歷史悲劇,而是警惕世人的一記當頭棒喝。因著記者貫有的敏銳觀察與流暢文筆,這篇文章的地理座標,不單單是發生在約翰尼斯堡一位愛滋寶寶的故事,它更揭露整個非洲大陸面臨世紀黑死病橫掃的困境;同樣地,文章的時間向度,也絕非停留在穆白吉政府的時代,它更可以溯及種族隔離制度的開始。
文章的美,美在一開始就帶領我們認識諾西這位愛滋小男孩,一位一出生就面臨死亡、卻又堅強地與命運搏鬥的小勇士。當他穿梭在愛滋收容所裡當個小助手、當他拖著羸弱的身體遠渡重洋到美國為愛滋募款;他似乎已經完美地演出愛滋天使的角色!而這位小男孩自始至終只有一個似也純真、似也卑微的要求:「我們都是一樣的,我們跟別人沒什麼不同;我們懂得愛和盡情歡笑,我們會傷心也會難過得哭泣;我們出生,然後死去。」
每個人都不應該因為膚色以及他所無法控制的疾病而遭受到不公平的歧視待遇。可悲的是,這種公平正義的論調,在現實的社會裡,不過是天方夜譚。諾西一出生就面臨膚色以及遺傳疾病—愛滋,而遭受雙重的不平等待遇;悲慘的命運因為遇見了蓋兒媽媽,才譜出可歌可泣的樂章。
文章的動人,在於巨大衝突有了最感性的協調:蓋兒媽媽,一位堅強且懂得將母愛發揮到極致的白人女性,收養了一位感染愛滋病毒、整天拉肚子、全身上下黏液不斷的黑人小孩;而他們所處的環境更是極盡矛盾:一個愛滋病患人數激增的國家,但政府領導者卻選擇視而不見的鴕鳥心態。令人欣慰的是,巨大的衝突在這篇故事中,有了最完美的協調:不同膚色的種族、愛滋患者與健康族群、愛滋肆虐的國度與鴕鳥心態的政府,都因為蓋兒媽媽與諾西小男孩的努力,籓籬被打破、衝突有了親密的接觸。
打破衝突的界線、擁抱雙方,你知道有多麼不簡單嗎?當黛安娜王妃不戴手套和愛滋病患握手、當伊莉莎白泰勒親吻愛滋小孩枯槁的臉頰時,那畫面彷彿是電影虛構情節、離現實社會太過遙遠。因為,現實環境所上演的戲碼是:一群居民拉布條抗議,只因社區裡面有愛滋收容所。
同樣地,德雷莎修女為愛滋病患洗澡的故事,似乎也只能被視為童話裡的溫馨劇情;因為現實環境中,愛滋病患大多落到眾叛親離的下場。就像我到彰化採訪一位因白血病輸血而不幸感染愛滋的病患時,正值青壯期的他,孤獨地守在三合院老家,因為所有親朋好友紛紛遠離他,留他一人羸弱地照顧自己、留他一人慢慢地等待死亡。由於對疾病的無知造成人們對愛滋病患的莫名恐懼,而這莫名的恐懼更導致愛滋患者遭受無情的懲罰與社會的排斥。要越過這籓籬、打破這衝突,人類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文章的可貴在於伍頓以記者一貫的事實查證精神,明明白白告訴你,一九九七年全世界至少有三千六百萬人感染愛滋。只不過,那是十年前的數據,根據聯合國及衛生組織最新的資料顯示,全世界感染愛滋病毒的人數已經超過五千萬!當然,這恐怖的數據絕對不是要你瞠目結舌,而是提醒世人,切莫再鴕鳥心態無視於世紀黑死病的嚴重性。揭發事實是一回事,解決問題又是另一回事;所以,伍頓走訪其它非洲國家,為讀者尋找答案:結果,在愛滋病毒橫掃的非洲地區,他發現了HIV感染機率下滑的國家—烏干達,而這個國家竟然有三分之一的人民篤信嚴禁婚前性行為及墮胎的天主教!換言之,烏干達政府在天主教信仰下推動保險套教育的魄力,更能凸顯南非穆白吉政府在愛滋防治上的自欺欺人。當愛滋病毒像十四世紀的黑死病般橫掃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國家時,政府的角色非不能也,不為也。
伍頓流暢的敘事能力加入了記者的查證力道,更顯鏗鏘有力!
這不單是描繪親情的文學創作,也不單是愛滋議題的實證紀錄,它更是關懷世紀悲劇的警鐘。誠如伍頓所言,「每個人都應該以他生來的膚色感到驕傲、不管是白人、黑人,或是棕色、紅色、或是白色、黃的,甚至是綠色。」如果說,愛與治療是對愛滋患者最珍貴的禮物,那麼,蓋兒媽媽用愛給了諾西短暫生命中最寶貴的親情;而伍頓則是用筆鋒給了所有愛滋患者及健康族群最難得的一課。
悲劇的土地、悲劇的人物;不凡的連結。
引言
新聞界的神秘就在於新聞從業人員似乎總是被付以報酬過著充滿期待的美好生活。提到這個,乃至於根據我們族群裡最懶散成員的瞭解,可以在特定的日子等到十足的驚喜。事實上,在我多年的職業生涯以來,我變得總是對那些不應當感到吃驚的事而感到萬分驚愕。然而,許多年前,當我第一次踏上非洲土地時,我毫無心理準備地接受了它對我造成的衝擊,即使那是它最初而短暫的面世,我卻從此發現了來自自然、文化、與歷史那般遼闊的景色與美麗,遠遠地超出了自己文化對於如此美景的尋常定義。
於是我一次又一次地重返非洲,不只是為了這片土地,而是為了那些我所見過以及曾經與我分享著豐富故事的人們。
我聽過以各種語言與方言表達的「非洲之母」,幾年下來,我用英語訴說這些文字,逐漸地以我的方式訴說屬於她的故事。當然,我們每個人都可以使用這個貼切的名字。若超脫於象徵主義之上,它對我們而言的確扮演著母親的角色-它是生命的搖籃,我們從那裡出生、紮根,無論我們生來是什麼膚色的人種。留在奈洛比(Nairobi)用過晚餐之後的一個夜晚,我與李察.利奇(Richard Leakey)回憶起這項象徵性關連的魅力。
這位有名的人類學者是位白人,他一廂地認為自己與鳩摩?肯亞達(Jomo Kenyatta)一樣是個不折不扣的肯亞人,笑著說道,「非洲啊,這個老傢伙,可是每個人的家鄉呢!」,或許那樣的見解是引領我重返非洲的部分原因,感覺在某種奇特的程度上,我確實是回家了呢!
毫無疑問地,身為一名記者,我在非洲的日子,深受映入眼簾的一些重要故事所吸引著,那些故事留給我的回憶,同樣的驚人而美麗:在剛果夢魘般的時刻,我目睹了一位身在盧安達的母親,把她死於斑疹傷寒的孩子翻轉推上如山丘成堆的屍體上頭,然後轉身走下來,平靜地迎向塵土飛揚的路面,一眼望盡遠方的山巒起伏;在辛巴威一個令人恐懼的午后,身為旅客之一的我所搭乘的小飛機墜落在大批眼鏡蛇出沒的田野間;有次在衣索匹亞,我被一群數十名從未見過白人的孩子狀似光榮地用拳頭拍打著,彼此擠來擠去之下,不幸被推倒在地;還有當尼爾森?曼德拉仍在獄中的時候,我花了一段漫長的時間與他的太太與孫兒相處。
而這本書始於這些故事的其中一部份。
這是關於一個來不及長大的黑人小男孩與一個從未放棄的白人女性的故事。它沒有快樂的結局,甚至也沒有一個充滿希望的開端,這個孩子沒有選擇的餘地,也沒有任何機會,而這名女性因她所挺身對抗的一切而順勢體悟了所有的生命歷程。後來他們彼此分離,各過各的生活,現在他們或多或少已成為不起眼的尋常百姓。而不論是獨自或分開過活,任何一種生活形式都已被忽視或已被遺忘在南非民眾生活中更大的一股洪流裡,但他們並非舉無輕重。總括來說,不管如何,他們所帶來的影響持續地佔有重要的地位。
我在他們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說是微乎其微的,或許我還不算是資深的記者,但也是個老鳥了,應該懂得比較多,然而即使我做了所謂不摻雜的努力,也就是維持記者一貫謹慎的距離,對於所看到、聽到的事不加以涉入個人情感因素,我還是被這位小男孩與這位女性強烈地吸引著,一如非洲那樣地使我傾心。差不多在我明白一切將會是如何之前,我們就已成了彼此的莫逆之交。
所以,帶著一些狀似勉強、反覆不多的練習,我把自己安插在他們故事裡頭的某一個觀點,不過為了提供整個故事的背景與來龍去脈-而且,我猜想,可以藉此強化故事本身的吸引力,進而對一些徹底決意維持超然立場的人們產生效應。
這就是我的寫作目的,當我開始撰寫他們的故事時,維持一貫穩定而直截了當的敘述手法;最後,無論如何,我發現有一些小環節與離題是不可避免的。
或許要表達的內容真的太多了,但是如果盡可能的抓住這個、那個故事,人們想要清楚地知道它們負有歷史、情感、政治的包袱,但卻無法掌握歷史、情感、政治領域等相關知識的話,一路讀來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就像大部分真正美妙的故事一樣,我心裡明白若只是純粹地敘述,這篇故事必然失色許多,而我的報導也無法重建真實,不能藉著寫作捕捉他們生命裡的豐富內涵與活力,然而,我的信念是,任何一個人都能擁有幸運與他人一同跨越生命的軌跡,特別像是這名小男孩與這名女性一同責無旁貸的向他們的故事邁進,姑且不論他們憑藉的媒介含有多少瑕疵或者方法有多麼的不完美。
也正是帶著那樣與生俱來的不完美,我嘗試著去完成這一切,樸實無華地在這些扉頁中向前邁進,相信有些知識的確是超出我能力所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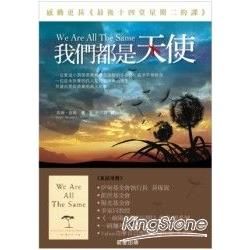

 共
共  2008/03/12
2008/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