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曾湮沒在歷史洪流中的臺灣詩人與文人
一段兒子尋找謎樣父親的動人故事
一段研究者探訪被遺忘作家的故事
帶領讀者進入詩文譜下的跨時代文學與歷史世界
在那波瀾壯闊的一九三○年代,在東京街頭一隅,一個殖民地臺灣南投山城之子,獻身紅色馬克思,用詩文譜下生命的希望,與燃燒的痛苦。
他的詩洋溢著南國情熱,以水牛、烏秋、白鷺鷥與苦苓樹抒發對故鄉的思念。他的詩滿懷對不義政體的控訴,從街頭浪人、工廠勞動者、客死異鄉的藝術家到被俘囚的異議分子。他的詩銘刻著殖民地與現代性的傷痕,即便湮沒在歷史的洪流中許久,仍舊如此深刻而令人動容。
他是吳坤煌(1909-89),少時因發起學運遭臺中師範學校退學,後負笈東京留學,前後肄業於日本大學藝術專門科及明治大學文科等。1933年同張文環、王白淵、劉捷、蘇維熊、施學習、巫永福等人組織了「臺灣藝術研究會」,並發行「福爾摩沙」文學雜誌,是東京臺灣藝術研究會發起人及負責臺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參與雜誌《福爾摩沙》及《臺灣文藝》的組織運作。他才華洋溢而風流倜儻,文友知己遍及臺灣、日本、中國及朝鮮,透過詩文寫作與戲劇演出進行東亞左翼文藝社團的跨國連結,譜出殖民地文學史上傳奇而炫目的一頁。
他為反殖民運動付出兩度身陷囹圄的代價,依然天真浪漫不改革命熱情。祖國接收後經歷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十年牢獄之災讓他噤聲與輟筆。他在國民政府的「心牢」中自囚封筆三十年,再出發已距離風雲叱吒的東京時期半世紀久遠。
他在晚年仍不忘以「詩人梧葉」自居,整理舊作成為遺願。這個願望在二十年後由他的長子吳燕和與一個年輕的臺灣文學研究者陳淑容共同完成。兩位編輯獲得海內外諸多人士協助,用數年時光拼湊出這塊臺灣文學史上瑰麗而陌生的版圖。
《吳坤煌詩文集》收錄的吳坤煌日文詩文作品,絕大多數都是此次首度中譯並公開出版。這是包括《テアトロ》、《生きた新聞》、《詩歌》、《詩精神》、《詩人》、《臺灣文藝》、《臺灣新民報》、《臺灣新聞》等報刊上的珍貴文獻;編輯者也致力蒐羅戰後作品,以全面呈現作家橫跨半個世紀的寫作為目標。
《吳坤煌詩文集》的展開,隱藏著兒子尋找父親、研究者探訪被遺忘作家的一段動人故事。編輯更透過年表、家族世系表、著作目錄、媒體報導及研究文獻等資料彙編,讓讀者得以掌握相關研究動態。書前並附叢書主編梅家玲及主編吳燕和、陳淑容序。
希望透過這些作品展演吳坤煌的文藝美學、思想轉折與行動演練。擴大來說,他的生命歷程與書寫,能夠成為跨時代知識人的縮影,填補不為人知的臺灣歷史與政治。
作者簡介:
吳坤煌(1909–1989),筆名「梧葉生」、「北村敏夫」、「譽烔煌生」,臺灣南投人。少時因發起學運遭臺中師範學校退學,後前往東京留學,成為東京臺灣藝術研究會及臺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的發起人,參與雜誌《福爾摩沙》及《臺灣文藝》的組織運作。才華洋溢的吳坤煌,文友知己遍及臺灣、日本、中國及朝鮮,透過詩文寫作與戲劇演出進行東亞左翼文藝社團的跨國連結,譜出一九三○ 年代殖民地文學史上傳奇而炫目的一頁。戰時旅居北平,結婚成家後返臺,後因白色恐怖繫獄十年,與文壇隔絕三十年而於晚年再出發。吳坤煌的生命及書寫是二十世紀臺灣歷史的重要見證與縮影。
主編簡介
吳燕和
吳坤煌的長子,一九四○年生於北京,臺大考古人類學系畢業,夏威夷大學人類學碩士,澳洲國立大學人類學博士。曾任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研究員兼人類學研究所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主任。現為夏威夷大學教授,東西中心資深研究員,中研院民族所兼任研究員。五十多年在南太平洋、東南亞、中、日、臺作田野調查。發表專書十餘種,論文百篇。
陳淑容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博士,曾任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現為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專長領域為現代文學、殖民地文學及報刊文藝研究。著有《一九三○年代鄉土文學/臺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曙光」初現:臺灣新文學的萌芽時期(1920-1930)》等書及研究論文多篇。
作者序
序一 吳坤煌研究的新起點 (叢書主編梅家玲序)
2009年9月,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和哈佛燕京學社合作舉行「交界與游移—近現代東亞的文化傳譯與知識生產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第二天,我們安排一場「重返《福爾摩沙》—蘇維熊、吳坤煌及其時代座談會」,討論三○年代升學「帝都」東京的臺灣留學生文藝團體「臺灣藝術研究會」成員的文藝活動,並特地邀請「臺灣藝術研究會」核心成員之一的蘇維熊哲嗣蘇明陽教授、吳坤煌哲嗣吳燕和教授與會。當時吳燕和教授雖遠在夏威夷,無法出席,但是寫了一封文辭並茂的英文發言稿,請廖炳惠教授翻譯代讀。會後,我們隨即得到蘇明陽教授和吳燕和教授的同意與協助,由臺大出版中心整理翻譯出版《蘇維熊文集》、《吳坤煌詩文集》。2010年11月,《蘇維熊文集》順利出版,蘇明陽教授專程從美國洛杉磯返臺出席在臺大總圖書館舉行的新書發表會,吳燕和教授正值在交通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亦特從新竹趕來與會,新書發表會上,蘇、吳兩位教授相視而笑,交談甚歡,溫馨的畫面令人難忘。當時預定隔年即要出版《吳坤煌文集》,但由於種種因素,直到今天總算順利問世,作為叢書主編,懸在心上多年的一塊大石,才算卸下。
在《蘇維熊文集》的代序〈立足鄉土,放眼世界─「臺灣藝術研究會」發起人蘇維熊教授與《福爾摩沙》〉一文中,我曾提及:關於《福爾摩沙》集團之整體研究已有豐碩成果,但是《福爾摩沙》集團之成員的個體研究,依然相當有限,《蘇維熊文集》、《吳坤煌文集》的出版,除了表示對前輩作家的敬意、為臺灣文學史料的整理翻譯盡點綿薄之力外,同時也希望有助於《福爾摩沙》集團成員之個體研究的進一步開展。
吳坤煌在戰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被遺忘,主要原因是1939年他即前往中國大陸發展,同時遠離臺灣文壇與日本文壇。他於1946年返臺,1948年曇花一現地出現在《新生報》「橋副刊」的作者茶會上。1950年,他被指控參與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活動,入獄十年,出獄後經商,將近有三十年與臺灣文壇處於絕緣狀態。一直到1980年,故黃武忠先生發表他的訪談,同年年底,相隔了三十二年,他在《自立晚報》發表了隨筆〈悼老友漢臣兄〉,隔年年初,羊子喬先生也發表了吳坤煌的詩論。1981年出版的《寶刀集─光復前臺灣作家作品集》(聯合報)、1982年出版的《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遠景),分別選錄了他的詩作,才又喚醒學者與文學界注意到這位前輩作家。至於他大陸時代的事蹟與戰後入獄的經過,則須等到吳燕和教授在2006年出版其回憶錄《故鄉‧田野‧火車─人類學家三部曲》之後,才大白於世。
而令人興奮的是,不只是臺灣學者,日本學者也注意到了吳坤煌的存在,日本關西大學北岡正子教授在九0年代初開始發表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東京支部的相關研究,包括:〈日文研究という雑誌(下)―左連東京支部文芸運動の暗喩―〉(《中国―社会と文化》第五号,1990年6月)、〈雷石榆《砂漠の歌》―中国詩人の日本語詩集〉(《日本中国学会報》第四十九集,1997年10月),發現了東京時代吳坤煌與當時日本左翼文學團體與作家、中國留學生左翼文學團體與作家、滿洲國留學生左翼作家的來往,此一研究,也影響了2000年中期以後下村作次郎教授與柳書琴教授關於東京時代吳坤煌的細部研究。
吳坤煌的詩文早已散佚,蒐羅不易,為了編輯這本文集,陳淑容博士上窮碧落下黃泉,反覆斟酌,投注了多年的心血與時間,令人感動。吳燕和先生撰寫〈重新認識父親吳坤煌〉長序,從為人子者的角度,為讀者呈現對吳坤煌先生的近距離觀照;在詩文譯作及相關研究之外,凸顯了不為人知的許多點滴,特別值得細讀。這幾年還有不少臺日學者關心《吳坤煌文集》的出版,並主動提供資料給編者,使本書的內容益趨豐富。特別是下村作次郎教授與柳書琴教授,除資料外,還提供了個人的相關研究論文,盛情銘感於心。只可惜後來因篇幅及體例所限,未能收入,十分遺憾。柳書琴教授多方協助此一文集的出版,更義務花費寶貴時間協助校訂,使本文集更臻完善;在此都要一併致謝。而我們也相信,《吳坤煌詩文集》的出版問世,將會為臺灣文學研究注入新的源頭活水,它將是吳坤煌,以及與他同輩的臺灣作家研究的一個新的起點。
序二 重新認識父親吳坤煌 (主編吳燕和序節錄)
母校臺灣大學的出版中心計劃出版先父作品文集,因此央我寫序,介紹我所認識的父親,以及他在世時的生活點滴,是文獻資料中看不到的那一面。
我介紹我的父親,其實是一件難事,我一生與他見面的日子屈指可數,與他面對面兩人談話的場合,僅止於兩三次而已。雖然我在大學時代,他出獄之後的兩、三年,閱讀了當時被查禁的他的故友王詩琅所譯《台灣社會運動史》(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社會運動史部分,後來一九八八年再由臺北縣稻香出版社出版,日本官方編輯的臺灣人反日史料),知道他自一九三○年在日本求學時即是位豐富多產的熱情詩人、演員、社會評論家,也看過他文筆流暢的中文文章和書信。平時他是一位寡言的人,與我談話多半只有「是」與「不是」。從我小學五年級(1951)直到高中畢業,他被關在綠島(火燒島),這八年我們保持著通訊,因而建立起超出一般父子的深厚情感。我知道自己在他心中占有極為特殊的地位,而我亦對他極為崇敬與佩服,他對理想的堅持,以及面對痛苦折磨的不屈毅力都異於常人。假若缺乏了近年臺灣文藝界人士的努力、臺灣近代史學與文學史研究亦無法振興、甚或是父親的著作被多位日本和臺灣學者發掘整理出來的話,我也不可能在古稀之年重新認識父親,聽到八、九十年前他作為一個臺灣青年的吶喊心聲。
我感謝臺灣文學界,帶我走入先父跨國跨境、超越時空的想像世界。從前我不瞭解先父的想像(imagination)是多麼的全球觀,他的文章揭示出臺灣人前輩作家在二十世紀初期,早已超越現代的想像與敘事。我很驚訝,八十年前一位來自臺灣深山的鄉下孩子,能在日本教育之下,浸淫在歐洲文明的理想大同世界。父親書寫的南投家鄉,是南歐地中海的小城,是一個女性化的意象(imagination),像他(八十年前)盼望得到解放的臺灣女性們。父親雖然沒能提筆寫下他漂流過的東京、北京、徐州、上海、甚至綠島,但是就像他的故友劉捷所描述的,父親是一位不可救藥的樂觀者,如果他執筆描繪這些城市,應當會表現出他一輩子在堅苦險惡環境之下,仍然懷有羅曼蒂克的、性別化的憧憬情懷(gendered, nostalgic imaginary)。
一、慈愛的父親
現在讓我從兒時的片斷回憶,談談我記憶中的父親,也許多少能填補一點他那從未被瞭解的空白的一生(這些回憶過去都沒有發表過)。
我從臺灣文學界的討論,聽到一個耐人尋味的疑問:為什麼青年時代熱愛家鄉,提倡脫殖民地文學與臺灣文化的多產詩人,同時亦是當年在東京跟中國大陸五四之後以文學家、戲劇家齊名發表的著名作家(見後),一九四六年回到臺灣之後,卻消聲匿跡、不再寫作?除了他從一九四八年起遭受三次牢獄之災,一九六一年終於出獄,一九八九年去世,這段期間幾乎全然封筆,我以下的回憶,或能為尋求答案提供一絲線索。但因長輩、家人俱健在,故我不能暢所欲言,以免造成誤解與遺憾。再者,我仍然期待研究臺灣近代史與文學史的學者們的努力,掀開前輩臺灣人的神祕面紗,讓我們了解到臺灣近代史之巨輪下,輾過、犧牲了多少有才華的悲劇性臺灣人。
我記得的父親的形象,是一位帶著滿臉笑容望著我的慈父。我的腦海中立即浮現五幕有他的臉孔的畫面,是我三歲至九歲之間,橫跨北京、南投、臺北三地的畫面。
第一幕畫面是父親抱著我,伸手指著遠方(北平)故宮高牆的一角,那是居於護城河上方的宮牆角樓。我當時應該只有三、四歲(我一九四○年出生)。父親笑著對我說話,我不記得說話內容,卻仍然記得站在護城河外圍的走道上,身旁一片綠色的田野。父親抱著我,要我朝著他手指的方向看出去,壯觀的高牆和蒼黑色角樓映入眼簾。那天也許是星期日或者假日,因此父親有閒暇帶我出門遊逛,但是我不記得母親是否也在身邊。
第二幕畫面也是在北京,應該是我四、五歲的時候。我坐在父親懷裡,他和母親並坐在高大的洋車上(由一位車夫在前面拉著跑的「人力車」)。我手裡還抓著紙糊玩具。印象中我們剛從天橋廠甸出來,在當時它是最熱鬧的遊樂區。人力車朝著回家的方向前進,四周的行人和車馬熙熙攘攘。
第三幕是父親帶著笑臉對我說話的畫面,那時我們回到老家南投,我大概六歲左右,應該還沒念小學一年級。我從外頭回家,一手提著一個小水桶,另一手拖著一條竹竿,竿尾綁著一個鐵勺。我看過祖母在我家院牆外面的水田旁邊,撈取綠色浮萍小草,回家餵她養的鴨子。鴨子們搶著吃水草,祖母告訴我鴨子最愛吃那種水草。
那天好像沒人在家,我偷偷拿了祖母的工具,走出家門,在道路的水田邊,學著祖母的動作打撈水草。等我心滿意足地回家,進入第二道院門時,看到父親高高在上地站在飯廳的玻璃門邊,低下頭望著我。我大吃一驚,因為我全身髒汙、雙腳沾滿水田的泥濘,怕挨父親的罵。結果出乎我意料之外,父親竟然笑著說:「真好,你真能幹,會幫忙找鴨草了。趕快把東西放好,去洗腳吧!」
我在南投鎮(原縣政府所在地,即今南投市)上小學一、二年級(1946 - 1948),很少在家中看到父親。除了知道二二八時,他曾經兩度被捉去關(總共前後兩年間)之外,最近才聽母親說起,當時父親在草屯初中教書,而她在南投初中教書(當時還沒有高中),後來四姨(母親的四妹:張若蕖)隻身來臺,就是透過父親介紹而在草屯初中教書。當時隨著我們回臺的五姨(張若蚨,她也在南投初中教書。她畢業於北京某間初中,是後來出名的考古家、中研院副院長張光直的同學。五姨還告訴過我,張光直的奶名叫「玲玲」。)
當時與父親來往的朋友們,都是地方上的大人物。記得父母經常帶著我到鎮長、銀行經理家串門、吃飯。每次在別人家吃晚飯,飯後大人們盡情談笑,可是最後的娛樂節目總是叫我出來唱歌,我好像唱過白光的歌,也唱過李香蘭的〈夜來香〉。我還記得我就讀的南投第二國民學校(原稱平和小學)的校長──張慶沛,是父親從小一起長大的好朋友。
有一次小學舉辦運動會,我沒想到父親會穿著全套西裝、打著領帶,出現在台上的貴賓席。後來他下台跟另外一位來賓表演打網球,周圍的老師和同學們圍著觀看,只有我躲得遠遠地,深怕同學知道那是我父親,這樣會讓我覺得不好意思。
我記得在南投那兩年,父親英姿煥發,穿著時髦、瀟灑,有時父母參加親友的喜慶宴會,他們會變成大家注目的焦點,反而忘了看新人。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家中來了一對穿著光鮮美麗的夫婦,從外地來訪,和父母有說有笑,然後一起出門遊玩,好多天沒有回家。多年之後我詢問母親,才得知他們是父親在日本時的好友──雷石榆和他的臺灣妻子──出名的舞蹈家蔡瑞月。父母帶他們去日月潭遊玩。
第四幕畫面是我就讀臺北國語實驗小學三年級的某個星期天。那天父親帶著我和弟妹,還有我的同學夏永田一共四人,乘坐每天接送他上班的汽車,清早就出發去圓山動物園(現在的中山北路四段、基隆河畔的小山上)。到達動物園門口,下車之後父親先去買了椪柑和糖果,分給我們。大家興高采烈地在動物園玩了一整天。這幕畫面裡好像又沒有母親的出現,可能她在家享受難得的晨睡吧!
序三 重讀吳坤煌:思想與行動的歷史考察 (主編陳淑容序節錄)
前言:吳坤煌的探問
一九三三年底,在東京發行的《福爾摩沙》(フォルモサ) 文藝雜誌上,吳坤煌發表一篇〈臺灣的鄉土文學論〉(臺灣の鄉土文學を論ず)。這是繼黃石輝以〈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一文揭揚鄉土文學論戰的大旗三年後,也幾乎是在整個論戰末期所發表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吳坤煌以宏闊的篇幅闡明其鄉土文學觀,嘗試跳開島內臺灣話文/中國白話文派的對立,將論辯提昇到階級層次,更是這篇文章的重要論點。吳坤煌說:「臺灣許多文學創作之中,如果描寫臺灣人的生活,而作品中沒有民族的動向,或沒有豐富的地方色彩,也不能算是我們向來主張的鄉土文學。」他引證列寧、史達林、藏原惟人的觀點,指出無產階級必須針對這個故有的文化遺產進行批判與再改造,提出內容是無產階級的,形式是民族的大原則,為建立將來的共同語言的統一文化創造條件。那麼,作為弱小民族的臺灣,其統一的文化語言為何?吳坤煌認為是能夠以承載民族文化遺產的共通語言。
這篇文章並沒有給我們回答一方面能夠串連普羅大眾,一方面又可以批判性地承繼民族文化遺產的「共通語言」究竟是什麼。換句話說,吳坤煌並不認為當時的臺灣存在著所謂的「共通語言」。也就是,在斟酌臺灣社會的實況之後,他將「共通語言」的存在與設立視為未來式的問題,而非理所當然地將「臺灣話文」等同於代表「普羅」的共同語言。這個論點想當然爾將引起島內諸多同志的撻伐,但終究發表時間已近論戰尾聲,再加上以日文發表在東京《福爾摩沙》同人誌上也限制了其影響力,因而我們無法看到太多相關的討論。事實上,在以日文寫就,發表於東京的同時,吳暴露他身為殖民地子民的限制;卻也開啟了日文作為一種連結工具的可能。
但這終究不是吳坤煌的問題,對他而言,語文究竟不只是工具,重點是這個語言承載了怎樣的民族文化?很顯然這是不同於統治者,屬於臺灣獨特經驗的文化。這個文化如何承繼傳統?並開花結實?對吳坤煌來說,其題解必得回到階級問題──也就是透過無產階級的改革,分析何謂真正的臺灣文化,然後才有隨之而來的語文問題產生的可能。吳坤煌對於「共通語言」的想像以及論述很顯然超乎了同時代臺灣作家的理解,事實上,在相隔論戰七十餘年的今日,他的探問依然未被正視。
本文將從吳坤煌對於「鄉土文學」的提問出發,梳理一個臺灣作家的生命故事。這個集詩人、文學評論及劇評家等多重身分於一的前輩文化人,在殖民統治壓力下,其身上銘刻了試圖逃離此困境而烙下的印痕。這些私密的個人經驗,連接他的思想與行動,反映多重殖民歷史下,跨時代文化人的掙扎與苦鬥。
序一 吳坤煌研究的新起點 (叢書主編梅家玲序)
2009年9月,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和哈佛燕京學社合作舉行「交界與游移—近現代東亞的文化傳譯與知識生產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第二天,我們安排一場「重返《福爾摩沙》—蘇維熊、吳坤煌及其時代座談會」,討論三○年代升學「帝都」東京的臺灣留學生文藝團體「臺灣藝術研究會」成員的文藝活動,並特地邀請「臺灣藝術研究會」核心成員之一的蘇維熊哲嗣蘇明陽教授、吳坤煌哲嗣吳燕和教授與會。當時吳燕和教授雖遠在夏威夷,無法出席,但是寫了一封文辭並茂的英文發言稿,請廖炳惠教授翻...
目錄
圖輯
編輯說明
吳坤煌研究的新起點 梅家玲
重新認識父親吳坤煌 吳燕和
重讀吳坤煌:思想與行動的歷史考察 陳淑容
輯一 詩
烏秋
旅路雜詠之一部(一)
城市之聲
悼陳在葵君
南蠻茶房
貧窮賦
冬之詩集(一)
晚秋與少女心
婚約者、婚約者
吹向丸之內街道的風
拂曉之夢
冬之詩集(二)
飄流曠野的人們
歸鄉雜詠(一)
更夜之歌
基隆碼頭下著小雨
歸鄉雜詠(二)
苦苓樹籽真正苦
思念秀鳳
母親
旅路雜詠之一部(二)
阿母
孤魂
向我求婚吧
搬家
俳句圓山
歸鄉雜詠(四)
南投之秋,謹獻給父親
處女離家出走
歸鄉雜詠(五)
秋的哀愁
淡淡的一夜不連續篇
宇宙之狂歌
悼老友漢臣兄
烏秋咬球
詩二首
白鷺鷥報春喜
種有木瓜樹的鄉鎮
輯二 文
致某位女性
臺灣的鄉土文學論
南國臺灣的女性與家族制度
臺灣老鰻傳奇
中國通信
現在的臺灣詩壇
農民劇團與露天劇:中國通信
出獄後的田漢與南京劇運
《春香傳》與支那歌舞伎之元曲
日本電影的勝利《田園交響樂》:兼談知性文學
旅與女
悲劇女主角秋琴:《可愛的仇人》讀後感
新北投遊記
藝旦的教育
戲劇之道:對皇民化劇之考察
給臺灣女性的公開信
臺灣戲劇通信
州內皇民化劇問題
續戲劇之道:戲劇創作ABC
臺灣藝術研究會的成立及創刊號
《福爾摩沙》前後回憶一二
懷念文環兄
輯三 譯文及其他
鹽
東京支部設立
東京支部提案:呈臺灣文藝聯盟總會
東京支部為將於七月來臺之舞蹈家
崔承喜小姐舉辦歡迎會
臺灣文聯東京支部通信
東京支部例會報告書
附錄
一、座談會發言
二、媒體報導
三、吳坤煌生平年表與同時代大事年表
四、家族世系表
五、著作目錄
六、研究文獻目錄
編後記 陳淑容
圖輯
編輯說明
吳坤煌研究的新起點 梅家玲
重新認識父親吳坤煌 吳燕和
重讀吳坤煌:思想與行動的歷史考察 陳淑容
輯一 詩
烏秋
旅路雜詠之一部(一)
城市之聲
悼陳在葵君
南蠻茶房
貧窮賦
冬之詩集(一)
晚秋與少女心
婚約者、婚約者
吹向丸之內街道的風
拂曉之夢
冬之詩集(二)
飄流曠野的人們
歸鄉雜詠(一)
更夜之歌
基隆碼頭下著小雨
歸鄉雜詠(二)
苦苓樹籽真正苦
思念秀鳳
母親
旅路雜詠之一部(二)
阿母
孤魂
向我求婚吧
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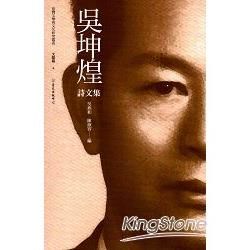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