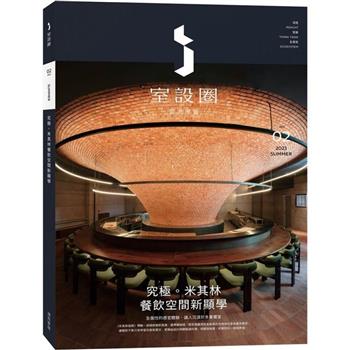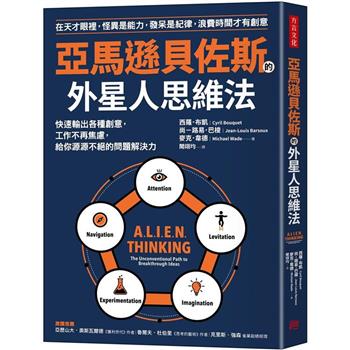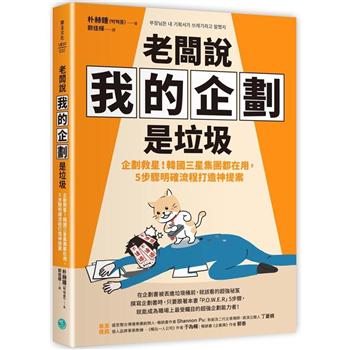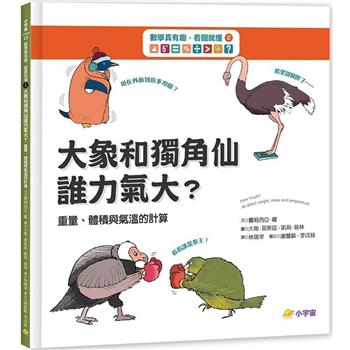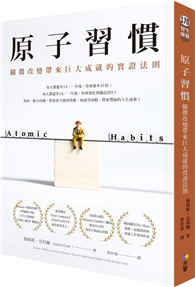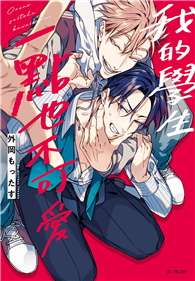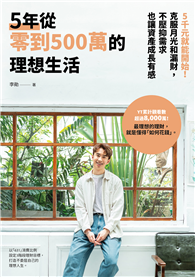現代科學就本質來講應稱西方科學,原是西方民族透過他們特有的宇宙觀與方法論,來對客觀運動及其外在世界所作的詮釋(物體&空間)。他們所發現的引力、電磁力、核力等,威勢驚人,便把歐美國家次第推上全球列強的寶座。但是,隨著現代科學日益出現矛盾分裂,各種最新證據顯示,科學理論無法充分說明真實世界,西方列強也步入盛極將衰的轉折。今天,「後科學」時代無疑已經來臨。
中國文化──以儒家為核心──數千年來針對天(超越)、地(自然)、人(人界)窮盡探詢,其形上特質似乎更能反映現實世界。本書因此揭櫫新興儒學,盼為明日世界領航。從傳統儒學本質出發,包括特有的宇宙模型與綜合方法,再經過融科學入儒學,便能打造出新興的「科學儒學」,進而為中國科學喊出啟航先聲。
本書特色
中國科學另闢蹊徑,是研究客觀變動及其內在結構的學理(事物&時間);二十一世紀人類有望由此找到科學突破,預期盛開嶄新知識的奇花異卉。
作者簡介
周哲水
1946年生。
學歷:臺灣大學農學士,英國倫敦大學農經、電腦碩士。
曾任: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講師,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所研究員,國外電腦公司高級主管、董事等職。
現任:「時間試驗」計畫主持人。
著作:《世紀大預言》(風雲時代,1995)、《挑戰西方科學》(正中書局,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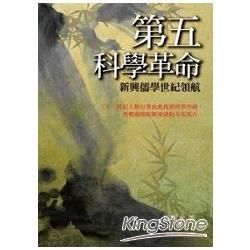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