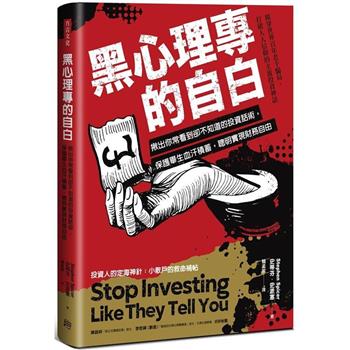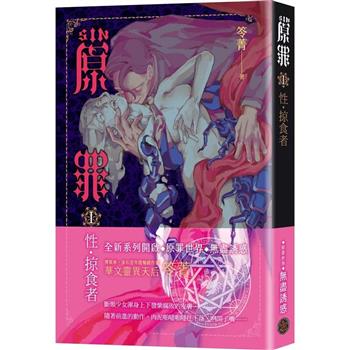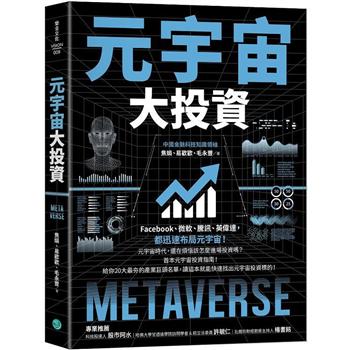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周復漢的圖書 |
 |
$ 395 ~ 475 | 滄桑回顧錄
作者:周紹賢/周復漢 出版社:致出版 出版日期:2021-07-12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滄桑回顧錄
內容簡介
《滄桑回顧錄》是作者從山溝裡的家鄉為了保家,隨時勢演變而浪跡大江南北,流落海角一隅,終至落葉而無根可歸的人生旅程;也是自十九世紀以來上億臉龐模糊但血淚分明的中國小民從身不由己的經歷與視野所述說的近代史。對照中國近代官史,《滄桑回顧錄》是人民的歷史。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周紹賢(1908/4~1993/10)
名延著,號「松華山人」,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童年師從晚清進士楊玉相,讀五經,習詩文。1933年,就讀於梁漱溟創辦的鄉村建設學院,畢業後,從事鄉村建設工作,任濟寧、曲阜等縣實驗區校長(即區長)。抗戰爆發後,山東淪陷,回鄉組織游擊隊。1938年,參加威海向陽山之戰。嗣任山東第七行政區保安第一旅政治部主任。1943年夏,因作戰受傷,赴皖北,後於山東政治學院任教。抗戰勝利後,任青島市《公報》主筆,並被選為市議員。1949年秋去台灣,曾任東吳大學、師範大學、政治大學教授,兼任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著有:《魏晉清談述論》、《道家與神仙》、《老子要義》、《莊子要義》、《孔孟要義》、《荀子要義》、《列子要義》、《大道之行–儒家發展概述》、《佛學概論》、《中國文學述論》、《論李杜詩》、《漢代哲學》、《魏晉哲學》、《先秦兵家要旨》、《道教全真大師丘長春》、《文言與白話》、《應用文》、《松華軒詩稿》等。1987年移居山東西魯家夼村。
周紹賢(1908/4~1993/10)
名延著,號「松華山人」,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童年師從晚清進士楊玉相,讀五經,習詩文。1933年,就讀於梁漱溟創辦的鄉村建設學院,畢業後,從事鄉村建設工作,任濟寧、曲阜等縣實驗區校長(即區長)。抗戰爆發後,山東淪陷,回鄉組織游擊隊。1938年,參加威海向陽山之戰。嗣任山東第七行政區保安第一旅政治部主任。1943年夏,因作戰受傷,赴皖北,後於山東政治學院任教。抗戰勝利後,任青島市《公報》主筆,並被選為市議員。1949年秋去台灣,曾任東吳大學、師範大學、政治大學教授,兼任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著有:《魏晉清談述論》、《道家與神仙》、《老子要義》、《莊子要義》、《孔孟要義》、《荀子要義》、《列子要義》、《大道之行–儒家發展概述》、《佛學概論》、《中國文學述論》、《論李杜詩》、《漢代哲學》、《魏晉哲學》、《先秦兵家要旨》、《道教全真大師丘長春》、《文言與白話》、《應用文》、《松華軒詩稿》等。1987年移居山東西魯家夼村。
目錄
▌序
▌滄桑回顧錄
一、登州之邑 海陽故鄉
二、家境淒涼 命途多舛
三、自幼好學 愧無所成
四、舊社會之殘影
五、清室腐敗 引起革命
六、群雄爭權 自相攻伐
七、聯俄親日 神州失色
八、日寇親華 共黨壯大
九、戰塵之中 艱苦生涯
十、流落皖北 所見所聞
十一、抗戰結束 神器易主
十二、小住青島 浪迹江南
十三、狂風暴雨 飄泊台灣
十四、往事成空 舊夢如昨
▌煙台聯中冤案
一、煙台聯中澎湖罹難
二、張鄒等之冤家
三、我在冤案死而復生
▌周復漢(建文)的流亡日記
▌臨終自吟與自輓
▌滄桑回顧錄
一、登州之邑 海陽故鄉
二、家境淒涼 命途多舛
三、自幼好學 愧無所成
四、舊社會之殘影
五、清室腐敗 引起革命
六、群雄爭權 自相攻伐
七、聯俄親日 神州失色
八、日寇親華 共黨壯大
九、戰塵之中 艱苦生涯
十、流落皖北 所見所聞
十一、抗戰結束 神器易主
十二、小住青島 浪迹江南
十三、狂風暴雨 飄泊台灣
十四、往事成空 舊夢如昨
▌煙台聯中冤案
一、煙台聯中澎湖罹難
二、張鄒等之冤家
三、我在冤案死而復生
▌周復漢(建文)的流亡日記
▌臨終自吟與自輓
序
序
陶唐盛治之世,帝堯欲知民間對政府之感應,乃微服遊於康衢,聞民謠云「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列子仲尼篇)。帝堯是君主,在現代民主風尚之中,一般人最好訶斥專制帝王,故對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更認為是愚民政策,使人民無知無識,只順從法令,甘作奴隸而已;不相信唐虞盛治之文獻,目的在乎推翻歷史,打倒中國文化,此種反常之病,成為時代流行之症,神醫亦不能使之接受藥石。
世道之治亂,非泛泛之群眾所能造端;流芳百世,遺臭萬年,皆非凡人所能為。禹、湯、文、武、漢祖、唐宗,治國平天下之聖哲,當然為「非常」之人;赤眉、銅馬、黃巾、黃巢,能造反作亂,荼毒萬民,亦為非凡人物。「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大學、孟子告子篇)。李、唐趙、宋,得群眾之擁護而統一天下;李自成、張獻忠亦得群眾之擁護而禍害天下;一治一亂,皆賴群眾之力量,然主動均不在群眾,而在傑出之非凡人物,群眾永不能作主,永須受領導,作為「順帝之則」之服從者。蚩蚩之氓,碌碌之輩,當隆治之世,則一倡百和,歌頌昇平;當板蕩之秋,則盲從強霸,滋長亂端。亂紛紛蜂唼蜜,密匝匝蟻排兵,鬧攘攘蠅爭血,造成陰霾充塞之恐怖世界,良莠混合,玉石俱焚,強梁者亦互相吞噬,先後消滅;次第興亡,輪迴不已,無數群眾,本為弱者,「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尚書益稷),若得「順帝之則」,亦為幸矣!
龍爭虎鬥是英雄,「英雄造時勢」,莽新、曹魏皆為英雄所造溷亂之世,群眾之命運,被英雄捲入時勢之中,隨波逐流,而不能自主。清末以來英雄輩出,鬥法逞強,勇於內鬨,紛歧錯雜,無奇不有。風動草偃,庶人雖多,只有服從。你強我勝,此起彼落,造成空前之浩劫,陷人民於泥犁之中,仍須頌邦家之進步,時代之偉大。
我生不辰,加上命途多舛,七十餘年以來,屢經劇變,在憂患困迫之中,世間不幸之事皆落於我身,自服命運艱苦,故人皆求福,己獨茍活,順乎自然,聽造物之安排而已。往事雲煙,歷歷如昨,獨坐沉寂,一幕一幕,湧上心頭,乃援筆錄之。災劫餘生,辛酸滿腹,命當如此,無所怨尤,乃將此非常時代、身世之遭遇、及時事之見聞,據實述出,無褒貶之權,無虛構之事;楚蕘凡夫胸襟狹隘,粗率之談,有識者見之,笑為「齊東野人之語」而已。
陶唐盛治之世,帝堯欲知民間對政府之感應,乃微服遊於康衢,聞民謠云「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列子仲尼篇)。帝堯是君主,在現代民主風尚之中,一般人最好訶斥專制帝王,故對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更認為是愚民政策,使人民無知無識,只順從法令,甘作奴隸而已;不相信唐虞盛治之文獻,目的在乎推翻歷史,打倒中國文化,此種反常之病,成為時代流行之症,神醫亦不能使之接受藥石。
世道之治亂,非泛泛之群眾所能造端;流芳百世,遺臭萬年,皆非凡人所能為。禹、湯、文、武、漢祖、唐宗,治國平天下之聖哲,當然為「非常」之人;赤眉、銅馬、黃巾、黃巢,能造反作亂,荼毒萬民,亦為非凡人物。「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大學、孟子告子篇)。李、唐趙、宋,得群眾之擁護而統一天下;李自成、張獻忠亦得群眾之擁護而禍害天下;一治一亂,皆賴群眾之力量,然主動均不在群眾,而在傑出之非凡人物,群眾永不能作主,永須受領導,作為「順帝之則」之服從者。蚩蚩之氓,碌碌之輩,當隆治之世,則一倡百和,歌頌昇平;當板蕩之秋,則盲從強霸,滋長亂端。亂紛紛蜂唼蜜,密匝匝蟻排兵,鬧攘攘蠅爭血,造成陰霾充塞之恐怖世界,良莠混合,玉石俱焚,強梁者亦互相吞噬,先後消滅;次第興亡,輪迴不已,無數群眾,本為弱者,「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尚書益稷),若得「順帝之則」,亦為幸矣!
龍爭虎鬥是英雄,「英雄造時勢」,莽新、曹魏皆為英雄所造溷亂之世,群眾之命運,被英雄捲入時勢之中,隨波逐流,而不能自主。清末以來英雄輩出,鬥法逞強,勇於內鬨,紛歧錯雜,無奇不有。風動草偃,庶人雖多,只有服從。你強我勝,此起彼落,造成空前之浩劫,陷人民於泥犁之中,仍須頌邦家之進步,時代之偉大。
我生不辰,加上命途多舛,七十餘年以來,屢經劇變,在憂患困迫之中,世間不幸之事皆落於我身,自服命運艱苦,故人皆求福,己獨茍活,順乎自然,聽造物之安排而已。往事雲煙,歷歷如昨,獨坐沉寂,一幕一幕,湧上心頭,乃援筆錄之。災劫餘生,辛酸滿腹,命當如此,無所怨尤,乃將此非常時代、身世之遭遇、及時事之見聞,據實述出,無褒貶之權,無虛構之事;楚蕘凡夫胸襟狹隘,粗率之談,有識者見之,笑為「齊東野人之語」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