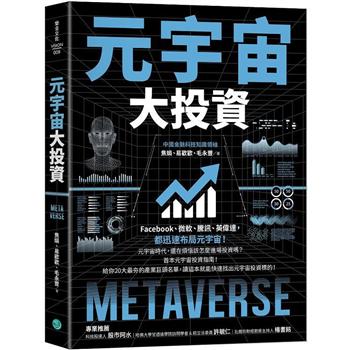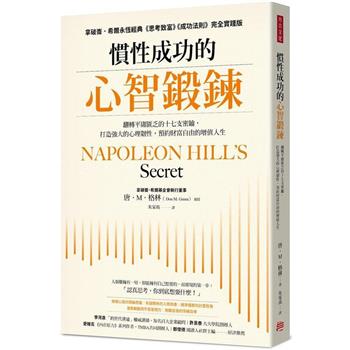才子加流氓──魯迅
你是歌德,但你是社會主義時代新中國的歌德。──周揚
你是歌德,但你是社會主義時代新中國的歌德。──周揚
郭沫若是二十世紀中國大陸著名詩人、劇作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他涉及多個領域,對中國現代文學有偌大影響。儘管他一生備受爭議,甚至有些人將他批為 近代中國文人「四大不要臉」之首。與之立場對立的魯迅也曾評判他是「才子加流氓」,但郭沫若在這動盪不明的時代仍炙熱地燃燒他滿腔的才華,在文學史中為自 己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地位。
本書以郭沫若的生平為線索,著重敘述了傳主的生平和感情世界的發展過程,並就時代環境對郭沫若的人格和文學創作、學術研究的影響做了線條鮮明的勾勒。
本書特色
1.此為秀威文哲叢書,韓晗老師主編。
2.郭沫若身為毛澤東欽點的第一文膽,對文學貢獻許多,然而一生卻備受爭議,拿著筆與槍在政治與文壇中遊走。因其身分的雙重,因此既是文學研究者研究的對象,同時也是民國政治研究者選讀的一環。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