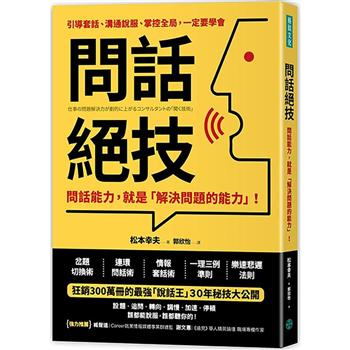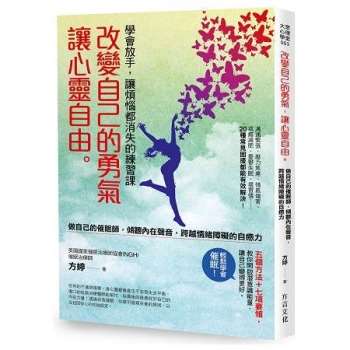五月後半月,有一天傍晚,一位中年男子正從沙斯頓朝著馬洛特村,往家裡走去。那馬洛特村,就座落在與沙斯頓毗鄰的布萊克穆爾谷,也叫布萊克摩谷。這男子走起路來,兩條腿蹣蹣跚跚,步履有些偏斜,身子不是直線向前,而總是有點歪向左邊。他偶爾用勁地點點頭,彷彿是對什麼意見表示首肯,儘管他不在考慮什麼特別的事。他胳膊上挎著一個雞蛋籃子,帽子的絨毛亂蓬蓬的,帽檐上摘帽時大姆指觸摸的地方,還給磨掉了一塊。過了不久,他遇見一個上了年紀的牧師,騎著一匹灰色騾馬,信口哼著小調,朝他迎面走來。
「晚安,」挎籃子的男子說。
「晚安,約翰爵士,」牧師說。
步行的男子走了一兩步,便停住了腳,轉過身來。
「哦,先生,對不起。上回趕集那天,咱倆差不多也是這個時候,在這條路上碰見的,我說了一聲,『晚安』,你也像剛才一樣,回應說:『晚安,約翰爵士。』」
「我是這麼說的,」牧師說。
「在那以前還有過一回―—大約一個月以前。」
「也許有過。」
「我杰克‧德貝菲爾只是個平民小販,你為什麼一次次地叫我,『約翰爵士』」
牧師拍馬走近了一兩步。
「這只是我一時心血來潮,」他說。接著,遲疑了一下,我說:「那是因為,不久以前,我為編寫新郡志而考查各家家譜時,發現了一件事。我是斯丹福特路的特林厄姆牧師,考古學家。難道你真不知道,你是德伯維爾爵士世家的直系後代嗎?德伯維爾家的始姐是佩根‧德伯維爾爵士,據《紀功寺錄》記載,那位赫赫有名的爵士,是隨同征服者威廉一世從諾曼第來到英國的。」
「我以前從沒聽說過呀,先生!」
「唔―—這可是真事――不過,有點不那麼威武了。當年,在諾曼第協助埃斯特雷瑪維拉勛爵征服格拉摩根郡的,有十二位武士,你的祖宗便是其中的一個。你們家的支族,在英國這一帶到處都有莊園。在斯蒂芬王朝,他們的名字都出現在《卷筒卷宗》上。在約翰王朝,你有一位祖宗闊得不得了,把一座莊園捐給了僧侶騎士團;愛德華二世執政時,你的祖宗布頓恩被召到威斯敏斯特,出席了那裡的大議會。在奧利佛‧克倫威爾時代,你們家有點衰落,但不是很嚴重。查理二世在位時,你們家因為忠於君主,被封為『御橡』爵士。哦,你們家有過好多代約翰爵士了。假使爵士也從男爵那樣,可以世襲的話,那你現在就是約翰爵士了。其實,在古時候,爵士封號就是父子相傳的。」
「真有這事!」
「總而言之,」牧師果斷地拿鞭子拍了拍自己的腿,斷定地說,「在英國,簡直找不出第二個這樣的家族!」
「還真找不出呀!」德貝菲爾說道。「可是你看我,一年年地東跑西顛,到處碰壁,好像我只不過是教區裡最低下的人……特林厄姆牧師,關於我這消息,大伙都知道多久啦?」
牧師解釋說,據他所知,這事早已被世人遺忘,很難說有什麼人知道。他自己的考查,是從那年春上的一天開始的。當時,他在考查德伯維爾家族的盛衰榮辱時,恰巧看見他的馬車上寫著德貝菲爾這個姓氏,便追根究柢,查尋了他父親和他祖父的情況,直至把事情搞得確鑿無疑。
「起先,我並不想把這樣一條毫無價值的消息告訴你,攪得你心神不安,」他說。「不過,人有時候太容易衝動,難免失去理智。我還以為你對這事早就有所了解了呢!」
「的確,我有一兩次聽人說,我家沒搬到布萊克穆爾以前,倒過過好日子。可我當時就沒理會那話,只當是說我們家從前養過兩匹馬,眼下只養得起一匹。我家裡有一把古銀匙,還有一方古圖章。不過,銀匙和圖章算得了什麼?……真想不到,我和高貴的德伯維爾家一直是一家骨肉。據說我老爺有些秘密事兒,他卻不肯說出他是打從哪兒來的……牧師,我想冒昧地問一句,我家人如今都在哪兒起爐灶?我是說,我們德伯維爾家都住在哪兒?」
「你們家哪兒也沒有人了。你們作為一郡的世家,已經絕嗣了。」
「真倒楣。」
「是啊――那些胡編瞎扯的家譜上所說的男系絕嗣無後――其實就是衰敗,沒落。」
「那我們家人埋在哪兒?」
「埋在綠山下的金斯比爾。一排又一排地躺在墓穴裡,帶有波倍克大理石華蓋的墓碑上,刻著他們的雕像。」
「我們家的宅邸莊園在哪兒?」
「你們沒有宅邸莊園了。」
「哦?也沒有田地了嗎?」
「沒有,儘管我才說過,你們家以前支系繁茂,擁有大量領地。從前在本郡,你們家的邸宅,金斯比爾有一處,謝爾頓有一處,米爾龐德有一處,拉爾斯丹特有一處,韋爾布里奇有一處。」
「我們家還會興旺起來嗎?」
「呵―—這我可說不準!」
「那我對這事該怎麼辦呢,先生?」德貝菲爾頓了頓,問道。
「哦―—沒有辦法,沒有辦法,除了用「英雄豪傑何竟滅亡」的思想訓誡自己之外,別無辦法。這件事,只有當地的歷史學家和系譜學家會有點興趣,沒有其他意義。在本郡的一些村舍裡,也有好幾家人,以前差不多和你們家一樣榮耀。再見。」
「不過,特林厄姆牧師,你告訴了我這消息,你還是回來跟我去喝它一夸啤酒吧?醇瀝酒店有上好的散裝啤酒―—雖說比起羅利弗酒店來,當然還差一點。」
「不,謝謝―—今晚不行啦,德貝菲爾。你已經喝得夠多了。」說罷,牧師便騎著馬繼續趕路,心裡在嘀咕:他把這條奇聞說出去,是否有失謹慎。
牧師去了以後,德貝菲爾如迷夢般地走了幾步,接著在路邊的草坡地坐了下來,把籃子放在面前。過了一會兒,遠處出現了一個小伙子,也朝著德貝菲爾剛才所走的方向走來。德貝菲爾一看見他,就舉起手來,小伙子便加快腳步,走上前來。
「小子―—拎起這個籃子!我要你給我跑趟腿。」
那個瘦長的小伙子皺了皺眉頭。「約翰‧德貝菲爾,你算老幾?倒支使起我來,還叫我『小子』?咱倆誰不知道誰的名字呀!」
「你真知道,真知道呀!這可是秘密―—這可是秘密啊!現在聽我吩咐,我叫你去送個信,快去送吧……好吧,弗雷德,我還是把秘密告訴你:我出身於遺族人家―—這是我今兒個午後剛發現的。」德貝菲爾宣佈這一消息時,本來是坐著的,卻把身子往後一仰,舒展地躺倒在草坡上的雛菊叢中。
小伙子站在德貝菲爾面前,把他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
「約翰‧德伯維爾爵士―—這就是我,」躺在地上的人接著說道。「就是說,要是爵士跟從男爵一樣的話―—本來就是一樣嘛。我的來歷都上了歷史了。小伙子,你知不知道綠山下的金斯比爾那地方?」
「知道。我去那兒趕過綠山會。」
「唔,在那個城――我是說那地方不是個城。至少我去那兒的時候,還不是個城――那是個不起眼的、可憐巴巴的小地方――」
「別去管那個啥地方,小子―—那不是我們要談的問題。在那個教區的教堂下面,安葬著我的祖宗們――有好幾百位呢――穿著鎧甲,戴著珠寶,裝在好幾噸重的鉛製大棺材裡。在南威塞克斯郡,誰家的祖墳也沒有咱家來得氣派,來得高貴。」
「哦?」
「現在,拎起這個籃子,跑到馬洛特,路過醇瀝酒店時,叫他們趕緊派輛馬車來接我。往車廂裡擺一點酒,裝在小瓶裡,記在我帳上。辦完這樁事以後,你再把籃子拎到我家,告訴我老婆別再洗衣服了,因為她用不著洗完,叫她等我回家,我有消息告訴她。」
見小伙子狐疑不決地站在那裡,德貝菲爾便把手伸進口袋,從他那一向少得可憐的先令中,掏出一個來。
「這是你的酬勞,小伙子。」
這一來,小伙子對事態的估計,可就起了變化。
「是,約翰爵士。謝謝您老。還有什麼事要我為您效勞嗎,約翰爵士?」
「告訴我家裡人,說我晚飯想吃―—嗯,要是能弄到羊雜碎,就吃炒雜碎;要是弄不到羊雜碎,就吃黑香腸;要是連黑香腸也弄不到,吃油炸豬小腸也行。」
「是約翰爵士。」
小伙子拎起籃子,剛一動身,就聽見從村子那裡傳來銅管樂隊的樂曲聲。
「這是幹啥的?」德貝菲爾問道。「不是為我吧?」
「這是婦女在開遊行會呀,約翰爵士。喏,您家千金還是婦女會的會員呢!」
「沒錯―—我光顧得想大事兒,卻把這事兒忘個精光!好啦,你還是去馬勒特吧,給我要輛好馬車,我興許能坐著車兜一圈,檢閱一下遊行會。」
小伙子走了,德貝菲爾沐浴在夕陽裡,躺在野草和雛菊叢中等候,過了許久,那條路上再沒走過一個人影。在這青山環抱之中,那隱隱約約的管樂聲,是唯一聽到的人間聲音。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唐慧心的圖書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黛絲姑娘
小說描寫了貧苦美麗的女主人公黛絲因年輕無知而失身於富家惡少亞歷克,受盡精神和物質上的煎熬,後來她與牧師的兒子克萊爾戀愛並訂婚,在新婚之夜她把昔日的不幸向丈夫坦白,卻沒能得到原諒,這段告解竟為原本幸福美滿的婚姻蒙上一層陰霾,幾年後,黛絲再次與亞歷克相遇,他不斷糾纏她,這時候她因家境窘迫不得不與仇人同居,不久克萊爾從國外回來,向妻子表示悔恨自己以往的冷酷無情,在這種情況下,黛絲終於在悲憤絕望之中殺死亞歷克,坦然地走上絞架……
作者簡介:
哈代(Thomas Hardy,1840.6.2~1928.1.11),英國作家,本書描寫農村姑娘遭受富人迫害以至毀滅的悲劇,公開地向維多利亞時代虛偽的社會道德挑戰,是19世紀英國文學的一顆明珠,奠定了哈代在英國乃至世界文學的地位,在美麗的黛絲身上人們至始至終看到的是她純潔的本性對逼迫她的惡勢力之苦苦掙扎,作爲一部震撼人心的悲劇傑作,已成為世界文學寶庫中一顆絢麗的明珠。
章節試閱
五月後半月,有一天傍晚,一位中年男子正從沙斯頓朝著馬洛特村,往家裡走去。那馬洛特村,就座落在與沙斯頓毗鄰的布萊克穆爾谷,也叫布萊克摩谷。這男子走起路來,兩條腿蹣蹣跚跚,步履有些偏斜,身子不是直線向前,而總是有點歪向左邊。他偶爾用勁地點點頭,彷彿是對什麼意見表示首肯,儘管他不在考慮什麼特別的事。他胳膊上挎著一個雞蛋籃子,帽子的絨毛亂蓬蓬的,帽檐上摘帽時大姆指觸摸的地方,還給磨掉了一塊。過了不久,他遇見一個上了年紀的牧師,騎著一匹灰色騾馬,信口哼著小調,朝他迎面走來。
「晚安,」挎籃子的男子說。
「...
「晚安,」挎籃子的男子說。
「...
顯示全部內容
|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