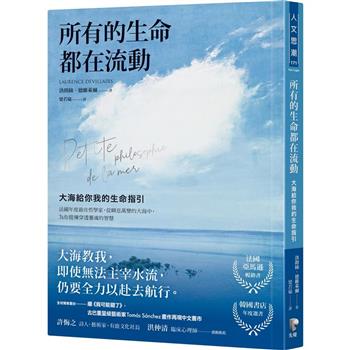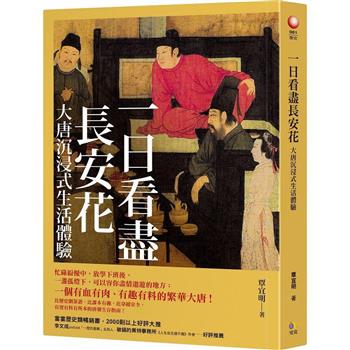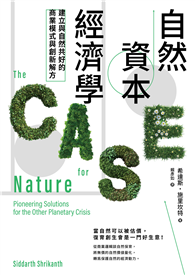對“物”的關注和研究是民族學和人類學的經典傳統之一。縱觀青藏高原人類文明的發展史,藏香不僅有“禮物之靈”,而且也似流動的橋樑和古道,把青藏高原和周邊的文明聯結在一起。
《藏香社會生命史的人類學研究》採用多點田野民族誌的研究方式,以西藏地區三大藏香製作主體——拉薩尼木縣吞巴鄉、山南紮囊縣敏珠林寺和拉薩甘露藏藥廠為主要田野點,以時間和空間為兩個研究維度,既講述了藏香所經歷的從聖物到貢品再到商品的角色變化的社會生命史,也闡述了藏香在空間流動中的“聚”(產生)與“散”(從地方性產物變為具有全球流通趨勢的商品),還分析了國家、市場、社會等多方力量的牽連與交織,如何共同塑造了現如今的藏香文化,讓藏香變成為藏民族重要的文化符號。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喬小河的圖書 |
 |
$ 408 電子書 | 藏香社會生命史的人類學研究 (電子書)
作者:喬小河 出版社:九州 出版日期:2019-06-01 語言:簡體中文 規格:普通級  看圖書介紹 看圖書介紹
|
|
|
內容簡介
目錄
導論
第一章 尋香之旅:田野點地理與社會文化背景
第二章 藏香社會生命的嬗變歷程
第三章 市場的力量:藏香的商品化與市場化
第四章 國家在場:藏香的去商品化與再商品化
第五章 從傳統到現代:藏香文化的堅守與變化
第六章 宗教神聖性的重塑與強化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序
講故事是一種古老的敘述方式。在《天真的人類學家》巴利博士的口中,多瓦悠人有著“不吃午飯,光喝小米啤酒都能爛醉不已”的可愛模樣,有著“生活太過悠閒、所以對禮節格外較真”的嚴肅態度,也有著一切事情都可以用“它是好的”來繞圈圈解釋的簡單性格。他們相信輪回,對自己母語評價不高,認為雞蛋惡心,沒有視覺藝術的歷史,甚至身份證上共用一個人的照片都無法被辨別。在巴利博士的故事里,多瓦悠人“天真”到善於玩“捉迷藏”,提供的信息也不時顛三倒四。他遷就、尊重多瓦悠人的“天真”,但也最終意識到,能夠直接從原住民口中得到的信息實在太過有限且模糊,這些因素似乎共同塑造了人類學的迷人之處——不確定、又頗有幾分天真。因此,好的故事以及好的“說書人”,似乎也可以讓更多的人了解人類學甚至喜歡上這門學科。
對“物”的關注和研究是民族學和人類學的經典傳統之一。無論是將“物”的演變與社會的“進化”並置,還是對“物”的社會化交換、流通與社會關系網絡的研究,抑或是將“物”作為人類社會的遺留和遺存來研究文化形態與物質環境的種種關系,“物”的表現形態與意義內涵遠遠比其自然屬性更為豐富、覆雜與飽滿。縱觀青藏高原人類文明的發展史,藏香不僅有“禮物之靈”,而且也似流動的“橋梁”和“古道”,把青藏高原和周邊的文明聯結在一起。
《藏香社會生命史的人類學研究》講述的是藏香的故事。在作者喬小河博士的眼中,藏香是有“生命”的,這種生命感,既來自生動的民間故事中有關藏香誕生時的神秘色彩,更來自藏香與藏民族生活的融合與嵌入。在一千三百多年歷史演進時所發生的角色變化和空間流動中,藏香就像是藏族的朋友一樣,在人生的諸多儀式、場合和禮俗中“如影隨從”,也與人們保持著一種“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默契和距離,總在那里,但不遠不近。社會生命史的研究視角,構成了本書的寫作基礎,藏香的故事也因為其特別的生命感而慢慢鋪陳開來。
但《藏香社會生命史的人類學研究》並不囿於藏香本身,而是以時間和空間為兩個研究維度,作者既看到了藏香所經歷的聖物、貢品和商品的角色變化,也看到了藏香空間流動中的“聚”與“散”。從故事中抽離出來,作者又以一種客觀、理性的視角,分析了國家、市場、社會等多方力量的牽連與交織,及它們如何共同塑造了現如今的藏香文化,讓藏香變成為藏民族重要的文化符號。其分析和闡述的過程,是一個循序漸進、抽絲剝繭“講道理”的過程,作者在其中很自然地融合了“講故事”與“講道理”這兩部分內容。
把故事講好,要有紮實的田野工作。自2009年進入中央民族大學學習以來,作者多次到甘肅、青海、西藏等地調研,足跡遍及當地的農村、牧區、寺院和企業,而且還孤身一人遠赴尼泊爾,做了大量、細致的訪談和問卷調查,也進行了長時間的參與觀察。在這樣的田野經歷中,作者搜集到了許多有意思的故事。“聽到好故事”自然也成為“講好故事”的重要前提。把道理講明白,要有充足的理論積累,還要有埃文斯-普里查德式“他者的眼光”,要在“走進去”和“走出來”的田野程式中,完成參與者和研究者角色的轉變,實現感性認知與理性思維的切換。通過運用嵌合理論與宗教世俗化理論,解釋藏香社會生命歷程的變化,將藏香的變化置於歷史淵源、時代背景和社會文化之中,力求呈現出一部有滋有味、有理有據的“物”的民族志。這本有關藏香的故事,從學術的視角出發,帶領讀者逐層揭開藏香文化和藏族社會的“面紗”。
在十年的學習和研究中,喬小河博士對藏族社會文化始終充滿溫情與敬意,她眼中的青藏高原日光傾城,她筆下的藏族文化精彩紛呈,她心中的學術樂園自由恬靜。她很少描摹田野經歷的曲折,也沒有刻意渲染撰寫文章的辛苦,但如果《藏香社會生命史的人類學研究》可以讓讀者嗅到一絲藏香的芬芳,從而聞“香”識西藏,探尋到藏族文化更深層的魅力,那麽就可以說,作者是位合格的“說書人”了。
喬小河博士跟我學習民族學和藏學先後有十年的時間,她自己以及和同門前後到西藏進行田野調查大概有六次之多,《藏香社會生命史的人類學研究》就是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撰寫而成。書稿付梓之前,她請我寫個序言,我琢磨了很長時間,千言萬語,竟不知從何說起,以至一拖再拖。對宇宙萬物而言,十年時光就是彈指一揮間,但對短暫的人生來說,十年時光可謂寶貴至極。《藏香社會生命史的人類學研究》的出版也可說是喬小河博士對自己十年民大情結的一份獻禮和一個總結。
蘇發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