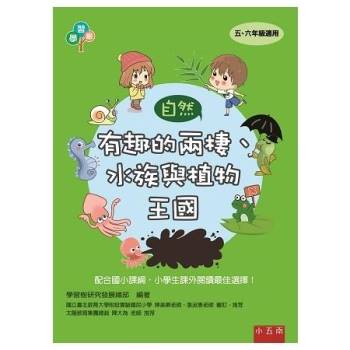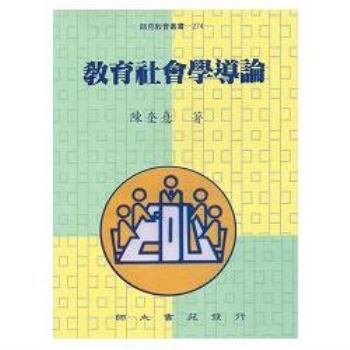在過去20年裡,創傷一直是依戀研究者關注的中心問題。典型的依戀創傷包括童年虐待—辱駡和忽視,這可能對成長帶來長期的不利影響。對於治療師和來訪者而言,全方位瞭解依戀關係中的創傷至關重要。本書作者喬恩·G.艾倫教授認為理解是創傷治療的核心,在依戀創傷治療中發展心智化可以幫助治療師理解來訪者的經歷,讓來訪者感到被理解,並學會在一段信任的關係中重建心理和情感聯結,這可以為經受痛苦體驗的來訪者提供安全感和安定感,從而使其建立受益一生的安全依戀關係。
為了豐富治療師和來訪者對依戀關係中創傷的理解,喬恩·G.艾倫教授在本書中對依戀和心智化進行了全面闡述,指出心智化是理解依戀關係發展的支點,提高心智化能力可以有效改善依戀安全和情感調節。他總結了一系列與創傷有關的精神疾病,說明心智化治療這種獨特的治療方式是如何應用於治療依戀創傷的。此外,他還加入了神經生物學內容,指出依戀、正念和心智化之間的聯繫,幫助讀者理解依戀創傷的生理基礎,從而加深對自己和他人的理解。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喬恩·G.艾倫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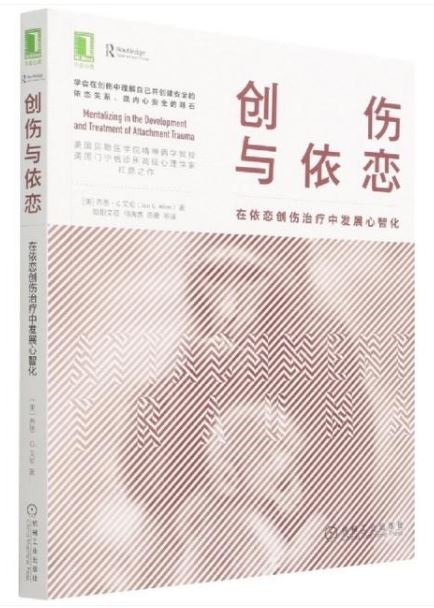 |
$ 421 | 創傷與依戀:在依戀創傷治療中發展心智化
作者:(美)喬恩·G.艾倫 / 譯者:歐陽艾蒞等 出版社:機械工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02-01 語言:簡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00頁 / 16k/ 19 x 26 x 1.5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1-1  看圖書介紹 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創傷與依戀:在依戀創傷治療中發展心智化
內容簡介
目錄
第1章早期依戀 ┆ 5
人格發展的兩條主線 ┆ 7
依戀理論和研究的早期發展 ┆ 8
基本概念 ┆ 15
依戀的發展 ┆ 25
安全依戀 ┆ 29
矛盾-對抗型依戀 ┆ 33
回避型依戀 ┆ 36
兒童氣質 ┆ 39
依戀安全性的穩定性和變化性 ┆ 47
依戀安全性和適應 ┆ 50
臨床意義 ┆ 56
第2章成人依戀 ┆ 57
戀愛關係中的依戀 ┆ 58
安全依戀 ┆ 66
矛盾型依戀 ┆ 73
回避型依戀 ┆ 79
伴侶匹配 ┆ 84
依戀安全性的穩定性和變化性 ┆ 86
依戀安全性的代際傳遞 ┆ 87
依戀原型:條件和限制 ┆ 97
臨床意義 ┆ 99
第3章在頭腦中抱持想法 ┆ 103
正念 ┆ 105
依戀關係中的心智化 ┆ 123
整合正念和心智化 ┆ 141
臨床意義 ┆ 147
第4章依戀創傷 ┆ 150
早期紊亂型依戀 ┆ 152
依戀創傷的代際傳遞 ┆ 161
紊亂型依戀的發展性影響 ┆ 170
兒童依戀創傷的種類 ┆ 178
成年依戀創傷 ┆ 189
臨床意義 ┆ 192
第5章神經生物學基礎 ┆ 194
依戀 ┆ 194
正念 ┆ 212
心智化 ┆ 215
有意識調節與前額葉皮層 ┆ 220
臨床意義 ┆ 229
第6章治療 ┆ 231
我們在治療什麼 ┆ 232
現有的創傷治療 ┆ 241
對心理治療中的依戀的研究 ┆ 246
心智化作為一種獨特的心理治療方式 ┆ 248
心智化創傷體驗 ┆ 256
總結性思考 ┆ 262
參考文獻 ┆ 264
人格發展的兩條主線 ┆ 7
依戀理論和研究的早期發展 ┆ 8
基本概念 ┆ 15
依戀的發展 ┆ 25
安全依戀 ┆ 29
矛盾-對抗型依戀 ┆ 33
回避型依戀 ┆ 36
兒童氣質 ┆ 39
依戀安全性的穩定性和變化性 ┆ 47
依戀安全性和適應 ┆ 50
臨床意義 ┆ 56
第2章成人依戀 ┆ 57
戀愛關係中的依戀 ┆ 58
安全依戀 ┆ 66
矛盾型依戀 ┆ 73
回避型依戀 ┆ 79
伴侶匹配 ┆ 84
依戀安全性的穩定性和變化性 ┆ 86
依戀安全性的代際傳遞 ┆ 87
依戀原型:條件和限制 ┆ 97
臨床意義 ┆ 99
第3章在頭腦中抱持想法 ┆ 103
正念 ┆ 105
依戀關係中的心智化 ┆ 123
整合正念和心智化 ┆ 141
臨床意義 ┆ 147
第4章依戀創傷 ┆ 150
早期紊亂型依戀 ┆ 152
依戀創傷的代際傳遞 ┆ 161
紊亂型依戀的發展性影響 ┆ 170
兒童依戀創傷的種類 ┆ 178
成年依戀創傷 ┆ 189
臨床意義 ┆ 192
第5章神經生物學基礎 ┆ 194
依戀 ┆ 194
正念 ┆ 212
心智化 ┆ 215
有意識調節與前額葉皮層 ┆ 220
臨床意義 ┆ 229
第6章治療 ┆ 231
我們在治療什麼 ┆ 232
現有的創傷治療 ┆ 241
對心理治療中的依戀的研究 ┆ 246
心智化作為一種獨特的心理治療方式 ┆ 248
心智化創傷體驗 ┆ 256
總結性思考 ┆ 262
參考文獻 ┆ 264
序
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期,我有幸及閘寧格診所的一群同事共同開發針對創傷的住院治療方案,我們稱之為創傷康復項目。這個專案的研究物件都有著複雜的慢性精神疾病,他們的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是早期的依戀關係創傷造成的。我組建了一個心理教育團體,它是這個項目的核心組成部分,後來也有一些工作人員和實習生加入進來。我們以一種類似研討會的形式和患者每週見兩次面。
我在教授患者的同時,也和他們一起討論,集思廣益。我意外地發現對患者進行心理教育是最好的治療途徑。在很多同事的熱情帶動下,這個創傷康復項目在整個醫院傳播開來,不僅被用於所有成年人住院治療項目,也被用於青少年治療專案以及部分住院(partialhospital)和門診項目,這令我感到十分欣慰。我們都在一起學習,我也在學習怎麼樣更好地教授。我在著手準備這個項目的時候,意外地發現了依戀理論。在此前的教育和培訓中,我沒有接觸過鮑爾比的任何著作,直到有一天偶然翻到一本言簡意賅的小書《安全基地》(ASecureBase)。那時,我正和一位有嚴重解離性障礙的患者一起工作,感到非常棘手,因為我所學的任何理論都無法精准地描述她的問題,而依戀理論卻能幫助我理解,我一下就被這個理論吸引住了。因此,我將依戀理論作為我撰寫的第一本書《應對創傷》(CopingwithTrauma)的理論基礎。隨著我對創傷的研究逐步深入,幸運之神再次眷顧我。
在我的第一本書出版的時候,彼得·福納吉(PeterFonagy)受邀加盟門寧格診所,以發展精神病理學為中心重構我們的研究專案。多年間,在和彼得及其同事合作的過程中,我掌握了更多關於依戀理論的知識。在此過程中,我被彼得的主要研究領域——心智化(指人理解和解讀行為與心理狀態的關聯的能力)所吸引。心智化是如何在依戀關係中形成的?這一形成過程是如何在依戀關係裡走向異常的?還有什麼比徹底搞清楚這兩個問題更有趣、對臨床工作者更重要呢?隨著對這一理論的領會逐漸深入,我發現心智化的異常發展是依戀創傷的癥結所在。在此前的幾本書裡,我一直引用依戀理論和心智化理論,以此作為理解創傷和相關障礙的基礎。在彼得的鼓勵下,我寫了整本關於這一基礎的書,並加入了一章關於臨床治療的內容。我有一種強烈的渴望(也許是自我中心意識):我渴望解釋清楚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瞭解的關於依戀的知識,其中包括對心智化的全面理解。
這本書的目標讀者不局限於專業人士,我發現患者也很熱衷於學習有關依戀的理論和研究,他們可以很快領會這些知識與他們自己問題的關聯,正如我一開始閱讀鮑爾比的著作時那樣。相應地,為了使好奇的非專業讀者也能理解本書的內容,我用聊天的口吻來撰寫這本書,這也符合我的臨床教育背景。如果沒有門寧格診所提供的幫助,我就無法完成本書。門寧格診所為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讓我可以將臨床工作和學術活動有效結合起來。在診所進行的治療都是長程的住院和門診治療,長程治療的設置對於實施這項雄心勃勃的全面教育專案來說,意義重大。這一教育項目讓我得以發展出一套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話語體系,現在“心智化”也被納入其中。在過去的幾年裡,隨著臨床實踐模式的改變,我的工作開始聚焦於歷時幾周的集中性住院治療——時長長於美國醫院慣常採用的幾天住院時間。我們也不再開設細分的治療項目,整個診所都致力於治療創傷。本書引用了一些過去十年間臨床實踐模式改變後的臨床案例,為了保護患者的隱私,我隱去了關鍵資訊,將不同患者的臨床表現融合在一起。非常感謝我們的前辦公室主任——迪克·慕尼克(DickMunich)。在診所從美國堪薩斯州托皮卡遷移到德克薩斯州休士頓以與貝勒醫學院建立合作關係之際,是他鼓勵我一起到休士頓工作。
他為我提供了一個職位,使我得以繼續致力於寫作。我也非常感謝現任辦公室主任約翰·奧爾德姆(JohnO1dham),還有伊恩?艾特肯(IanAitken)、休?哈德斯蒂(SueHardesty)、湯姆·艾理斯(TomEllis),他們在行政方面的支持給了我繼續寫作的空間,這些支持至關重要。我還要感謝一些讀了這本書並給出修改意見的同事:克裡斯·福勒(ChrisFowler)、湯姆·艾理斯、約翰·哈特(JohnHart)、裡茲·紐林(LizNewlin)、拉米羅·薩拉斯(RamiroSalas)、萊恩·斯特拉森(LaneStrathearn)、羅傑·弗登(RogerVerdon)。感謝史蒂夫·赫雷拉(SteveHerrera)在文獻方面給我提供的幫助。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妻子蘇珊(Susan),是她在我全神貫注地寫作時給了我極大的包容和支持。她也閱讀了整本書的手稿,使得這本書更加通俗易懂。
我在教授患者的同時,也和他們一起討論,集思廣益。我意外地發現對患者進行心理教育是最好的治療途徑。在很多同事的熱情帶動下,這個創傷康復項目在整個醫院傳播開來,不僅被用於所有成年人住院治療項目,也被用於青少年治療專案以及部分住院(partialhospital)和門診項目,這令我感到十分欣慰。我們都在一起學習,我也在學習怎麼樣更好地教授。我在著手準備這個項目的時候,意外地發現了依戀理論。在此前的教育和培訓中,我沒有接觸過鮑爾比的任何著作,直到有一天偶然翻到一本言簡意賅的小書《安全基地》(ASecureBase)。那時,我正和一位有嚴重解離性障礙的患者一起工作,感到非常棘手,因為我所學的任何理論都無法精准地描述她的問題,而依戀理論卻能幫助我理解,我一下就被這個理論吸引住了。因此,我將依戀理論作為我撰寫的第一本書《應對創傷》(CopingwithTrauma)的理論基礎。隨著我對創傷的研究逐步深入,幸運之神再次眷顧我。
在我的第一本書出版的時候,彼得·福納吉(PeterFonagy)受邀加盟門寧格診所,以發展精神病理學為中心重構我們的研究專案。多年間,在和彼得及其同事合作的過程中,我掌握了更多關於依戀理論的知識。在此過程中,我被彼得的主要研究領域——心智化(指人理解和解讀行為與心理狀態的關聯的能力)所吸引。心智化是如何在依戀關係中形成的?這一形成過程是如何在依戀關係裡走向異常的?還有什麼比徹底搞清楚這兩個問題更有趣、對臨床工作者更重要呢?隨著對這一理論的領會逐漸深入,我發現心智化的異常發展是依戀創傷的癥結所在。在此前的幾本書裡,我一直引用依戀理論和心智化理論,以此作為理解創傷和相關障礙的基礎。在彼得的鼓勵下,我寫了整本關於這一基礎的書,並加入了一章關於臨床治療的內容。我有一種強烈的渴望(也許是自我中心意識):我渴望解釋清楚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瞭解的關於依戀的知識,其中包括對心智化的全面理解。
這本書的目標讀者不局限於專業人士,我發現患者也很熱衷於學習有關依戀的理論和研究,他們可以很快領會這些知識與他們自己問題的關聯,正如我一開始閱讀鮑爾比的著作時那樣。相應地,為了使好奇的非專業讀者也能理解本書的內容,我用聊天的口吻來撰寫這本書,這也符合我的臨床教育背景。如果沒有門寧格診所提供的幫助,我就無法完成本書。門寧格診所為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讓我可以將臨床工作和學術活動有效結合起來。在診所進行的治療都是長程的住院和門診治療,長程治療的設置對於實施這項雄心勃勃的全面教育專案來說,意義重大。這一教育項目讓我得以發展出一套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話語體系,現在“心智化”也被納入其中。在過去的幾年裡,隨著臨床實踐模式的改變,我的工作開始聚焦於歷時幾周的集中性住院治療——時長長於美國醫院慣常採用的幾天住院時間。我們也不再開設細分的治療項目,整個診所都致力於治療創傷。本書引用了一些過去十年間臨床實踐模式改變後的臨床案例,為了保護患者的隱私,我隱去了關鍵資訊,將不同患者的臨床表現融合在一起。非常感謝我們的前辦公室主任——迪克·慕尼克(DickMunich)。在診所從美國堪薩斯州托皮卡遷移到德克薩斯州休士頓以與貝勒醫學院建立合作關係之際,是他鼓勵我一起到休士頓工作。
他為我提供了一個職位,使我得以繼續致力於寫作。我也非常感謝現任辦公室主任約翰·奧爾德姆(JohnO1dham),還有伊恩?艾特肯(IanAitken)、休?哈德斯蒂(SueHardesty)、湯姆·艾理斯(TomEllis),他們在行政方面的支持給了我繼續寫作的空間,這些支持至關重要。我還要感謝一些讀了這本書並給出修改意見的同事:克裡斯·福勒(ChrisFowler)、湯姆·艾理斯、約翰·哈特(JohnHart)、裡茲·紐林(LizNewlin)、拉米羅·薩拉斯(RamiroSalas)、萊恩·斯特拉森(LaneStrathearn)、羅傑·弗登(RogerVerdon)。感謝史蒂夫·赫雷拉(SteveHerrera)在文獻方面給我提供的幫助。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妻子蘇珊(Susan),是她在我全神貫注地寫作時給了我極大的包容和支持。她也閱讀了整本書的手稿,使得這本書更加通俗易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