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令人激動的經歷」
梅寧哲博士回憶拜訪佛洛伊德的經歷
貝克巷位於維也納一片灰色建築物的汪洋大海中間。春天的第一縷陽光才剛剛將冬天的寒冷驅走,佛洛伊德就又被吸引到了沉浸在維也納森林芬芳中的城市郊區。從五月到九月,他居住在那裡一棟用他的話說「美得像童話一樣」的古老別墅裡。別墅位於高級住宅區格林津,裡面有一個美麗的花園。維也納的這個地區常出現在歌曲裡,這裡著名的是葡萄酒和販售當年新酒的酒館。佛洛伊德一九三四年來到這兒度夏的時候,正值時局「火熱」的一年。二月,奧地利境內上演了一場血腥的內戰,七月,聯邦總理又在國家社會黨人策劃的一場謀殺案中身亡。因祖國的未來而陷入深深悲觀情緒的不僅只有佛洛伊德。
四十一歲的美國精神病科醫生卡爾‧梅寧哲正是在這樣的局勢中乘坐一架螺旋槳式飛機踏上從堪薩斯到奧地利的漫長旅途,他要去拜訪七十八歲高齡的佛洛伊德。到達後的第二天,他乘坐計程車從位於維也納市中心的飯店來到佛洛伊德在格林津的施特拉斯巷裡租住的避暑別墅。開門的是安娜‧佛洛伊德,她先將客人領進一個昏暗的房間,然後,經過一段漫長的等待之後,才把他帶到別墅的花園裡,她的父親坐在一棵大樹的樹蔭下。兩位醫生就在那裡見面了。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出生在一百五十年前,如今已經沒有親眼見過他並能講述類似經歷的人了。我一九八九年春天到美國堪薩斯州首府托皮卡的時候,尚有一位健在。他的名字叫卡爾‧梅寧哲,一九三四年八月去維也納拜訪佛洛伊德的就是他。我見到梅寧哲博士的時候,他已經是九十六歲高齡。這個人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充沛精力和讓人嘆為觀止的工作能力。他一手建立的梅寧哲基金會是全世界最大的私人精神病醫院之一,而且他還是基金會裡非常活躍的主席。我在托皮卡的兩天時間,這位行動敏捷、為人熱情的精神病學專家帶著我參觀了他當時還要每天去工作的五家醫院和學院。
「您是為佛洛伊德而來,」卡爾‧梅寧哲說道,「沒錯,我當年坐飛機去維也納拜訪他,那是一次令人難忘的經歷,或許不是最美好的,但絕對是我曾經歷過最讓人激動的事之一。」作為佛洛伊德傳記的作者,現在見到了一位仍健在的見過佛洛伊德的人,我很快就提出了縈繞在心頭許久的那個問題。這個問題是關於這位或許稱得上是二十世紀最重要人物的個性和他的個人魅力。
「哦,佛洛伊德看上去就是大家想像中的學者的模樣,他是一位典型的維也納紳士。」梅寧哲博士說,「佛洛伊德教授態度友善,彬彬有禮,他很優雅,但是也懂得保持一定的距離,並不是一個握握手就馬上能跟人『熱絡』起來的人。他在當時已經成為傳奇人物,而且他自己也清楚這一點。」
佛洛伊德和梅寧哲在這個陽光燦爛的夏日所進行的是一場深入的交談,絕不是一個世界知名的人跟年紀幾乎可以做他兒子的拜訪者之間空泛的客套。當時的梅寧哲也已經是個名人,他的著作《人的心靈》是美國的暢銷書之一,銷量遠超過佛洛伊德的著作,為精神分析學在美國乃至全世界的推廣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並且他當時已經是梅寧哲醫院的院長,這所醫院是少數運用精神分析法治療病人的精神病醫院之一。
那麼,美國最早從事精神分析學的學者來到維也納朝拜精神分析學之父時,會說些什麼呢?
「我先是向佛洛伊德把青椒雞肉這道菜大大誇獎了一番。我生平第一次吃到這道菜,在一個新酒酒館的花園裡。我們還談到了那裡演奏的音樂。」
「您總不會是為了這個才去維也納的吧?」
「哦,不是,」梅寧哲笑了,「我們說起了『死本能』,你們用德語怎麼說的?哦,對了:Todestrieb。」卡爾‧梅寧哲是佛洛伊德門徒中少數幾個贊同自己偶像這個觀點的人之一,他們認為死亡的胚芽從一開始就存在於人的有機體之中。
談話時,佛洛伊德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雖然帶著濃重的奧地利口音」。儘管重病纏身,他依然全神貫注,對每個質疑,每個不管多麼複雜的問題都一一作答。梅寧哲來拜訪的時候,西格蒙德‧佛洛伊德已經患頷癌十餘年,經常承受著難以忍受的疼痛,並且已經做過數次手術。「但是他有鐵一般的自律性,並沒有流露出一絲一毫的痛苦。」
和卡爾‧梅寧哲談話時,我能感受到那位偉大的老人對他的吸引力。然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次拜訪也是讓人失望的。「您設想一下,我去維也納的時候滿懷期望。畢竟我一直致力於在美國推廣精神分析學,在那個時代,很多人根本不想瞭解這門學說,我在這裡就像是他的學說的一個代理律師,一個傳教士。但是結果呢?我千辛萬苦地從美國來到歐洲,佛洛伊德先是讓我在昏暗的前廳等了整整一個小時後才接見我。這也就罷了,只是在整個談話過程中,我始終有種感覺,佛洛伊德壓根兒沒有因為跟一個美國人共同探討問題而感到特別的高興,別人為他和他的研究所做的一切,他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並不打算提供我們在美國為精神分析學所做的工作任何支援。當然,這並不是因為對我個人的好惡,其根源還在若干年前:一九○九年,佛洛伊德曾經訪問美國,儘管當時受到了熱烈歡迎,但他從那以後還是對這個國家產生了反感。這件事很奇怪,因為在歐洲,人們可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為他設置了重重的阻礙,他的學說反倒是從美國開始傳遍世界的。後來我常常想他究竟討厭我們美國人哪一點。」
佛洛伊德本人解釋為什麼排斥這個對他張開雙臂的新大陸,說是因為長年的消化問題,他認為罪魁禍首是美國的食物。並且在美國的那兩個星期裡,他對美國人不合傳統的行為舉止也不怎麼欣賞。
梅寧哲基金會裡有一座雄偉的梅寧哲檔案館,其中有一個規模在全世界數一數二的精神病學圖書館。因為有梅寧哲博士的明確許可,檔案館允許我看了梅寧哲博士拜訪過佛洛伊德之後與他的通信,在信中,梅寧哲介紹了自己在美國進行精神分析實踐的情況,從維也納寄來的回信就像他講述的那次會面一樣,禮貌而又冷淡。不過回信倒是顯示出反對一切盲目個人崇拜的佛洛伊德的一些典型性格特徵。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他寄往托皮卡的信中寫道:「尊敬的同仁。感謝您親切的來信,以及對您所做工作的詳細介紹。同時感謝您寄來的《臨床醫學》雜誌。您提及要將雜誌第五期題獻給我,我本應為此感到高興,然而我的一個基本原則是,不親自參與這類與個人有密切關係的活動。致崇高的敬意。佛洛伊德。」
「就像他在維也納對我說過的,我們完全依照他的觀點所進行的工作讓他感動。但是他並不打算接受我的請求,不願意為我們的雜誌寫前言。」
留在卡爾‧梅寧哲記憶中的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天才,他為我們描繪的也是這位偉大科學家生活中一幅頗具代表性的畫面:佛洛伊德可以是友善的,而同時又讓人有疏離感。年輕時他對死亡有著強烈的恐懼,而那又正好是他才思泉湧的時期。許多出版商想要出版他的傳記,都被他硬生生地拒絕了,但是比起世界歷史上的大多數偉人,他又給我們留下了更豐富的傳記素材。他離開自己最親密、最忠誠的朋友,忍受著被孤立的痛苦,而這痛苦卻有一部分是他自己造成的。
佛洛伊德本人就是適合佛洛伊德分析的病例,這句話一點都沒錯。正是因為他複雜的個性,也正是這個充滿矛盾的天才,奠定了全面研究人類心靈活動的基礎。就像他自己曾經說過的:「最主要的病人就是我自己。」
留在梅寧哲記憶中的是一個雖然有魅力,卻非常冷淡的佛洛伊德,但是我在維也納看到佛洛伊德以前一個病人的信件,裡面卻描述了一個截然不同的佛洛伊德。這個病人名叫布魯諾‧格茨,一九○二年時曾短期接受過佛洛伊德的治療。當時還在上大學的格茨異常坦誠地詳細描述了一個讓人著迷的、幾乎是有魔力的佛洛伊德。
將滿二十歲的格茨患有嚴重的面部神經痛,他來到貝克巷的時候「心情很複雜」:「佛洛伊德朝我走過來,握了握我的手,讓我坐下,然後仔仔細細地打量我。我看著他的眼睛,他的眼神溫和極了,熱情、憂鬱而又充滿智慧。我當時就覺得像是有一隻手輕拂過我的額頭。」格茨在寫給少年時代一位好友的信中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說一見面,疼痛就「彷彿隨風而去」。醫生的氣質一下子迷住了這位新病人。格茨在閒暇時寫詩,他後來還翻譯過托爾斯泰和果戈理的作品。佛洛伊德先是一言不發地微笑著坐了一會兒,然後和氣地說:「讓我先來認識一下您吧。我這裡有幾首您寫的詩,寫得非常美,但是涵義隱晦。您把自己隱藏在這些詞語的後面,而不是讓它們把您襯托出來。振作起來!您根本沒有必要對自己感到恐懼……現在,請談談您自己吧!您的詩裡不斷出現大海,它有什麼象徵意義嗎?或者您真的跟海有什麼淵源?您是哪裡人呢?」
布魯諾‧格茨是海員的兒子,出生在俄羅斯的港口城市里加。佛洛伊德敏銳的直覺讓他很吃驚。「我覺得心裡就像打開了一扇閘門,不假思索地把自己的一生向他和盤托出,毫無保留,包括那些我從未向任何人說過的事。在他面前隱藏事實有什麼意義呢?反正你不用說他就已經什麼都清楚了。」
「他聽我說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沒有打斷我,也沒有看我。有的時候他會輕輕笑幾聲。」終於,佛洛伊德把話題引向了病人的父親:「您的父親對您是不是很嚴格?」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們心念相通。我只是從沒對他說過跟一個姑娘和一個年紀比較大的女人之間可笑又不幸的愛情,也沒有說過我瘋狂迷戀過幾個水手,迷到恨不得狠狠地把他們親個夠的事。我擔心他可能不會認真看待這些事,會在心裡嘲笑我。他肯定是不會責備我的,我對自己也根本沒有什麼可以責備的─除了我缺乏膽量,還有後來,每次躺在床上……您明白的……」
「當然,當然,」佛洛伊德用低沉的嗓音說,「那,跟水手的事並沒有讓您感到不安嗎?」
「完全沒有!」病人說,「我愛得死去活來。人一旦陷進去了,就覺得什麼都是對的,不是嗎?」
「在您身上當然是!」佛洛伊德說著,突然忍不住大笑起來。「您的心安理得真是讓人羨慕,這要感謝您的父親。那麼您的母親呢?……」
因為佛洛伊德建議病人接受藥物治療,所以他們只見了幾次面。「親愛的格茨同學,」他說,「我不會給您做分析,您並不會因為這些心結感到不幸福。不過對付您的神經痛,我倒是有個適合的藥方。」
佛洛伊德開的藥很快就發揮作用,病人的神經痛不久就消失了。布魯諾‧格茨記住了一個偉大、熱情的佛洛伊德。
不同於作為醫生的梅寧哲博士和作為病人的布魯諾‧格茨,留在西格蒙德‧佛洛伊德外孫記憶中的是一個理想的「外祖父」:埃內斯特‧佛洛伊德是少數幾位還健在的家人之一,他對這位擁有子女六人,「像上帝一樣的家長」依然保留著鮮活的記憶。外祖父去世的時候,埃內斯特‧佛洛伊德二十五歲,他一部分時間住在漢堡,一部分時間住在維也納。埃內斯特依然記得貝克巷的那個維也納大家庭,「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價值觀,雖是猶太家庭,但並非是極端正統派,這是一個體面的知識分子家庭,非常正直、誠實。這個家裡有外祖父,實際上他是一切的中心,還有外祖父的小女兒安娜,她是外祖父的左右手。然後是外祖母,米娜姨婆,身兼管家和女傭兩職的寶拉,還有廚娘。此外還有五位年邁的姑婆(佛洛伊德的妹妹),都是好人,熱情,樂於助人。外祖父非常有人情味,但同時又絕對正確,而且所有的人都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外祖父不用開口說想怎麼樣,事事都井井有條。」
在埃內斯特‧佛洛伊德的記憶中,佛洛伊德「通常都是忙著寫東西、看書或者思考,經常能看到他用一把大的拆信刀裁開還沒有看過的新書書頁。永遠是親切、坦率、誠實。他說話很慢,字斟句酌,他說的那些話總能夠引起別人的思考。我從來沒有見過他情緒失控或者憤怒。家裡永遠是一片祥和寧靜,看不出絲毫緊張的氣氛。大家努力保持意見一致。我不記得有哪個家庭成員大聲嚷嚷,互相叫罵,或是用拳頭砸桌子,氣得跺地板、摔門或者罵人。所有這些都是難以想像的,因為這家人脾氣好,驕傲而又克己。」
讓我們從佛洛伊德的外孫那裡回到托皮卡的梅寧哲博士這裡。他把自己的第二部著作《生之掙扎》寄給佛洛伊德之後,佛洛伊德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四日表示了感謝:「尤其要感謝,因為精神分析學者們並不是很喜歡『死本能』。」這是佛洛伊德寫給梅寧哲的最後一封信,他顯得很高興,因為美國的這位同行再次對他自己非常重視的「死本能」表示了關注。
處於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核心位置的正是人類的這兩種本能:其中一個是毀滅自身或他人存在的「死本能」,另一個是集中在情慾和生殖上的「生本能」(「利比多」)。後者處在每個生命的源頭,就此,我們也順理成章地翻開了佛洛伊德生活的第一頁,他的童年。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喬治.馬庫斯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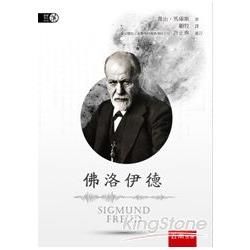 |
$ 202 ~ 304 | 佛洛伊德
作者:喬治.馬庫斯/著,許正典/審訂 (Georg Markus) / 譯者:顧牧 出版社:五南 出版日期:2013-11-25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04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佛洛伊德
佛洛伊德是個什麼樣的人?圍繞著他那張著名的沙發又發生過什麼故事?喬治 • 馬庫斯以生動、幽默的語言,循著佛洛伊德的私人生活與學術研究這兩條線索,將精神分析之父一生中的重要經歷和學術研究的重大發展階段娓娓道來,從艱深的理論與抽象的心理學概念中發掘出一個生動、飽滿的佛洛伊德形象呈現給讀者。在這部傳記中,讀者不僅能了解與精神分析學發展緊密相關的一些著名病例,還能讀到佛洛伊德與愛因斯坦、施尼耶勒、維克多 • 阿德勒和馬勒等著名人物之間的故事。
本書特色:
本書作者以生動、幽默的語言,循著佛洛伊德的私人生活與學術研究這兩條線索,將精神分析之父一生中的重要經歷和學術研究的重大發展階段娓娓道來,讀者不僅能了解與精神分析學發展緊密相關的一些著名病例,還能讀到佛洛伊德與愛因斯坦、施尼耶勒、維克多 ‧ 阿德勒和馬勒等著名人物之間的故事。
作者簡介:
喬治 ‧ 馬庫斯
(Georg Markus, 1951~)
奧地利著名作家,曾任維也納《信使報》編輯,並為該報撰寫專欄「歷史故事」。從上世紀七○年代末開始文學創作,至今已發表作品二十餘部。這些作品的內容多為歷史題材和人物傳記,最新的作品有記述奧地利大家族興衰史的《奧地利家譜》(2010),記錄奧地利不同歷史時期各階層人民生活的《似水流年》(2009),描述歷史人物的《遇見時代見證者》(2008)等。《佛洛伊德》發表於1989年,本書目前已翻譯成法語、西班牙語、俄語、波蘭語和捷克語等多國語言。
章節試閱
「一次令人激動的經歷」
梅寧哲博士回憶拜訪佛洛伊德的經歷
貝克巷位於維也納一片灰色建築物的汪洋大海中間。春天的第一縷陽光才剛剛將冬天的寒冷驅走,佛洛伊德就又被吸引到了沉浸在維也納森林芬芳中的城市郊區。從五月到九月,他居住在那裡一棟用他的話說「美得像童話一樣」的古老別墅裡。別墅位於高級住宅區格林津,裡面有一個美麗的花園。維也納的這個地區常出現在歌曲裡,這裡著名的是葡萄酒和販售當年新酒的酒館。佛洛伊德一九三四年來到這兒度夏的時候,正值時局「火熱」的一年。二月,奧地利境內上演了一場血腥的內戰,七月,聯...
梅寧哲博士回憶拜訪佛洛伊德的經歷
貝克巷位於維也納一片灰色建築物的汪洋大海中間。春天的第一縷陽光才剛剛將冬天的寒冷驅走,佛洛伊德就又被吸引到了沉浸在維也納森林芬芳中的城市郊區。從五月到九月,他居住在那裡一棟用他的話說「美得像童話一樣」的古老別墅裡。別墅位於高級住宅區格林津,裡面有一個美麗的花園。維也納的這個地區常出現在歌曲裡,這裡著名的是葡萄酒和販售當年新酒的酒館。佛洛伊德一九三四年來到這兒度夏的時候,正值時局「火熱」的一年。二月,奧地利境內上演了一場血腥的內戰,七月,聯...
»看全部
作者序
「就像發現新大陸」
斯特凡‧魯達斯的前言
歷史上總有一些發現不斷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和世界觀。西格蒙德‧佛洛伊德關於潛意識對人類生活、經歷和共同生活關鍵性作用的認識無疑就是這樣一個重大發現。
佛洛伊德創立的精神分析學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治療方法和心理學學科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廣泛運用,今天,精神分析學已不僅限於心理社會學,它還滲透進了和人類研究有關的所有研究領域。佛洛伊德對於醫學的影響自然尤為深遠,特別是在解釋精神障礙和疾病的產生及治療方面。他也認為自己首先是一位醫生,從事的是救死扶傷的職業。
和其他很多...
斯特凡‧魯達斯的前言
歷史上總有一些發現不斷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和世界觀。西格蒙德‧佛洛伊德關於潛意識對人類生活、經歷和共同生活關鍵性作用的認識無疑就是這樣一個重大發現。
佛洛伊德創立的精神分析學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治療方法和心理學學科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廣泛運用,今天,精神分析學已不僅限於心理社會學,它還滲透進了和人類研究有關的所有研究領域。佛洛伊德對於醫學的影響自然尤為深遠,特別是在解釋精神障礙和疾病的產生及治療方面。他也認為自己首先是一位醫生,從事的是救死扶傷的職業。
和其他很多...
»看全部
目錄
「就像發現新大陸」
斯特凡‧魯達斯的前言
「一次令人激動的經歷」
梅寧哲博士回憶拜訪佛洛伊德的經歷
「此子難成大器」
童年和少年時期
都是因為歌德─但這不是他的錯
因為一個誤會選擇醫學
「而不是吻你甜蜜的唇」
佛洛伊德戀愛了
「論古柯」
佛洛伊德與古柯鹼事件
將軍是鸚鵡
佛洛伊德、部隊和婚姻
安娜‧O
邁向精神分析
維也納第九區,貝克巷十九號
一個創造了世界歷史的地方
「我不遵從你的戒菸令」
朋友弗利斯和無時不在的死亡恐懼
「最主要的病人,那就是我自己」
沙發
愛瑪
佛洛伊德的...
斯特凡‧魯達斯的前言
「一次令人激動的經歷」
梅寧哲博士回憶拜訪佛洛伊德的經歷
「此子難成大器」
童年和少年時期
都是因為歌德─但這不是他的錯
因為一個誤會選擇醫學
「而不是吻你甜蜜的唇」
佛洛伊德戀愛了
「論古柯」
佛洛伊德與古柯鹼事件
將軍是鸚鵡
佛洛伊德、部隊和婚姻
安娜‧O
邁向精神分析
維也納第九區,貝克巷十九號
一個創造了世界歷史的地方
「我不遵從你的戒菸令」
朋友弗利斯和無時不在的死亡恐懼
「最主要的病人,那就是我自己」
沙發
愛瑪
佛洛伊德的...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喬治 • 馬庫斯/審定者:許正典 譯者: 顧牧
- 出版社: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11-25 ISBN/ISSN:978957117396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04頁
- 類別: 中文書> 傳記> 思想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