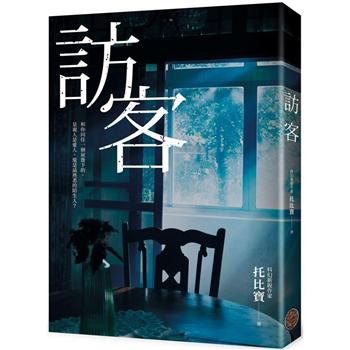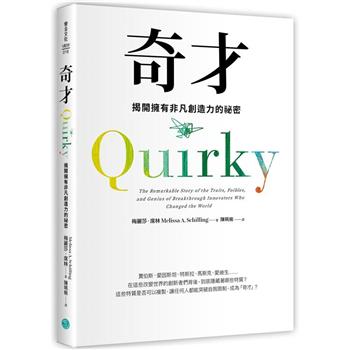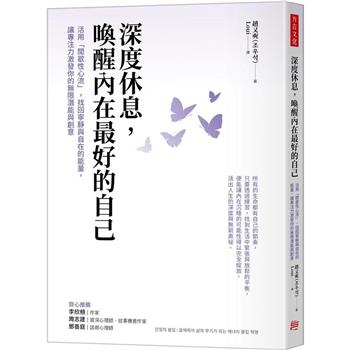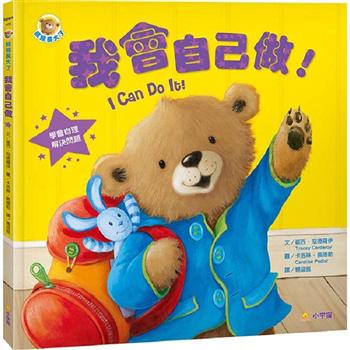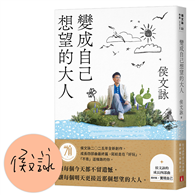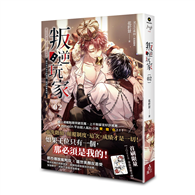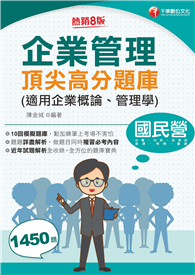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2 項符合
喬納森.沃夫的圖書 |
 |
$ 420 ~ 474 | 人天生就是政治動物:政治哲學緒論 (電子書)
作者:喬納森.沃夫(JonathanWolff) / 譯者:鄭楷立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25-05-13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普通級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420 電子書 | 人天生就是政治動物:政治哲學緒論
作者:喬納森.沃夫,JonathanWolff 出版社:城邦出版集團 出版日期:2025-05-13 語言:中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