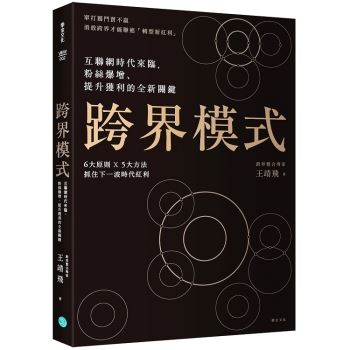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嚴寄鎬的圖書 |
 |
$ 207 ~ 315 | 痛苦可以分享嗎?:不以愛與正義之名消費傷痛,讓創傷者與陪伴者真正互助共好的痛苦社會學
作者:嚴寄鎬 / 譯者:黃子玲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19-10-05 語言:繁體書  共 11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1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本書特色
▍一本細膩探究痛苦形式與核心、深思社會結構與個人心理因素,尋求解決之道的另類療癒之作。
▍作者特別為台灣讀者撰寫繁體中文版序文。
允許悲傷、擁抱脆弱,才能真正地看見痛苦,與痛苦同行。
幫助受傷的人說出生命中無處安放的痛,
讓「我們」一起好起來。
◇◇◇◇◇
從高度階級化的韓國切入,以社會學視角,看見全人類的痛苦。
一本來回爬梳痛苦的養成過程、痛苦在不同階級的展演,以及藉由痛苦所壯大的宗教與網路經濟,
如剝開層層洋蔥,深刻探討「痛苦效應」的驚人之作。
原來,我們過去所理解的「痛苦」,只是表象而已……
生而為人,一定都曾陷入痛苦,
但我的痛苦,無法與你的痛苦劃上等號。
現代社會中,許多人的靈魂都生了病,
當人人皆痛苦的時代來臨,卻無法彼此同理,支持系統也難以建立,
個人該如何才能走出這種強大的情緒監牢?
甚至,藉由述說並分享痛苦的經驗,找回與外界喪失已久的連結?
◇ 因年邁而罹患慢性病,身體劇痛、行動困難,卻無法讓家人理解萬分之一的在熙媽媽
◇ 不僅婚姻貌合神離,丈夫破產後還瞞著自己逃走,徒留鉅額債務的宣雅
◇ 無論如何都無法從喪妻之痛走出、最後一頭栽進了神祕宗教的學者
他們時時自問:
◇ 為什麼遭遇如此不幸的,不是別人,而是我?
◇ 無論我怎麼費力形容,為什麼一說出口,我的痛苦就顯得平庸至極,跟其他人毫無不同?
◇ 別人都說經歷痛苦是有意義的,但如果只是因為沒得選擇,此後也會不斷發生……那麼,意義何在?
活在社會中的每一個人,無論在過去與未來,都懷抱著各自的創傷前行,也都需要著他人。
若人不是孤島,我們就該思考:
◇ 身為受苦者的親友,如何才能正確陪伴?
◇ 無法負荷對方的情緒重擔時,陪伴者如何應對與自救?
◇ 當感到孤立無援時,如何才能暫時擺脫情緒,給自己喘息的空間?
◇ 當「極度痛苦」破壞了個人內在對外在世界的交流管道,如何重新打造溝通橋梁?
當痛苦無法被述說,它就不會消失;它會化為一堵高牆,將個體與他人全然隔絕。然而,痛苦的敘事該如何才能正確形塑?深陷痛苦時,唯有語言才是唯一的解決之道嗎?原本極度個人化的「痛苦」心理,在擴大為集體的心理狀態之後,又反映了哪些社會與階級問題?韓國人權工作者嚴寄鎬以其獨特的社工視角來切入,從集體與個人經驗雙管齊下,為了無數在痛苦情緒中掙扎浮沉的受苦者與陪伴者,提出最深刻的觀察與建言,探討遭逢巨大創傷的人們該如何互相扶持,邁向復原之路。
作者簡介
嚴寄鎬엄기호 지음
1971年生。在國際人權團體工作,透過人權語言來解讀世界各地的痛苦。著有《閉嘴,全球化!》、《誰也別管別人》、《這何嘗不是青春》、《我們活得沒錯》、《教師也害怕學校》等書。
譯者簡介
黃子玲
政大日文系╱韓文系畢,譯有《我每天都想離職》。
聯絡信箱:evior.ling@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