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被紐約NY MOVES雜誌評選為2010年最有影響力的女性
★ 《柯克斯書評》、《書單雜誌》、《出版人週刊》推薦
★ 東海大學社會系 朱元鴻教授推薦
一趟追尋信仰、改變生命的朝聖之旅
一本深度認識伊斯蘭社會的迷人之作一趟「文化衝擊」之旅
無預警的被美國拒絕延長簽證,坎妲.艾哈邁德,一位年輕的英國穆斯林女醫生,即將被流放。一時興起,她接下了沙烏地阿拉伯一個令人興奮的工作。沙烏地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國度,一個她以為她理解的國度,一個她希望找到歸屬感的地方。她以為這不只是一份新工作,更是一個在異國冒險的機會。然而,她卻受到了巨大的文化衝擊。
當一個信仰伊斯蘭教、卻是在英國受西方教育長大成人的女醫師,來到沙烏地阿拉伯王國行醫,這將是怎樣的一趟旅行?是深入伊斯蘭文化的尋根之旅?還是考驗信仰的試煉之路?當現代西方文明,遇上傳統伊斯蘭文化,在巨大的文化衝擊當中,坎妲.艾哈邁德卻發現了埋藏在衝突對立表象之下的溫柔。
作者簡介:
坎妲.艾哈邁德博士(DR. QANTA A. AHMED)的童年在英格蘭度過,她在那裡就讀諾丁漢大學醫學院。之後到紐約受訓,擁有四項專科證照,包含內科、肺部疾病,重症監護醫學,以及睡眠障礙醫學。目前任職於查爾斯頓的南卡羅來納大學醫學院擔任助理醫學教授,她在那裡生活並行醫。
譯者簡介:
譯者簡介
李見修
台灣大學物理系、中央大學天文所畢業,德國慕尼黑大學天文物理博士。
喜愛閱讀原文書,因緣際會之下開始了翻譯工作。
目前從事科學研究,並利用閒暇時間進行翻譯。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這本書是一位穆斯林女性深具洞察力的書寫,是閱讀伊斯蘭社會一條慧眼獨具的道路。」
──東海大學社會系 朱元鴻教授推薦
國際好評
「用獨到的見解,描述沙烏地阿拉伯婦女神秘的世界……用寬容的眼光,審視與我們截然不同的社會底下,極端的矛盾──然後我們會發現,或許這與我們的社會也沒有太大的不同。」
──《柯克斯書評》星級評價(Kirkus Review STARRED REVIEW)
「在這本令人驚艷的書裡,受過西方教育的穆斯林醫生將女性在沙烏地阿拉伯生活所會遇到的問題,活生生的帶到讀者的面前。我本身很少遇到如此赤裸的迴避、羞辱、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但出人意料的是,艾哈邁德博士在被極端主義逼到角落時,也發現了溫柔,並展開一場尋回她穆斯林信仰、改變生命的朝聖之旅。」
——《紐約雜誌》編輯兼撰稿人 蓋爾.希伊(Gail Sheehy)
「坎妲.艾哈邁德是一位巴基斯坦裔的英國人,31歲的她離開了紐約來到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在這裡她遭遇到許多不合理的壓迫與歧視,她有醫師執照,可以在急重症病房中使用ICU醫療儀器,卻因為身為女性,而不可以在這裡開車,而且她還必須把自己從頭到腳都用布蓋住。在這本書中,坎妲.艾哈邁德以身為穆斯林和女性主義者之姿,提出了睿智且深刻的評論,兼具包容與高度的批判性,為今日沙烏地上層階級的生活提供了深入的觀察,包括沙烏地女性與男性在戀愛、婚姻、養育後代、離婚、工作、交友等人生階段中所扮演的角色。在911之後,坎妲.艾哈邁德震懾於廣泛的反美主義。由西方名牌所搭建起來的消費主義,雖然略顯疲軟,但它仍在這本詳實的回憶錄中關於往來與衝突的篇章中佔據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所謂『現代vs.中古』、『凱迪拉克』(Cadillac) vs.『駱駝』(camel)的對立當中。」
──漢賽爾.羅克曼(Hazel Rochman)《書單雜誌》(Booklist)
「這本回憶錄是航向一個複雜世界的旅程,讀者將會覺得迷人,偶爾也會有反感……本書是一本深刻且細膩的紀實,為讀者揭開一個大多數人一生都沒有機會窺見的神秘世界。」
——《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
「從廿世紀初爭取婦女選舉權,西方婦女運動一個世紀以來成果斐然。然而對於今日在南亞、中東、非洲等廣大地區的婦女情境,西方女性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卻很難相干。在威權的穆斯林國度如埃及、蘇丹、葉門、沙烏地阿拉伯或伊朗,不易看到婦女運動熟悉的示威遊行、組織動員、遊說。然而我們卻不能說這裡沒有婦女運動,一種或許沒有領導中心、不太喧囂、卻是日常漸進式的強韌抗爭。婦女週、書展、影展、運動競賽,都可以成為刨掘父權結構的行動時機。為什麼塔里班要刺殺一個十四歲想要爭取受教育的少女馬拉拉?看似誇張卻很有啟示:蘇聯與英美軍事武力都摧毀不了的塔里班,深知他們真正的掘墓人:在一個女性普遍受高等教育的國度,塔里班不可能存活。本書作者坎妲.艾哈邁德醫師與馬拉拉一樣是巴基斯坦裔的穆斯林女性,而本書裡令人冷顫的宗教警察(見本書24章)則與塔里班同屬一個宗派勢力:Wahabi。我認為這將是未來半個世紀劇力萬鈞的鬥爭。這本書是一位穆斯林女性深具洞察力的書寫,是閱讀伊斯蘭社會一條慧眼獨具的道路。這是我推薦這本書的理由。」
──東海大學社會系 朱元鴻教授推薦
名人推薦:「這本書是一位穆斯林女性深具洞察力的書寫,是閱讀伊斯蘭社會一條慧眼獨具的道路。」
──東海大學社會系 朱元鴻教授推薦
國際好評
「用獨到的見解,描述沙烏地阿拉伯婦女神秘的世界……用寬容的眼光,審視與我們截然不同的社會底下,極端的矛盾──然後我們會發現,或許這與我們的社會也沒有太大的不同。」
──《柯克斯書評》星級評價(Kirkus Review STARRED REVIEW)
「在這本令人驚艷的書裡,受過西方教育的穆斯林醫生將女性在沙烏地阿拉伯生活所會遇到的問題,活生生的帶到讀者的面前。我本身很少遇到如此赤裸的迴避...
章節試閱
內文試閱
〈Chapter 1在貝都因人的床畔〉
從醫院的瑣事中忙裡偷閒,我把目光轉向外面的世界。才上午十點,熱浪早已洶湧肆虐,灑水器正將珍貴的水珠澆灌在曬傷的草上,花瓣隨著夏瑪風搖曳,此時正是西北風最強勁的時刻。
在樹籬的陰影下,一名孟加拉工人正尋求庇蔭,免於太陽的荼毒,他拖著脫水的身軀,享用著午餐,頭上汗水淋漓的頭巾,是他在高溫之下唯一的慰藉;遠方有臺百萬賓士跑車呼嘯而過,捲起漫天沙塵。我透過口罩,對著自己的倒影微笑,倒映在擋風玻璃中的我,是穿著白色醫師袍的女子,我的外表跟以前在紐約執業時無異,而現在一切卻已不同。
我回到卡拉.奧泰比的身邊,她是我在沙烏地阿拉伯的第一位病人:貝都因人,看起來年過七旬,但沒人確定她究竟幾歲(在沙烏地阿拉伯,女性出生時並未登記)。她因肺炎而接受插管治療,病情沒有太大的起色。她正昏睡,對我的注視全無反應。同事正準備替她更換中央靜脈導管(置於深層血管的大型靜脈導管)。
在準備的同時,她身上的衣服被褪去,另一位醫師用沾了優碘的棉片在她古銅色的肌膚上消毒。這是個我曾進行過無數次的平凡流程,但在沙烏地阿拉伯,卻讓人如此詫異。她的軀體瞬間被藍色的無菌床巾所掩沒,我將視線往上移,卻發現她臉上依舊罩著黑色的面紗,彷彿她正在外頭的市場中,匆匆穿過一群閑晃的男人。這一幕震撼了我。
凹凸不平的面紗遮住她臉上每一處細節。黑色尼龍布正中央的凹陷處,是一張沒了牙的嘴,塑膠導管從中蜿蜒而出,穿出她的面紗(伊斯蘭傳統服飾,用於隱藏女性的美貌)。一條導管將呼吸器緊緊的與她的肺相連,另一條則將養分輸送到她的胃。導管與面紗交疊且不住顫動著,有時伴隨著輕聲嘆息,有時則是咳嗽聲。刺耳的聲音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在面紗底下是一位重病患者。透過黑色的尼龍,我可以看見在她眼皮上貼著的黑色眼罩。護士溫柔的拉起面紗的一角,讓醫生得以完成消毒工作。我沉醉的盯著她看,完全忘了消毒的流程。
在這片黑色尼龍軟布的深處,浮現一支更大的塑膠波浪管柱,這是主呼吸管。它順著病人的呼吸道蜿蜒而出,隨著每一次機器送入的氧氣發出嗖嗖聲響。在呼吸管的末端看不到病人的臉,而是一片空洞,好像呼吸器是在給這層面紗充氣,而非維持一個女人的呼吸。我學到,即使在極度病危的情況下,遮住女人的臉比什麼都來得重要。我注視著一切,陷入宗教與科技間的衝突。這是我的宗教,屬於我信仰裡的一部分。突然,我聽到背後傳來一陣激動的聲響。
在因手術而拉起來的帘子後面,有位家屬來回走動。他是患者孝順的兒子,時不時盯著我們看。看著他纖細的咖啡色手指不住的轉動念珠,我看得出來他很明顯是在擔心。我想他應該是擔心中央靜脈導管的植入手術,就像其他的家屬一樣。
他時不時的爆出飛快的阿拉伯語,要求護士聽從他的指示。我好奇他究竟是在要求什麼,一切都很順利,事實上,我們很快就要完成插管手術,我們幾乎要結束了,那麼他到底在擔心什麼?
我從疑惑中慢慢摸出了一點頭緒。每當外科醫生的袖子碰到病人的面紗,讓面紗滑動時,這個孩子就呈現一臉焦慮,這個看起來年約十九歲的孩子,一直痛苦的將眼神避開,深怕不經意看到母親全裸的身體,以及他這輩子第一次看到的女性乳房。
每當他下完命令之後,外科醫生的口罩底下總會接著傳來含糊的阿拉伯語,要求護士照做,並且把面紗固定好;外科醫生的口氣聽起來漠不關心,但這個兒子似乎被固定在一張不舒服、令人痛苦的網上,他焦慮的踱步,擔心母親的健康、擔心她的尊嚴,以及她對上帝的責任;她在面紗底下的病容,以及她隨著年齡而下垂的裸露乳房,形成了一幅令人難以想像的畫面,我跟這個阿拉伯的子民一樣感到困惑。
我凝視著除了臉上罩層紗之外全身裸露的病人,以及在一旁監督一切的脆弱兒子(我心想,為什麼不是女兒呢?)。在她因為麻醉而陷入深深昏迷的睡臉上所罩的面紗,讓我覺得非常困惑,我想上帝肯定不會要求她把身體也遮起來,不讓醫生檢查她的身體吧?一個失去意識、病重的穆斯林,是否跟一個意識清醒、身體健康的穆斯林一樣,要承擔同樣的責任呢?雖然我是個穆斯林女子,但我之前從未想過這個問題,我的辯論是內隱且孤獨的;在我身邊的人卻很清楚他們自己的義務:患者是女性,所以必須戴上面紗。外科醫生正在指導菲律賓籍護士,如何滿足患者兒子的要求;看得出來菲律賓籍護士很習慣面對這類問題;患者的兒子則從母親身上學到他的義務。只有我,如墜五里霧之中。
我更進一步的看著她,試著瞭解更多。纖細的手臂無力的垂在她仰躺的身側,手掌向上,瘦弱的三頭肌微微顫動;她看起來很矮,最多不過一百四十公分,在兩隻手掌上,我可以看到掌心有著藍色的斑點,這些是代表所屬部落的深色、圓形刺青;護士將面紗移開,保持呼吸道的暢通,將過去半個小時內所產生的,充滿氣泡的唾液給吸出。
現在,垂下的黑色尼龍布被移開了,我終於可以一睹奧泰比女士的芳容:飽經風霜的臉上滿布痛苦,凝結的淚珠從眼罩後面的眼皮中流出。我告訴護士準備一些止痛劑,同時看著無聲的眼淚在她凹陷的雙頰上蜿蜒流動,眼淚在這張受到沙漠中烈日鞭笞與強風侵蝕而變老的臉上聚集成小水窪。她的顴骨聳立;本應是牙齒聚集的地方,現在已是一片空洞;她的下巴突出,給人一種堅定、倔強的印象。我思忖她醒著時會是什麼模樣。
她臉上的記號掩飾了女性的特徵。現在我可以看到複雜的藍色刺青形成交叉的圖案,刺青在她臉頰的正中央交叉,就像在癌症患者身上做記號,來標示放射性療法的標靶部位,只不過這個叉來得大得多,在她的額頭上也有類似的符號,就在她禿掉的眉毛上交叉,呈現完美的對稱;這一切讓人痛苦的裝飾,難道只是為了在面紗被揭開之際,還能隱藏住女人的容貌嗎?我好奇這些符號所代表的意義,於是問了我的阿拉伯同事們。原來她是部落裡的長老,臉上的刺青代表她在部落裡的位階,同事們如此向我解釋,早已厭倦了我的好奇心;顯然他們已經看過無數帶有刺青的貝都因女子。對他們來說,奧泰比太太沒有任何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
她咖啡色的小手即使在睡夢中仍然握著拳。我把她的手指扳開,看到粗短、無血色的橘色指甲。我知道這顏色是來自指甲花;我看著自己抓住她的手,我那充滿光澤的黑色指甲,和她修剪過的橘色指甲形成強烈對比。我的手來自西方,而她則是來自東方,這兩者是如此的不同,但有著同樣愚蠢的念頭:改變我們指甲的顏色。
我因為發現彼此間第一個相似之處而無聲的微笑著。阿拉伯的貝都因女子經常在妝扮時使用這顏色──在手掌中塗上一些黏黏的深綠色指甲花液,然後緊緊的握拳,將指甲尖端深深的埋入這厚重的染料。女人們常常在睡前拿繩子緊緊的綁住手,只為了醒來的時候可以擁有橘色的指甲。奧泰比女士肯定在幾個禮拜前,當她的身體還無恙的時候做過這事。我把視線往上移,看著她凌亂、被汗水沾溼的頭髮,在髮絲上也見到了指甲花的痕跡,在與龐大的白色髮絲之間的戰爭中節節敗退。
在她圓滾的肚子上,有著無法解釋的傷痕,小小的、皺皺的,比旁邊的肌膚蒼白,綴滿她的腹部。這些傷痕均勻的分布在她的腹部右上方,看起來像是腹腔鏡手術的痕跡,但不該在這個部位才是,我想不到有什麼器械會留下這樣的痕跡,我抬頭看著同事,一臉困惑。
「她去找過巫醫──貝都因的治療師。他們都這麼做。我們常在肝病的患者身上看到這些記號。」他繼續說:「巫醫用燒紅的烙鐵去治療患者幾個月前開始的疼痛。」
我後來發現,有許多病人身上都帶有同樣的痕跡,通常是為了舒緩因肝臟發炎而加劇的苦痛。肝炎在沙烏地阿拉伯是很常見的疾病,而我的新工作地點,利雅德的法哈德國王國家護衛軍醫院,是治療肝臟病變的卓越醫療中心。在這裡,我們看到上百名肝臟出問題的病人。貧窮的病人常常略過沙烏地阿拉伯的諸多公立醫療中心,轉而尋求民俗療法,當他們來就診時,往往已病入膏肓。
所以,身處於我所熟悉、閃閃發亮、高科技的加護病房環境之中,我卻遇到未曾見過的事物,我被這個女人身上所揭露的古老療法深深困惑;更困擾我的是,在這個信奉回教、推崇知識進步的宗教國家中,巫醫和異教術士又扮演了什麼角色?
我的思緒在兒子不斷幫母親蓋上面紗時飄蕩,即使她是如此病重,他仍舊堅持幫她蓋上面紗。難道他看不出來,在這個當下,她的生命隨時都有可能消逝,而面紗是最無關緊要的一件事嗎?難道他不知道上帝充滿憐憫、寬容和理解,絕對不會在這樣的情況下對面紗一事挑剔嗎?我甚至懷疑上帝會在任何情況下在意面紗。
我甚至覺得在手術中罩上這層面紗,只不過是兒子個人的要求,但也許關於這點我也錯了,我已經開始注意到自己對這個國家一無所知。或許當病人在無力反抗時,發現自己的面紗被掀開,將會感到暴怒。但對我來說,我只看到:對一個垂死的女子來說,面紗竟是必要、無可避免的存在。這就是我所身處的新世界。在這個當下,以及接下來的兩年,我將會看到許多我無法理解的事物。即使我是一個穆斯林,但在這個國度,我仍覺得自己是個外人。
〈Chapter 2離開美國的時刻〉
我回憶起幾星期前離開美國的那個寒冷夜晚。大雨讓街道濕得發亮,模糊的車陣向前蜿蜒,這是我最後一次開車經過這裡。我感到一陣壓力襲來,將我深深的壓進皮革座墊裡。我是否還會再稱呼這個國家為我的家呢?我所搭乘的,飛往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班機,將於九點時從甘迺迪機場起飛。我最近的經歷,讓我變成那個反映在照後鏡中,臉上充滿遺憾的移民者。是時候該離開美國了。
延簽被拒,我的美國移民夢最終破局。當我最後一次試圖改變我的身分被拒時,我毅然決定要將我的醫術帶到中東,帶到那個美式醫藥被廣泛應用的地區。這是一個倉促的決定,讓我再度變成一個被遺棄的人。
在紐約的那幾年,我完成了住院醫師以及主治醫師的訓練,獲得內科、呼吸道疾病以及重症照護的執照。我也完成了睡眠障礙的主治醫師訓練,就快要獲得執照了。我在紐約的短短幾年,繳出了一張漂亮的成績單,得知我不能在美國繼續待下去之後,不到幾個禮拜,我就被沙烏地阿拉伯的一家醫院聘請。在我一開始的猶豫稍稍消除之後,我接受了這份工作,以及誘人的免費住宿和優渥的薪水。作為一位穆斯林女性,我相信我非常熟悉回教國家,對沙烏地阿拉伯的生活並不擔心。我不顧朋友的反對,毅然決然接下這份工作,再也不去多想。
開著安靜的凌志汽車,我踩下油門,加快速度,不住擺動的雨刷加深了我的哀傷,只因我不知道何時才能再度開車──我早已知道在沙烏地阿拉伯是不允許女性開車的。在利雅德,我將會被核發醫生執照,允許我對病重的患者進行手術,卻永遠不能開車──只有男人才能享有這項特權。
在我開往機場的路上,我感覺到腳下的車發出一陣開心的嗚嗚聲。我已經開始想念踩著油門的原始快感和力量,這種從內心深處將我和車子融為一體的感覺。不久後,我的車鑰匙就會消失。大西洋的風吹亂了我厚重的頭髮、撫摸我女性波浪的秀髮,很快的,我的頭髮就會被遮起來,驅走這嬉戲的微風。沙烏地阿拉伯立法規定,在該國我必須把頭遮起來。一切都將變得不同。
我搜尋記憶中那個下大雨的夜晚。抵達甘迺迪機場時,機場空蕩蕩的,這是在九一一之前,永遠回不去的寧靜、美好的日子。登機手續在幾分鐘內就完成了,我公寓內的物品將暫時寄放在紐約的倉庫裡,這是一個隨意的決定;我的車留給一位朋友,他會幫我保存好,直到我回來。我直覺的感受到,我只是短暫離開。
「今年到底怎麼回事?」我記得我對自己這麼說過,當時我正魯莽的簽下合約,隨意翻看內容,忽視那些用粗體字標注的死刑訊息。因為無知的決定,我發現自己現在受到阿拉伯法律的規範,其中包括砍頭。
我一個人在登機口前等待,試著用快壞掉的手機打電話。我鼓起勇氣,用開玩笑的心情研究著聚集而來跟我搭同一班飛機的旅客。
我以前看過的阿拉伯人並不多,像是在克里夫蘭診所等待問診的病人、在哈洛德百貨公司的迪奧專櫃看到的零星幾位阿拉伯人、以及在希思洛機場轉機,帶有異國情調的阿拉伯旅客。今晚我看到了幾十個阿拉伯人,我目光所到之處,阿拉伯男人跟女人都是分開坐的,有個無形的屏障把他們隔開。我聽到幾句阿拉伯語的呢喃,一小撮阿拉伯人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注視著他們。
一組又一組的阿拉伯人用一種準確的方式,依照只有他們才知道的幾何圖案,朝對稱的線聚集。他們排成整齊的行列,朝向停機坪,面對夜晚的大西洋。現在是宵禮的時間,是穆斯林在日落之後最後一次的晚間朝拜。看著他們朝拜,讓我覺得很不自在,這提醒了我沒有遵守朝拜的規定,但我仍然發現自己對此情此景極其入迷,在我身邊,就在機場的休息室,一個名副其實的清真教儀式正在進行。阿拉伯人朝拜了二十分鐘,我無法將視線從他們身上移開,但其他人對此似乎一點興趣也沒有。
當他們膜拜上帝的時候,我很好奇阿拉伯男子的頭飾怎麼能在他們把額頭碰觸地板的時候,依然保持原樣、不掉下來。他們每一次磕頭,我都期待那紅白相間的格紋頭飾會不會掉下來,那底下是不是有什麼機關?女人們則融成一團,在隔著玻璃的夜空底下,她們看起來就像一團黑色的聚合物,輪廓無法分辨。我幾乎沒注意到這些阿拉伯女子,我早已忘記,再過幾個小時之後,我將會成為她們的一分子。此時此刻,我的眼神被那些穿著優雅長袍的男士們吸引。
我很困惑,這一幕在我的紐約生活中從未出現過。我一直都不知道這些穿著長袍、戴著面紗的禱告者存在。我到過這個城市裡的幾座機場無數次,但在此之前,這些阿拉伯人對我來說都像看不見一樣。我感受到自己陷入在他們極度的虔誠之中,我緊張的瞧了瞧自己為這趟旅程所準備的裝扮。我希望自己的衣服得體,讓我可以順利進入沙烏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是一個回教國家,遵從回教律法(上帝的神聖法律);沙烏地阿拉伯也是所有穆斯林所尊敬的聖地,最重要的是,它是回教的守護者,同時也是聖城麥加(回教的精神以及歷史中心)的所在地。作為一個穆斯林女子,我想尊敬沙烏地阿拉伯,我絕對不想表現出不敬之意。
開始廣播登機了,阿拉伯人各個分開、打散,朝登機口席捲而去。我是機上屈指可數的西方人之一,很少旅客跟我一樣,女性、獨自一人、「非阿拉伯人」──這是我從現在開始擁有的新代名詞。看了看身邊的層層面紗,我懷疑機上有任何人跟我一樣,是個西化、不偏激的穆斯林女子。
我丟掉手中最後一杯星巴克殘留的冰冷液體,看著一大群身著黑衣的女子朝空橋席捲而去,我看得出神。我把手機關掉,現在的我完全與外界失聯,美國正迅速的變成我的過去。
在入口,一個阿拉伯女空服員引導我往東走。混合式的帽子上附著面紗,遮住了她一部分的頭髮,但她光滑、沒有皺紋的脖子還是露了出來。我可以聽到她跟乘客用一種生硬、近似德文的語調在談話,我很快就知道,這是沙烏地阿拉伯語。每一個斷句、喉音,都是來自深不見底的喉嚨。
「女士晚安。」她用字正腔圓的英文說:「您要搭乘今晚飛往利雅德的班機嗎?」我略帶猶豫的點了點頭。
「往沙烏地阿拉伯的班機請往這邊走,女士。祝您有個愉快的旅程。」她優雅的朝空橋揮手,同路的旅客匆匆走過,急著將小孩、行李還有其他拖在身後的東西一同帶上飛機。這鼓起我在瞬間消逝的勇氣,我開始跟著其他人前進。
我已踏上旅程。
我在座位上坐好,把安全帶稍微拉緊,在等待飛機飛離美國的同時,一個虛幻飄渺的聲音開始祈禱。
「以阿拉之名,我們讚美主!祂是如此完美,沒有祂的幫助,我們將無法飛翔。上帝是我們命運的主宰。」
機長複誦這段精心準備的穆斯林祈禱文,給即將展開這段航程的旅客。透過廣播,充滿韻律的阿拉伯文嚇了我一跳。我呆呆的盯著機長廣播的喇叭看,很快的,我著迷於他們放在螢幕上的阿拉伯文字。看不見的可蘭經文在我身旁編織成一層柔軟的保護網,我發現自己很放鬆,這已經是一趟不同的旅程,從前這些經文我只有從父親口中喃喃聽到過,回教勢力正在增長,之前僅限於我小小家庭中的隱私,現在變得非常公開。
在那段第一次飛往沙烏地阿拉伯的航程中,我經常想起我的宗教。爬進這架飛機後,我一頭栽進廣大的回教世界。在機艙的中心有一個大屏幕,一般是用來播放電影的,現在卻顯示出一個一動也不動的飛機剪影,被一支白色箭頭釘住;這影像永不改變,箭頭指向麥加的方向,是所有穆斯林的精神寄託,穆斯林稱它為「Qibla」。我發現自己盯著它看,我被深深的吸引。
沒有睡意的我,為了排遣無聊,我好奇的看著其他旅客。即使在一萬公尺的高空,走道還是擠滿了忙碌的乘客,飛機上有好幾排座椅被拆掉,以清出空間,即使是經濟艙,大概每十排座位就有一個私密的凹室,讓乘客在飛機上也可以進行朝拜。我只看到男人在這個半開放的空間遵守朝拜的習俗,至於他們的妻子,寧願蜷縮在自己的座位上,進行簡化版的旅人朝拜。一整晚都有阿拉伯男人在走道上來回走動,手上滴著剛行完洗手儀式的水(這是朝拜的必要手續)。當他們前往朝拜的凹室時,天鵝絨的禱告墊隨意的被放在他們高大、寬闊得令人驚訝的肩膀上。我的座位靠走道,所以我預期他們會經過我。他們每個人身上都留有濃厚,但令人心曠神怡的古龍水味道,這是他們剛剛在洗手間為了朝拜所做的準備(航空公司知曉回教國家建議男性使用古龍水,因此體貼的提供了大量的古龍水,供乘客免費使用)。在他們的右手上,念珠隨著默默的禱告旋轉。我注視了他們很長的一段時間,無法入眠,也不願朝拜。
我時不時把上飛機前隨手抓的一本《財富》雜誌(Fortune)拿出來翻閱,本月的封面是一個沙烏地阿拉伯億萬富翁,我心裡暗忖,這正好符合我的旅程。我開始認識瓦利德.本.塔拉勒王子,照片上他穿著沙烏地阿拉伯式的長袍。從我身旁走過、跟王子穿著一樣服飾的男子們發出的沙沙聲令我分心,使我抬起頭來,我無法看出飛機上的男子跟這位王子間的差異,這古老的服裝似乎傳達了平等的概念。我飢渴的看著文章,試著去記住王子的名字。這個國家將成為我的家,我渴求任何與它相關的知識。
無聲的焦慮深深困擾著我。我憂心一切,其中最擔心的是我的外表。再過幾個小時就要降落了,我開始認真考慮我的穿著:米色的寬鬆休閒褲、套頭毛衣以及一件灰色長袖的開襟衫,搭配一頂帽子。我希望不要引起別人的注意,所以已經穿上沙漠般的保護色了,但我還是向女空服員尋求確認。
「我看起來怎麼樣?我的打扮合適嗎?我很擔心,因為我沒有符合阿拉伯要求的罩袍。我知道在沙烏地阿拉伯,所有的女人都需要穿罩袍。我會因為這樣,在機場遇到麻煩嗎?」我聽起來好像小朋友在喃喃自語。
「您的穿著很完美。」她親切的說。我想她應該是在說謊,開襟衫在我身上看起來太短了。我早該留意到的,我將正式成為一位穆斯林。我知道我的臀部太惹人注意了,大聲的昭告我的性別,我真希望有其他的東西可以隱藏我弱勢的性別,我幾乎希望自己是個男人。
「哈立德國王機場是一個國際的區域。」她接著說,聲音大到周圍的人都聽得到,完全無視於我累積的焦慮。「在機場裡您不需要穿罩袍,當您抵達目的地,女士們會幫您準備一件罩袍。」她給我一個毫不動搖、堅定的微笑,讓我安定下來。
在進入沙烏地阿拉伯的領空一小時後,我們降落在利雅德。我往窗戶外面看去,當飛機還在繼續飛行的時候,我盯著外面好長一段時間。在深夜時分,外面是一片由星光點亮的沙海,綿延好幾公里遠。「內華達!」是我腦海中第一個閃過的念頭。這裡前後左右數公里的範圍內,都是荒蕪的景色,荒涼、完全平坦。我突然感到被無聲的陰謀拉了一把,這將會是一場冒險。
通過密閉的空橋下了飛機,我的飛行已跨越了一日。夜晚的熱氣穿透了我的袖口,把令人發懶的空氣灌入我的衣服底下。即便現在是十一月底的凌晨兩點鐘,穿著輕薄的毛衣對我來說都嫌太熱。在昏暗的空橋出口,散亂的旅客湧向由石油堆砌出的王國所散發的耀眼光芒。
混和著恐懼以及著迷所帶來的顫動,我像是接受父母指腹為婚的新娘一樣,偷窺著初次見面的沙烏地阿拉伯。我在強烈燈光的照射下眨著眼,往頭上看了一眼,一個巨大的雷蒙威時鐘標示著時間。我先聽到了聲音,之後才看到由大理石噴泉所形成、發出很大聲響的瀑布。它噴灑著珍貴的水,在這裡一公升的水比一公升的石油還要貴。我的眼睛抵抗著疲勞,開心的盯著室內的造景庭園看:我的鞋子踩在閃閃發亮的大理石地板上,發出清脆的聲響,隨著腳步的挪移,拼花地板也呈現出灰色、白色、米色、沙色的美麗光澤;銅和玻璃將巨大的大理石空間分隔成寬廣的樓梯、巨大的中庭、入境關口,以及大理石造景,真讓人覺得心曠神怡。這裡沒有不苟言笑、頭戴鴨舌帽、手拿指示牌還戴著花俏耳機的豪華轎車司機,也沒有來自海地的計程車司機在招攬乘客。我在一個離壓抑、憤怒非常遙遠的世界,我突然感到一陣疏離感。
身後傳來議論紛紛的阿拉伯語將我的注意拉離這一幕。我全身緊繃,有那麼一刻,沙烏地阿拉伯的士兵全副武裝、戴著扁帽靠近我,我就站在他們身旁,距離近到我可以看見他們臉上的鬍渣從輪廓分明的下顎冒出來,但他們似乎沒有看到我。他們有深邃的眼睛、英俊的臉蛋,他們故意提高音量給人壓迫感,但我一句也聽不懂。他們在搜尋一張臉,最後,迸出找到人了的大喊聲,混亂中是一陣戲劇性的請安,接著他們就往前走了。他們是某個政要的護衛,顯然這個政要跟我搭乘同一班飛機。帶走了身穿紅色和白色衣服的政要,他們也一同帶走了充滿迷人風情的口音。
我走下通往護照查驗關口的樓梯。在我前方的左右兩邊是貧窮的孟加拉男人所排成的兩條直線,他們是為了接受雜務和勞動工作而來的。他們盯著所有的女人看,而我是機場裡唯一一個沒有戴上面紗、非白人的面孔,他們毫不遮掩的盯著我看。我早已被這審視的目光激怒,用毛衣的帽子遮住我的頭,隔開那些男人像矛一般聚焦在我身上、將我團團包圍住的眾視線。我像個小孩一樣,相信如果我看不到他們,那他們也看不見我的道理,在我的「面紗」底下,我覺得好多了。
其他隊伍完全由女人組成,隔離早已展開。我注意到為了沙烏地阿拉伯僱主而來的菲律賓女子、女傭或保姆。她們看起來很貧窮,並沒有穿戴珠寶或是化妝,跟在紐約市那些穿著名牌衣服、拿著古馳的菲律賓女子完全不同。我選擇了看起來最不可怕的隊伍──裡面有著最多西方女性的隊伍。
我發現我不是唯一一個想把自己隱藏起來的女人,其他人早已穿起她們破舊的罩袍,她們急忙的從隨身行李中拉出罩袍,行李的縫隙中露出邋遢的耐吉鞋。很明顯的,她們曾經來過沙烏地阿拉伯,也許是在渡假後返回家鄉。不只是西方人在下飛機前忙著換裝,同樣的,沙烏地阿拉伯的婦女也將自己包裹得更徹底。有一個沙烏地阿拉伯的女性,看起來像是沒有準備好的樣子,她耐心的在隊伍裡排著,身上披著飛機上的毯子,像帘子一樣遮住她那頭看起來所費不貲的染髮,還有她那沉睡著、天真無邪的獎賞──一個沙烏地阿拉伯的孩子。
我研究起在我這個隊伍之中的西方女性,她們之中有許多是在附近醫院工作的護士──愛爾蘭、英國、南非白種女性。她們一點都不為別人的注視所苦,她們充滿經驗的過來人姿態讓我安心,我羨慕她們的自信,並往她們靠近一點。
終於輪到我了。一個頭髮梳理得無可挑剔的沙烏地阿拉伯士兵仔細看著我的護照。我看了看四周,想知道是否有來自我的醫院的人。我也知道,在沙烏地阿拉伯,像我這樣的未婚女性僱員,得要有一個「監管人」(從我的僱主派來的代表)來接我,同時把我的文件交給護照查驗人員。如果醫院沒有派人來,那我將會被拘留在機場。
當我正好奇誰會被派來接我時,我看到上百個馬來西亞的穆斯林女子靜靜的蹲在大理石地板上,就在停止的行李輸送帶旁邊。她們每個人都罩著面紗,即使穿著層層衣服,我還是可以感受到她們散發出的順從、卑屈。她們把自己縮成一團,眼睛看著地上,安靜的等待她們的僱主。我沒有聽到笑聲或是輕聲閒聊,她們就像身旁未被領取的行李那樣堆著,她們安靜,沒有動作,而她們的安靜並非來自於疲勞或時差,她們是失去希望的女子。
即使我有高超的醫術,也不能改變這個事實,不論醫生或是一般的市民,不論是穆斯林或非穆斯林,未婚的女子是不能隻身進入沙烏地阿拉伯的。沒有監管人、沒有丈夫或是父親、沒有兒子或是兄弟,我們就必須像女傭一樣,跟行李一起等待、像行李一樣的等待,直到我們被人領走。在這個國度裡,女人不是獨立的個體,我的自主權早已遭褫奪。
護照查驗人員揮揮手,要我離開入境的隊伍,移動到玻璃窗口前。進行護照查驗的士兵沒有對我微笑,他不歡迎我到他的國家。即使我的姓氏透露出我是個穆斯林,他也沒有像個穆斯林般跟我打招呼,事實上,他理都不理我,他高傲的忙著檢視我的護照。在他的暗示下,我也沒有跟他閒話家常,我們的眼神沒有接觸,我很直覺的察覺到沙烏地阿拉伯的運作方式。他用一種不屑的態度揮著手,示意我往前走,把我的護照丟到一個遙遠的窗口。印著英國女王王冠的金黃戳記,被淹沒在皺巴巴、手寫的阿拉伯字條中,一股鄉愁突然湧上我的喉頭,讓我想起我在英國的童年。出於習慣,我不顧一切的往前走,試著拿起我的護照,然而卻有個笨重的身影熟練的搶走它,將它帶離我的身邊。
我抬起頭,看到一個身形龐大的男子,他用明顯的厭惡回應我的眼神,他是烏馬爾,我的監管人。在他的男性權威之下,我現在終於可以離開護照查驗關口,進入沙烏地阿拉伯。烏馬爾是來自我僱主的「接待」,我受到驚嚇的發現自己蜷縮在他男性的陰影底下。身為一個巨大、高挑的沙烏地阿拉伯人,烏馬爾穿著白色長袍,上面留有像被口水噴到的煙草痕跡。古老的涼鞋幾乎跟駝峰一樣高(它們看起來是如此的厚),跟他的衣服配成一套,露出他又肥又龜裂的腳跟;在他的頭上,戴著一頂紅白相間的格紋頭飾,那頭巾迫切需要用手按著。雖然同樣都穿著沙烏地阿拉伯人的國家服飾,他看起來卻跟我在《財富》雜誌封面上所看到的那位王子不同,他沒有那麼注意細節。
雖然他見到我了(更準確的說是見到我的護照),但他並沒有歡迎我。我們用肢體語言交談,因為他不說英文,而我的阿拉伯文又只會禱告文。愚蠢的我徒勞無功的想要拿回我的護照,但他用獅子般的拳頭緊緊的抓住,被激怒的他用皮膚鬆弛、沾了尼古丁的手指,示意我去拿我那笨重的行李。而他把巨大的身軀靠在欄杆上納涼。他試著慢慢的把肥胖的手放進一個無縫合線的口袋,拿出一包嚴重壓扁的萬寶路。他沒有任何要幫忙的意思,寧可無聊的看著我,時不時抓抓他的肚子。
行李輸送帶持續的轉動那些沒有人急著領取的行李箱,馬來西亞女傭仍然一動也不動的靠著輸送帶。我獨自把我巨大的行李箱從輸送帶上卸下,身旁圍繞著圍觀的男性,不管是搬行李的人或是旅客,沒有一個男人來幫我。
最後,行李領取櫃檯掃描完我的行李,確定我沒有把任何非法的東西帶進沙烏地阿拉伯後,我終於可以離開航站了。我鬆了一口氣,機場裡明顯的權威人士讓我感到非常不自在,急著想要離開。我踏進十一月的夜晚,沙漠吹來的西風輕撫著我的臉,沒有必備的黑色罩袍讓我顯得格格不入。我早已發現,利雅德比紐約有更多穿著黑色衣服的人。
我把自己塞到醫院的廂型車中,車窗被塗黑,廉價的隔熱紙貼在窗上,把氣泡和我困在這紫色的薄霧中。從現在起,許多我即將搭乘的車輛,本身就是一個面紗,讓我好奇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麼顏色。
烏馬爾把行李裝進車裡,把我載往新家。一塵不染的路帶我們離開機場,延伸數公里遠。這是條筆直的道路,不像倫敦或紐約,需要轉彎或是急轉彎。在這個深夜,路上的車潮驚人的擁擠,每個人都開得很快,好像在逃離逼近的死亡般。道路兩旁的風滾草和沙漠樹叢埋在無止盡的沙中,夜晚的月光映照出地球上的寧靜海。唯一在動的,是微風吹拂著沙子所帶來的無聲漣漪,但很快就被我們誇張的車速攪亂。
我們駛上往市區的主要高速公路,全球化已經到達這了。在幾分鐘內,我窺探到美國流行音樂在利雅德販賣的預告;我突然感到一陣激動,因為我童年時學會的阿拉伯文還夠用來解讀路上的廣告,我開始大聲的唸出它們的名字。十公尺外的空中閃著一道不協調的螢光,有一個看板用阿拉伯文寫著「塔可鐘」──沙烏地阿拉伯人也吃墨西哥烤肉跟捲餅!從廂型車中,我可以看到阿拉伯的家庭走出轎車,進入快餐店,我很失望,這個新世界看起來是如此令人沮喪的單調,有那麼多的美國商品。這個沙烏地阿拉伯式的地景呈現出的都是美國文化,只不過配上阿拉伯字幕罷了。在這裡的男人跟女人都吃漢堡、喝可口可樂,麥當勞、百事甚至是肯德基都跟著進駐,建構出單調又令人不安的錯置熟悉感。我沒有看到任何真正的阿拉伯式商品,我們現在行駛的主要高速公路上充斥著速食店、汽車經銷商的布條、販售通用汽車和保時捷。
從我們身旁呼嘯而過的車子當中,充斥?凱迪拉克,裡頭載滿了沙烏地阿拉伯婦女以及她們的孩子,開車的都是男人。我很好奇,時間這麼晚了他們要去哪?每臺車後方的窗戶都用深色的隔熱紙或窗帘遮住。這條公路上有著比紐約公園大道更多的凱迪拉克,但在每臺光鮮亮麗的車子內的人,肯定大都來自這個國度。我露出第一抹不被察覺的微笑。
漆成黑色或鐵色的賓士S系列越過做作的凱迪拉克,在高速公路上競賽。我看著左手邊,眼神鎖定在一隻長睫毛的駱駝身上,牠坐在一臺飽受摧殘的鈴木小卡車裡,這明確的提醒了我,我已經不在紐約了。橡膠路標用手寫體標出「一般道路」,德國轎車的新王國正在削弱駱駝的舊王國,這兩者在麥加高速公路上對決。
我看著那些司機。在這些有著凱迪拉克、賓士外型的現代駱駝之中,這些現代貝都因人有著鷹一般銳利的雙眼,他們慵懶的握著方向盤,每個人都戴著格紋的頭巾和飄逸的白袍,每個人都帶著一支手機,這幾乎是他們頭巾的附屬品。男人們毫不在意的用單手開車、身體歪斜著。這裡有這麼多穆罕默德的繼承人,當然,這裡完全看不到女性駕駛。這現代與中古世紀間的衝突是如此荒謬、喧鬧──賓士跟貝都因人、凱迪拉克跟駱駝,在我留在這個國度的期間不停的出現,總是那麼的顯眼。
那時我還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被這許多的第一次給虜獲了。
內文試閱
〈Chapter 1在貝都因人的床畔〉
從醫院的瑣事中忙裡偷閒,我把目光轉向外面的世界。才上午十點,熱浪早已洶湧肆虐,灑水器正將珍貴的水珠澆灌在曬傷的草上,花瓣隨著夏瑪風搖曳,此時正是西北風最強勁的時刻。
在樹籬的陰影下,一名孟加拉工人正尋求庇蔭,免於太陽的荼毒,他拖著脫水的身軀,享用著午餐,頭上汗水淋漓的頭巾,是他在高溫之下唯一的慰藉;遠方有臺百萬賓士跑車呼嘯而過,捲起漫天沙塵。我透過口罩,對著自己的倒影微笑,倒映在擋風玻璃中的我,是穿著白色醫師袍的女子,我的外表跟以前在紐約執業時無異,而現在...
目錄
目錄
Ch.1:在貝都因人的床畔
Ch.2:離開美國的時刻
Ch.3:我的新家─軍事基地
Ch.4:採買罩袍
Ch.5:蒙面和安全
Ch.6:獨自跳舞的沙烏地阿拉伯女子
Ch.7:蒙面的醫生
Ch.8:沙烏地阿拉伯的迷途男孩
Ch.9:一個父親的悲傷
Ch.10:上帝的邀請
Ch.11:回教的中心
Ch.12:走進光中
Ch.13:上帝的子民
Ch.14:百萬人潮所組成的巨輪
Ch.15:誤觸禁忌
Ch.16:找醫生
Ch.17:沙漠的女兒
Ch.18:下一站:赦免
Ch.19:星空下的禱告
Ch.20:在魔鬼和紅海之間
Ch.21:穆特威:身穿咖啡色服裝的男子
Ch.22:單身沙烏地阿拉伯男子
Ch.23:暴風雨前的平靜
Ch.24:清淨徒的怒火
Ch.25:沙烏地阿拉伯的齊瓦哥醫生
Ch.26:在沙烏地阿拉伯墜入愛河
Ch.27:請出示結婚證書
Ch.28:以眼還眼
Ch.29:王子、一夫多妻與貧民
Ch.30:沙烏地阿拉伯式離婚
Ch.31:沙烏地阿拉伯的離婚女子
Ch.32:沙烏地阿拉伯的慾望師奶
Ch.33:打造一個沙烏地阿拉伯女性外科醫生
Ch.34:辣媽
Ch.35:沙烏地阿拉伯的葛羅麗雅.史坦能
Ch.36:兒童戰士
Ch.37:沙烏地阿拉伯對九一一的看法
Ch.38:最後的時刻,最後的日子
後記:嚴峻的光輝
註解
參考書目
分組閱讀討論指南
致謝
目錄
Ch.1:在貝都因人的床畔
Ch.2:離開美國的時刻
Ch.3:我的新家─軍事基地
Ch.4:採買罩袍
Ch.5:蒙面和安全
Ch.6:獨自跳舞的沙烏地阿拉伯女子
Ch.7:蒙面的醫生
Ch.8:沙烏地阿拉伯的迷途男孩
Ch.9:一個父親的悲傷
Ch.10:上帝的邀請
Ch.11:回教的中心
Ch.12:走進光中
Ch.13:上帝的子民
Ch.14:百萬人潮所組成的巨輪
Ch.15:誤觸禁忌
Ch.16:找醫生
Ch.17:沙漠的女兒
Ch.18:下一站:赦免
Ch.19:星空下的禱告
Ch.20:在魔鬼和紅海之間
Ch.21:穆特威:身穿咖啡色服裝的男子
Ch.22:單身沙烏地阿拉伯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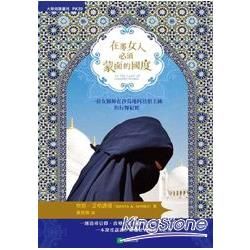
 共
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