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下來,我們就已失去「清白」的資格。
「天助自助者!」雖然奉行這句格言的人有時會被視為自私,但我真心認為,不遵照這句話的人是軟弱無力,跟寄生蟲沒什麼兩樣。
——葛瑞絲
人生的選擇不是非善即惡,不過是一團混沌,
所有的決定,都只為了好好活下去
1914年夏天,鐵達尼船難後兩年,葛瑞絲.溫特,22歲,剛剛成為寡婦,也是一起船難中的倖存者。
為了脫離父親經商失敗的窘迫日子,也不甘願只能淪為家庭教師,一心想進入上流社會的葛瑞絲,終於成功嫁給英俊且多金的亨利.溫特。然而,當她和丈夫搭乘高級輪船從局勢不穩的歐洲返回紐約時,船上卻發生神祕爆炸事件。亨利想盡辦法讓葛瑞絲最終能搭上救生艇,她卻從此與丈夫天人永隔。
一旦失去了食物與容身之處,人性中的善意與崇高也會隨之消失殆盡。
救生艇在大海中漂流且人數超載,食物和飲用水有限。在無處可去的船上,權力、謠言、飢渴、受凍等等現實開始展開人性對求生的意志與極限。眼看船已開始進水,眾人饑寒交迫,精神與體力都瀕臨崩潰。為了讓更多人活下去,哪些行為該被視為救人,哪些決定該被認定為殘酷?葛瑞絲眼看著船上的紛亂,為了活下去,她必須做出選擇。
法律的權威至高無上,我們仍在官司中載浮載沉。
獲救後的葛瑞絲出乎意外地被捕入獄,即將面對審判。她雖然從汪洋中生存下來,卻必須面對另一場生存之戰,回答「為什麼你們能活下來?」的問題。律師與心理醫師建議葛瑞絲寫下那二十一天的漂流狀況。只是,她的「日記」能否道出真相?或者,這一切只是助她在法庭上繼續活下去?
作者簡介:
夏綠蒂.羅根
1975年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主要從事建築及工程等領域的工作,目前和丈夫及親愛的三胞胎住在康乃迪克州。
譯者簡介:
林力敏
輔大翻譯所就讀中,曾獲聯合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等,並獲公費補助赴哈佛大學暑期進修。聯合報〈繽紛版〉專欄作家。
各界推薦
媒體推薦:
……稱它為「一個在海上求生的動人故事」以及「一個活生生的地獄」。
──《紐約時報》書評
……彷彿在與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對話、與《蒼蠅王》共鳴,這本書實在深刻得令人難以忘記。
──英國《週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
本書黑暗而殘酷、生動精彩、節奏流暢,同時也充滿人性的滑稽。
──英國《衛報》(guardian)
也許只有小說可以解決倖存者所面臨的道德困境。本書令人不安,也令人愛不釋手。
──英國《觀察家報》(The Observer)
又怪異又了不起的一部小說。
──英國《旁觀者》雜誌
本書巧妙地布置了一個陷阱,讓讀者難以自拔。
──《房間》作者愛瑪.唐納修(Emma Donoghue)
作者以在海上漂流的救生船探索了所有人類生存,以及自欺欺人的能力。
──200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柯慈(J.M. Coetzee)
把所有讀者的注意力全部釘在書頁中,你動不了,也不想動。
──《狼廳》作者希拉蕊.曼特爾(Hilary Mantel)
引人入勝、筆法新穎,即使熬夜也想一口氣讀完。
──《負荷》(The Things They Carried)作者提姆.歐布萊恩(Tim O’Brien)
媒體推薦:……稱它為「一個在海上求生的動人故事」以及「一個活生生的地獄」。
──《紐約時報》書評
……彷彿在與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對話、與《蒼蠅王》共鳴,這本書實在深刻得令人難以忘記。
──英國《週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
本書黑暗而殘酷、生動精彩、節奏流暢,同時也充滿人性的滑稽。
──英國《衛報》(guardian)
也許只有小說可以解決倖存者所面臨的道德困境。本書令人不安,也令人愛不釋手。
──英國《觀察家報》(The Observer)
又怪異又了不起的一部小說。
──英國《旁觀者》雜誌
本...
章節試閱
第一日
在救生艇上的第一天,大家幾乎沉默不語。有些人已接受這場戲劇性災難的事實,明白自己正置身在波濤洶湧的汪洋;有些人則依然無法面對。約翰‧哈戴先生身強體壯,是第十四號救生艇上唯一的船員並且當下決定扛起責任。他依照重量配置的原則替大家安排座位。救生艇吃水很深,因此他禁止大家站立,也不准有人未經許可便擅自移動。他從座位底下猛拉出一個船舵,固定在船尾,再要求懂得划船的人負責拿那四根船槳。三名男子以及一位名叫格蘭特的強壯女子立刻應聲。哈戴先生指揮他們盡快划離正在下沉的郵輪,放聲大喊著:「快給老子死命地划,不然大家就要命喪海底啦!」
哈戴先生穩穩站定,眼神警覺小心,指揮著他們靈巧閃避海中的障礙物。他們四個人安靜、用力地划船,肌肉緊緊繃住,連指關節都繃得發白。有些人抓住長槳的尾端,想助他們一臂之力,但動作過於笨拙,害得船槳只是輕輕撫過水面,並未扎實地撥開海水。我雙腳牢牢地踩在船底,同情著他們。船槳每划一次,我的肩膀便繃緊一次,彷彿這樣做可以讓救生艇前進得更快。
哈戴先生有時候會打破這種駭人的死寂,說著:「再划兩百公尺,大家就安全啦。」或是說:「再過十分鐘郵輪就會沉下去了,最長不會超過十二分鐘。」或是說:「九成的婦女跟兒童都已經獲救。」
這些話安慰了我,雖然我之前才親眼目睹一位母親把小女兒扔進大海,再跟著跳進海中,之後便消失了。我不清楚哈戴先生是否看到那一幕,不過我認為他看到了,畢竟,他藏在濃眉底下的漆黑雙眼始終不斷地掃視,任何事情似乎都逃不過那雙眼睛。總之,我沒有糾正他,也不認為他在說謊,反而覺得他像位領袖,正試著激勵大家的士氣。
我們這艘救生艇屬於最後下水的那一批,前方海面已相當擁擠。我看到兩艘救生艇想躲避一大塊漂浮物卻不幸相撞。我冷靜地覺得哈戴先生是想找到一塊較不擁擠的水域。他的帽子掉了,現在頭髮飛張,目光炯炯。面對這種災難,大家驚恐萬分,他卻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樣。
「大夥兒用力划啊!」他放聲大吼:「讓我見識一下你們有多少力氣!」
拿槳的人聽了,划得更為賣力。後方傳來一連串爆炸聲,有些乘客還在亞歷山德拉皇后號上頭,或在附近的海面載浮載沉,這時紛紛發出淒厲的尖叫聲,彷彿是來自地獄的慘叫──如果地獄確實存在的話。我回頭望見巨大船身正在左右搖晃,並且第一次發現船艙的窗戶正竄出橘紅烈焰。
我們穿過一塊又一塊的破碎木片,經過半浮半沉的水桶,以及蟒蛇般彎彎曲曲的繩索。我看見躺椅跟草帽一起漂浮,旁邊還有一個像是兒童玩偶的物體,這使我不禁黯然想起當天早上的晴朗天氣,還有整艘郵輪原本洋溢的度假氛圍。三個較小的木桶一起漂向我們,哈戴先生大喊:「哇哈!」並且要大家把其中兩個桶子撈到船上,放在船尾那張三角形椅子的下方。他向我們保證說,這兩個木桶裡裝著飲用水,一旦我們逃離郵輪沉沒所造成的漩渦,便需要解決口渴與飢餓等難題。然而,我想不到那麼久之後的事。在我看來,這艘救生小艇的欄杆早已逼近水面,停下來撿任何東西只會害我們更難逃離沉船所造成的漩渦。
海面上漂浮著屍體,還活著的人則死命攀抓著殘骸或破片。我看到另一對母子,那名臉色慘白的男孩朝我伸出雙手,放聲尖叫。我們划到他們附近,發覺那位母親早已斷氣,屍體趴在木板上,一頭金髮披散在慘綠的海水中。那男孩戴著迷你版領帶,露出兩條吊帶。雖然我一向欣賞正式的服裝,且此刻身上仍穿著不久前在倫敦買的緊身衣與蓬裙,搭配牛皮靴,但我依然覺得那位母親把兒子打扮成這樣有些可笑。
一名男子大喊:「往這邊划一點,我們去救那個小男孩!」
哈戴先生回答:「好啊,你想把誰踹下船,好留個位子給他?」
哈戴先生說起話來就像個無禮的水手。有時候我聽不太懂他的發音,反而因此對他更有信心。他對大海瞭若指掌,嘴上說著大海的語言。我越不了解他,應該就表示他越懂得大海。沒人回答他的提問,我們就這麼划過那位正在放聲大叫的男孩。
我身旁一位瘦小男子喃喃抱怨:「我們絕對可以丟掉那兩個桶子,那麼,那可憐的小傢伙就有位子了!」
但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掉頭回去。事實上,我們對那位男孩的同情心轉瞬即逝,跟著我們的過往一起沉入汪洋,因此,我們只能沉默。只有那位瘦小男子開口說話,但他的聲音微弱得幾乎難以聽見。一些更大的聲響掩蓋掉他的說話聲,例如槳架反覆發出的規律噪音,沉船引發的轟然巨響,刺耳的號令聲,還有痛苦淒厲的叫喊聲。
「只不過是個小男孩罷了,能給船增加多少重量?」他說。
後來我知道他是基督教聖公會的執事人員,但當時我並不清楚救生艇上的各個成員叫什麼名字,從事何種職業。始終沒有人回答他。划槳的人彎著身子賣力划水,其他人也跟著壓低身體,這似乎是我們唯一能做的事了。
沒過多久,海裡有三個人奮力游向我們。他們一個接著一個抓住小艇周圍的救生索,拉得小艇更往下沉,一波一波的海水濺到船上。其中一名男子與我四目相接。他的鬍子刮得乾淨,臉凍得發白,但碧藍的雙眼散發著光芒,顯然是鬆了一口氣。我聽到撞擊的聲響,隨後看見哈戴先生舉起一隻笨重長靴擲向他的臉。他發出痛苦哀號,叫聲露著驚訝。我無法移開視線,而那位陌生男子成了我這輩子最同情的人。
我們這艘救生艇右側正在發生大大小小這類的慘事。我的丈夫亨利就在某處,也許他坐在小艇上攻擊求救的人,和我們的做法如出一轍;也許他正拼命游泳求救,卻遭到小艇上的人驅趕。亨利先前展現厲害本領,為我在救生艇上爭取到一個位子。我想到這件事便比較安心,相信他也有辦法讓自己登上別艘救生艇。不過,如果亨利也面臨生死關頭,他是否會做出像哈戴先生那樣的行為?我能嗎?我反覆地想起哈戴先生的冷酷無情——我確定那些舉動讓人毛骨悚然,也相信小艇上的其他人絕對無法像他那般殘酷。然而,那是他身為領袖的當機立斷,他的行為救了我們。他不那樣做,我們或許都會喪命。我甚至不確定那樣的行為是否該被稱為殘忍。
那時平靜無風,海面不起波浪,但海水仍會不時地濺進超載的船中。幾天前,律師以實驗證明,那艘救生艇只要再多載一位正常體重的成人,我們就會立即陷入危機。我們自身難保,無法救助每一個人,同時又救自己。哈戴先生對這一點心知肚明,並依據腦中的知識大膽行動,要不是他那幾個小時的努力,我們早已喪生海底,無法死裡逃生。然而,他的行為也引起格蘭特女士的反對。格蘭特女士是救生艇上最堅強以及最敢於發言的女性。
她大喊:「禽獸!我們至少該回頭救那個小男孩!」
其實,她自己也明白回頭只會害大家賠上性命,但她這樣一喊,卻使她儼然成為人道主義者,而哈戴先生則宛若惡魔。
那時,大家也有一些可貴的行為。身體較好的女性會照顧身體較差的女子。況且,若不是划船者的齊心協力,我們也無法迅速遠離正在沉沒的郵輪。哈戴先生一心一意要解救我們,並立刻分辨出哪些人肯聽從指示,那些人則不願聽他發號施令。其他人則多花了些時間才能辨別這兩種人。有好幾天,我並不覺得自己與十四號救生艇又多大的關聯,我應屬於亞歷山德拉皇后號上住頭等艙的乘客階級,而且,誰不會呢?儘管這幾年經濟蕭條,我依然過著奢華生活。亨利花了超過五百美元才買到頭等艙的船票。當時,我仍覺得自己要光榮返鄉,而非狼狽不堪的船難生還者,也不是落魄商人之女。相反的,我應該是某個歡迎晚宴的嘉賓,身穿華美的禮服,以及戴上珠寶首飾──雖然那些禮服與珠寶已沉入幽深陰暗的海底。我幻想著亨利終於把我介紹給他的母親,由於我們的婚姻已成事實,她對我的抗拒應會煙消雲散。我還幻想著,那些欺騙我父親的爛人會飽受唾棄,淪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哈戴先生能如此迅速應對當前的局面,我認為是因為他擁有水手的靈魂,而且早已將各種情感拋諸腦後──假使他以前確實有過各種情感的話。至於他的行為是善是惡,就暫且不論。他在腰帶上插了一把刀子,不知從哪裡找來一條破布包在頭上,代替他消失的帽子。那條破頭巾跟他夾克上的金釦子形成強烈對比。不過,改變裝扮能突顯出他可以隨機應變,而且已經準備就緒,這使我對他更有信心。等我終於想到要探望四周時,其他救生艇已與我們相隔甚遠,只剩渺小的影子。跟船難現場的騷動混亂相比,處於空曠海面終究比較安全,因此我覺得這是個好徵兆。
哈戴先生把最佳的位子留給最虛弱的那些女性,並稱呼我們為「女士」。他問我們是否安然無恙,好像他有辦法醫治我們似的。大家起初都謝謝他的好意,謊稱自己沒事,但大家都看出芙萊明女士的手腕骨折成奇怪的角度,而平時擔任西班牙文家教的瑪麗亞則驚魂未定,顯然大受打擊。替芙萊明女士的手臂綁上繃帶的是格蘭特女士。第一個大聲質問為何哈戴先生會在這艘救生艇上的也是格蘭特女士。後來我們才知道,雖然按照規定,每艘救生艇上必須要有一位受過訓練的船員。但是,舒特船長與多數船員皆留在郵輪上維持秩序,協助乘客登上救生艇,避面恐慌。
我們在緩慢卻逐間拉大的距離之外,親眼看著油輪上的船員與乘客已不分彼此,只想迅速降下救生艇。但是,由於郵輪劇烈傾斜,他們越急反而越手忙腳亂。後來船身開始由內往外破裂解體,情況變得更加混亂。等到我們這艘救生艇準備往下降至大海時,已無法筆直從甲板垂降至海面。這艘小艇很可能會反覆撞到傾斜的船身,操作滑輪與繩索的船員也必須耗費更多力氣,才有辦法讓救生艇的船首與船尾以相同速度下降。當我們的船垂降到海面後,立刻又有一艘救生艇往下垂降,但它卻忽然整個翻轉,上面的老弱婦孺全都墜落海中。我們聽見他們放聲叫喊,在海中揮舞雙手求救,但我們並未向他們伸出援手,而且,要不是有哈戴先生指揮我們,我們可能會跟他們落入相同的噩運。經歷過整件事之後,我可以肯定地回答我先前質問自己的那個問題:如果哈戴先生沒有攻擊那些游向我們的人,我可能就會親手驅趕他們。
第一日
在救生艇上的第一天,大家幾乎沉默不語。有些人已接受這場戲劇性災難的事實,明白自己正置身在波濤洶湧的汪洋;有些人則依然無法面對。約翰‧哈戴先生身強體壯,是第十四號救生艇上唯一的船員並且當下決定扛起責任。他依照重量配置的原則替大家安排座位。救生艇吃水很深,因此他禁止大家站立,也不准有人未經許可便擅自移動。他從座位底下猛拉出一個船舵,固定在船尾,再要求懂得划船的人負責拿那四根船槳。三名男子以及一位名叫格蘭特的強壯女子立刻應聲。哈戴先生指揮他們盡快划離正在下沉的郵輪,放聲大喊著:「快給老子死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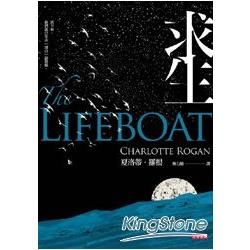
 共
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