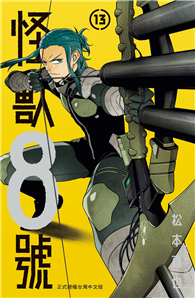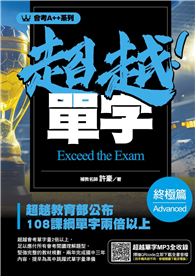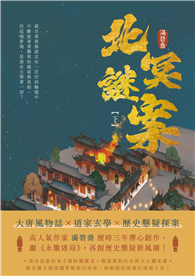導讀
你未曾認真對待過的你
它是你生命的莫逆之交。
人體所能展現的任何一種功能,沒有一項是多餘的;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了「看而未必見」、摸不到,來無影、去無蹤,從你有生以來始終伴隨著你的夢。
然而,它總是被「誤認」為多餘;因此,它也是我們生命中最被「誤解」的一環。
夢,是帶著訊息來的,不僅在你「日有所思」時才如此;縱使在你未必有所思、或者在你未必意識到自己其實有所思時,它也仍然忠實的把你「應該」知道、或者最好能夠知道、或者「也許需要知道」的訊息,在你意識逐漸放下、潛意識逐漸開放之間,娓娓的傳達給你。
意識,代表著我們在清醒狀態下有意無意的武裝、防衛、造作;潛意識,則代表著我們程度上的開放。
腦子,這個意識運作的中心,在為我們鑽營、為我們設計,也因此為我們設防,因此而饒有定見且堅固不化。所有致力於追逐心靈超越的人都知道,腦子正是我們力圖超越的大敵,唯有真正超越了腦袋,人才有真正進入心靈層次,獲致生命療癒的可能;然而,已然習慣了萬般都依賴腦子的我們,這又談何容易。
相較於意識,潛意識更為接近真實的我們,而它多半只活躍於我們全然放鬆的狀態下,譬如我們的睡夢之中。此時,我們的心靈開始呈現吸收的渴望,夢就在這時被邀請了進來,參與我們生命的「討論」。它忠實的發言、毫無掩飾的建議、給予建設性的提示、慷慨的給出線索,經常也直指痛處;剩下的,只是我們想不想聽,以及聽懂了多少、接納了多少——你要是不想聽,或者從不把它當作重要的生命伙伴,你當然就總是記不得它。
對夢的敏感,女人顯然比男人強烈得多、感性顯然比理性強烈得多、開放顯然比壓抑強烈得多;而敏感的人受益於夢,顯然也比不敏感的人豐富得多。
細細的回想、咀嚼,你當了悟,這世上最瞭解你的,實是你的夢;只可惜它始終遭受忽略——在我們的意識裡,它經常只是我們心底不經意掠過的一抹殘影,而在生活中,它充其量也只是我們偶然沉吟回味的落葉一瞥,或僅權充茶餘飯後的素材——如果你一覺醒來還記得它的話。
據一位藏族朋友說起,每天早晨,家族的人通常都會聚在一起,說說昨夜的夢境,互相分享、彼此解析夢的「境象」。他們視夢境猶如「先知」,包括對身體的,以及對過去與未來的種種索隱。這在他們家鄉,由來已久;因此他們對夢都能保持著一定的「警覺」,深怕錯過了哪一場事關重大的夢。而她自己包括家人的幾場大病,以及她後來的婚事,據說也都受益於夢中的「啟示」。
夢,自有它的生命,而它的生命是和你的生命融為一體的;它的生命是伴隨著你的生命而有的——至少,你在王鳳香博士於這本書裡的論述,可以清楚的得到這樣的理解和印證。
它不僅只是你白天「未竟之夢」的重現而已,它也是你心裡情緒的反映和觀照,尤其是那許多躲在潛意識裡的那些被壓抑的、被遺忘的、被擱置的嚮往或恐懼、憂煩或悲傷;以及潛伏在我們身體裡面較深處、隱約莫測的病兆或病灶。
探討夢境或夢的書,未曾少過,但王鳳香博士以其中醫、心理學和哲學的深厚學識背景和豐富的臨床,並從《黃帝內經」等中醫和中國文化經典的基礎上,將觸角伸入疾病與夢境的勾連,不恣意於神祕領域的渲染,理路清晰而有所本。這本書實是諸多尋夢作品之中,較能符合醫學和科學,且脈絡清楚的一本。
夢在我們生命中絕非可有可無的事,否則生命不會給你這些——你該知道,生命絕不會隨意去做一些沒有意義的事;你的腦子會,你的夢可不會——它太瞭解你的生命、你的身心,它太瞭解你了!
『生命有路』書系總策劃
詹德茂
自序
我出生於中醫世家。學中醫是聽從父命,學心理是聽從心聲。
我自幼喜愛文學,曾立志要成為作家。初中時偷偷寫過從未發表的詩詞與小說;但在高考(高等教育升學考)填報志願時,父親在密密麻麻的學校中圈出了中醫藥大學,「就讀這所吧,離家也近,我們放心。」父親平靜的聲音中並沒留有可商量的餘地。
本科無可選擇地攻讀中醫學,但我對人身的關注遠不如對人心的好奇。總想搞清楚那些謎一樣的問題,人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人的意志信念、思想心靈,尤其是那些神奇的夢境:美妙的飛翔、恐怖的追殺、荒誕的奇遇……,那些逼真的畫面究竟是怎麼來的?它們又意味著什麼?
大學圖書館成為我尋找答案的地方。我開始廣泛涉獵心理學、哲學、社會學、文化學等方面的書籍,母校圖書館裡有限的書籍幾乎被我翻閱遍了,還借來同學的圖書證跑到外校去借閱。
那是充滿趣味也充滿迷茫的五年寒窗!
大學畢業後我參軍入伍,成為一名軍校教師。中醫課程歷來枯燥乏味、不受學生歡迎,但是我的課堂卻常常爆發出笑聲和掌聲,因為我把很多心理學的知識融入中醫課程裡,講得繪聲繪色,深深吸引住了年輕的軍校學生。任教期間我多次在優質課評比中獲獎,獲得優秀教師、優秀黨員、科技先進個人等榮譽稱號,並榮立三等功。在進行素質教育期間,軍校領導指派我為全校千餘名師生進行素質教育講座,反響強烈;一九九七至一九九九年,為省報做心理版的兼職編輯,為電臺的心理節目做嘉賓,受到普遍好評。這些經歷奠定了我對心理學的信心,也激起了我更強烈的學習興趣。於是決定攻讀心理學碩士,讓自己的愛好成為今生的事業。
碩士學習期間,在系統學習西方心理學理論之後,我發現中醫學、中國文化學中蘊涵著豐富的心理學智慧。要把握中國人的心理,必須瞭解中國文化;要在中國普及心理學,必須從中國文化切入;要發展中國的本土心理學,必須以中國文化為依託。基於這樣的認識,碩士畢業後,我考取了國學泰斗朱伯崑先生的得意弟子張其成教授的博士,在導師的引領下,開始從心理學的視角研讀《黃帝內經》、《周易》等中國文化經典。這樣的研讀是艱難的,也是富有詩意的,我徜徉其中再也不肯出來,直到現在,我依然保持著每天必讀經典的習慣。我不僅將心理學與中國的文化智慧融合在一起,而且將經典智慧融入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血液,成為自我的一部分。
心理學和傳統文化的共同之處是,它們的精髓不能通過單純的讀書學習得到,而要經過修身養心來悟到。讀博士期間,我參與了一系列心理學體驗課程,並在心理督導師指引下進行了長程的自我心理分析,自我分析筆記達百餘萬字,其中詳細記錄、分析了自己每夜的夢;同時,跟隨博士生導師給一些社會精英授課。這些體驗讓我越來越瞭解自己,越來越接近那些未知的答案。我對夢的理解也從詫異到好奇,從好奇到接納,夢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它並不奇怪,我們只需要學會傾聽它、聽懂它。
最初的時候,我總是認為心理學和傳統文化是自己的兩條腿,我吃力地協調它們、磨合它們,希望它們配合默契,自己才能走得更快、更穩。但是,對二者的瞭解越深,我越發現它們之間根本不存在分別,它們不是兩條分離的腿,而是一個整體,它們在本質上是同一個東西。
近年來我一直在為高校學生、企業高層、社會精英以及心理諮詢師隊伍授課,多家出版社在聽過我的課後發出邀請,「最重要的是趕緊抓住機遇火起來!」這是很多出版社的朋友對我的真誠奉勸。我卻並沒有接受讓自己迅速「火」起來的建議,一直默默地筆耕不輟。如果我還沒到該「火」的時候,「火起來」對我來說就不是機遇而是陷阱。如果我的「鍋裡」還沒有儲存足夠多的水,火大了必然把鍋燒壞。我不想「引火焚身」,我以玩笑的口吻謝絕那些善意的勸告。
二○○八年夏天,推辭不過朋友的再三約請,我答應在某出版社出書,出版社催得很急,希望儘快付印!這時我的父親已臥床近十個月,其間回去看過幾次,總見父親靜靜地躺著,安詳得像個嬰兒。只是氣力越來越弱,先是不願下床,再是不願坐起。最後一次回去看他,父親已經不會說話,依然安詳地躺著,喜歡兒女們圍在他的床邊說說笑笑。儘管非常清瘦,但父親的眼睛卻清澈明亮,沒有老年人的混濁暗淡,也沒有暮年的悲涼和對死亡的恐慌。只是在我要返京前他抓住我的手不放,眼角溢出兩行清淚。我告訴他必須回京一趟和出版社商談書稿的事:「您要乖乖地等我回來!」他像懂事的孩子般鬆了手,還忙不迭地去摸紙巾想擦拭眼淚。但是,父親沒有履行我們的約定,我剛回京不幾天他就走了。接到電話我飛奔回家,進家門時已近午夜,灰朦的天空中懸著一輪明月,寧靜得一如父親的臉。
父親去世後兩年的時間裡,我整日在書稿上塗塗改改,卻無法靜下心來完成它。我拒絕了那家出版社的簽約請求,對其他出版社的約請也有一搭沒一搭地應付著。多少個夜晚從昏亂的夢中驚醒,回想剛才的夢卻不知所云,靜坐良久才能再次入睡。我沒有意識到這股巨大的能量和父親的離世有關。父親躺了整整十個月,這是又一次出生的時間;他安詳地走了,無牽無掛,猶如歸家。父親七十八歲過世,不算高齡,但卻是真正的善終,我應該欣慰才是。
我心難安!就像一個喝醉酒的人躑躅在路上,找不到回家的方向。我去討教精神分析界的一位前輩,他冷靜的分析中規中矩,但感覺卻如隔靴搔癢。
外求不得,我回到了自己的探索,試著讓那些昏亂的夢清晰化。一晚,我清晰地夢到一位中年男子陪著一個小女孩在看電影,男子修長挺拔,格子上衣塞在牛仔褲裡,英俊瀟灑。影院裡似乎只有他們倆,女孩幸福地依偎著他,一邊觀看一邊說笑,其樂融融。我看著他們的一舉一動,像是在看電影中的畫面,又似在看很熟悉、很親近的人,忽然我驚醒過來,一個聲音脫口而出:「我要爸爸!」與之伴隨的是噴薄而出的淚水,似乎它們已經在眼眶中蓄意待發很久,只等這聲命令。在眼淚的盡頭,我真正看清了自己對父親的不捨,看清了自己內心的愧疚。本來,在父親走的時候我可以守在他的身邊!父親是兒女心中頂天立地的支柱,無論他的身體健壯有力還是臥病在床;儘管父親在走前的十餘個月裡已經不能自理生活,但他的離世依然令我體會到巨大的喪失感。體味到這份痛,接納了這份痛之後,內心的力量開始慢慢復甦。
如今,父親已經走了三年,上週我回老家到他的墳上祭奠,墳邊一片鬱鬱蔥蔥,透露著父親的慈祥和淡然。我心已安!
由中醫改學心理,最後又回到中醫藥大學攻讀博士,每一次選擇都得到父親的首肯,他認為醫人先醫心,不矛盾。
經過近三年的醞釀,這本書終於要付梓了。雖然書中剖析的是別人的夢境,卻記錄著我對人生的感悟和心靈療癒的旅程。
這本書還不夠成熟,但足夠誠懇;雖未達豐滿,卻已致豐富;她可能被浮躁的吆喝聲淹沒,但決不會被扼殺,因為它生長在堅實的生活土壤,富有頑強的生命力。
她不會辜負您,她值得一讀!
王鳳香
二○一一年八月十八日,於北京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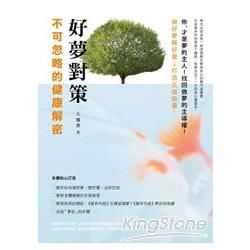
 共
共  健康是指生物的功能性和代謝效率的水平。
健康是指生物的功能性和代謝效率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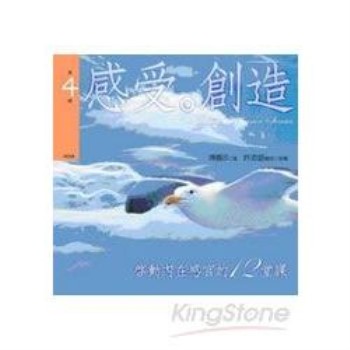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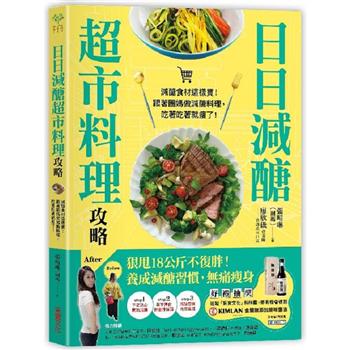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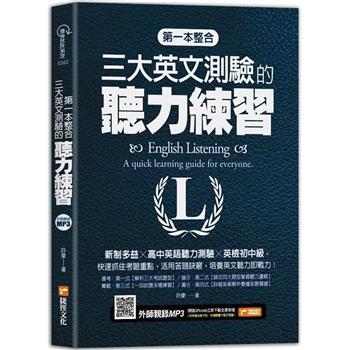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