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dBook |
|
有 2 項符合
威爾斯.陶爾的圖書 |
 |
$ 39 電子書 | 一切破碎,一切成灰(單篇)
作者:威爾斯.陶爾 出版社:一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07-18 語言:繁體中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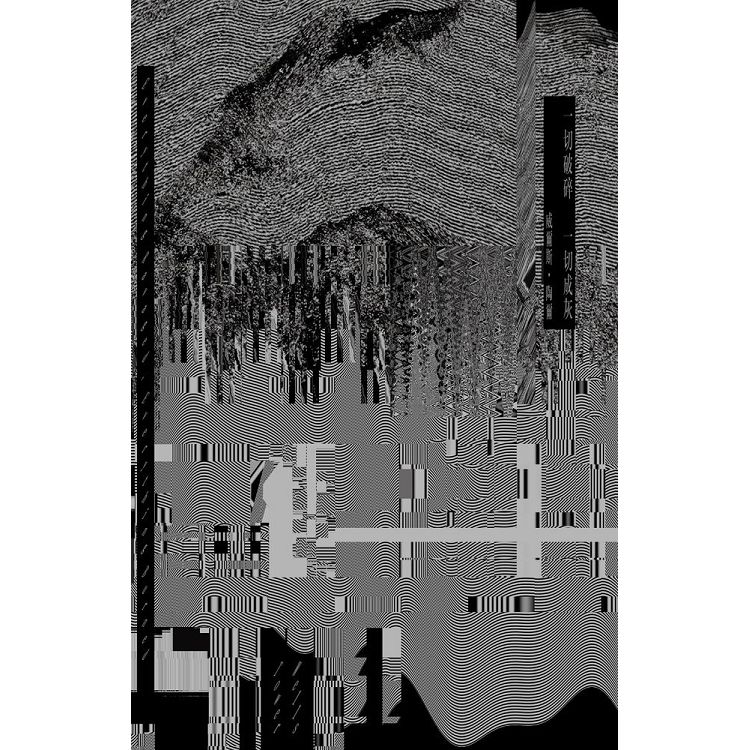 |
$ 130 ~ 360 | 一切破碎,一切成灰
作者:威爾斯‧陶爾(Wells Tower) / 譯者:劉霽 出版社:一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07-18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68頁 / 13 x 19.8 x 1.6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威爾斯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一切破碎,一切成灰
你很清楚這世界會如何對待他們,因為你自己曾親手做過同樣的事。
威爾斯‧陶爾在第一本短篇小說集裡就提供了當代現實美國社會與中世紀奇幻維京海盜並列的奇妙閱讀體驗,同時展示了小說家對命運的宏觀視野與對情感的細緻體察,獨特的視角讓他的短篇故事在看似平凡日常中爆發出強烈張力,留下不絕餘韻。九篇小說分別藉由夫妻、兄弟、親子、朋友、鄰里等或親密或陌生的人際關係,一個個處在社會或群體不同面相的邊緣角色,寫出了羈絆在人與人之間那幽微莫測的善與惡,及潛伏在日復一日生活中那無可抗拒的命與運。每篇故事都在難分難解的愛恨中,交融一爐的荒誕幽默與椎心殘酷間,呈現出一個悲傷與有趣並存,擾人不安卻又美麗迷人的小世界,既描繪出美國當代眾生的掙扎,也隱隱反映了整個西方文明的困境。
作者簡介
威爾斯‧陶爾 Wells Tower(1973-)
生於溫哥華,成長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大學攻讀人類學與社會學,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創意寫作碩士學位。畢業後曾周遊美國,打過各種零工。現專職報導寫作與小說創作,文章散見於《紐約客》、《巴黎評論》、《哈潑》等雜誌,《一切破碎,一切成灰》是他備受好評的第一本小說集。
譯者簡介
劉霽
書迷、影迷、球迷、武迷,偶爾寫作,偶爾翻譯,偶爾出版。譯有《影迷》、《再見,柏林》、《柏林最後列車》、《冬之夢》、《富家子》、《夜未央》。
|
 威爾斯,在中國又譯為威爾士,位於大不列顛島西南部,為英國的構成國之一,東界英格蘭,西臨聖喬治海峽,南面布里斯托灣,北靠愛爾蘭海,卡地夫是其首都與最大城市。
威爾斯,在中國又譯為威爾士,位於大不列顛島西南部,為英國的構成國之一,東界英格蘭,西臨聖喬治海峽,南面布里斯托灣,北靠愛爾蘭海,卡地夫是其首都與最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