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戰爭可能害死我們的朋友、破壞我們的家園
卻摧毀不了我們與生俱來的正直、慷慨與仁慈,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
亞馬遜五顆星推薦
震撼度直逼《西線無戰事》的戰地報導文學小說,
如果《戰爭與和平》為你帶來心靈成長與救贖,那這一本更是不容錯過的經典!
走過烽火、悲慟、屍骸與扭曲文化交織的片段,
她,一個女人,如何在劫後餘生的歲月中重新建立價值觀?
餐桌,這唯一的和平應許之地,
用葡萄葉捲、薩姆麵包、烤雞、優格,烹調出屬於家園的溫暖滋味!
● 烤南瓜優格:用漫長寒冬醞釀出的美味
● 穆拉式蕪菁沙拉:質樸簡單,卻帶著無限渴望
● 神聖的薩姆麵包:俄國人就要像尊敬列寧一樣尊敬它
● 留守家園的羅宋湯:烹煮的不是食材,而是等待的愛
● 葡萄葉捲:層層包裹住女人的溫暖愁緒、男人的愧疚
● 阿富汗烤羊肉: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 三色蒸餃:品嘗熱氣蒸騰中的多彩繽紛
● 中東羊肉飯: 為世界和平貢獻心力的最佳推薦
● 炸豆丸小烈士:要做這道菜,最好在10歲前就要開始準備
● 道地肥牛漢堡:家鄉味是最好的慰藉
● 安息日特製烤雞:溫暖全家的香氣是微甜的寧馨
● 能放一個禮拜的玉米糕:純天然、很便宜,還是生存的唯一希望。
● 甜甜炸線圈:即使燙口,也要搶在還活著的這一刻一口吞下。
知名公益旅行作家 褚士瑩
三立新聞台總監 李天怡 真情推薦
《虎媽的戰歌》作者 蔡美兒
作者簡介:
安娜‧巴德肯(Anna Badkhen)
蘇聯戰地女記者,善於書寫生活在戰爭中的人們。她採訪過世界上最殘酷的衝突,得到普利茲危機報導中心的資助,完成阿富汗相關系列報導,著有《戰食和平》、《等待塔利班》、《外交政策》。曾榮獲「促進社會責任心理學家協會」頒發喬爾‧賽爾丁獎,也曾兩度入圍國際報導類李文斯頓青年記者獎,作品見於舊金山紀事報、紐約時報、波士頓環球報等。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本書讓我想起,當賓拉登每天早上坐在餐桌,跟孩子一起吃著加野生蜂蜜的優格時,不是國際恐怖份子,只是個笑容滿面的父親,美味當下,沒有誰是十惡不赦的。
──褚士瑩,知名公益旅行作家
作者透過「食物」,除了傳達生活在艱困中的苦辣與酸甜,也讓讀者隨著吃進肚裡的美味,品嘗期待和平的眼淚。推薦給想要了解完全不一樣世界的你。
──李天怡,三立新聞台總監,「消失的國界」主持人兼製作人
這是本生動寫實、扣人心弦的好書,裡頭還有一些絕佳的食譜。
──蔡美兒,《虎媽的戰歌》、《著火的世界》、《帝國時代》作者
人類的慷慨原來如此深刻而普遍,並透過最卑微也最必要的人類行為來呈現,那就是飲食。
──吉娜¬.奧茨納,《俄國夢幻書》作者
作者用富於感官之美的筆觸描寫戰爭,讓我們得以和那些名不見經傳、沒有臉孔、身陷在戰爭的恐怖與困苦之中的士兵和老百姓取得連結。我們不但可以走進這些人的廚房,甚至能進入他們的靈魂。
──諾曼.奧勒斯特,《紐約時報》特約作家,《求生回憶錄》作者
名人推薦:本書讓我想起,當賓拉登每天早上坐在餐桌,跟孩子一起吃著加野生蜂蜜的優格時,不是國際恐怖份子,只是個笑容滿面的父親,美味當下,沒有誰是十惡不赦的。
──褚士瑩,知名公益旅行作家
作者透過「食物」,除了傳達生活在艱困中的苦辣與酸甜,也讓讀者隨著吃進肚裡的美味,品嘗期待和平的眼淚。推薦給想要了解完全不一樣世界的你。
──李天怡,三立新聞台總監,「消失的國界」主持人兼製作人
這是本生動寫實、扣人心弦的好書,裡頭還有一些絕佳的食譜。
──蔡美兒,《虎媽的戰歌》、《著火的世界》、《帝國時代》作者
...
章節試閱
戰地居民生活方式,和你想的不一樣
一個小男孩,在一輛戰車車頂上發現一塊形似恐龍牙齒的炸彈碎片。他用腳趾尖將它踢離城垛的石牆,再專心且滿意地傾聽著這塊金屬掉落到前線裡的碧玉色小麥田裡時,金屬與石頭撞擊的聲音。
一名游擊兵,將來福槍搭在肩上,閉起眼睛,聽著從朋友處借來的電晶體收音機,在靜電的嘶嘶聲裡大聲播放著流行歌曲,並隨之擺動身體。
一個小女孩,身著大她好幾號的衣服(姊姊們留下來的),在罌粟田裡採罌粟。這裡,曾經被一顆地對空飛彈炸出一個窟窿,腥紅色的野罌粟,沿著扭曲的莖幹往天空的方向迤邐生長。小女孩把盛開的罌粟花插進自己辮子裡。
一個婦女,正精挑細選出最熟成的蔬菜和最新鮮的肉,準備煮頓大餐。雖然外頭烽火連天,她家人卻慷慨邀請我這個外人到他們相對安全的家裡共進晚餐。
身為戰地記者的我,在一個又一個被恐怖、衝突與無盡的哀傷給浸透的國度裡,卻從這些單純卻人性化的行為中學到最重要的一課:戰爭,除了血腥的殺戮──在午夜的埋伏裡,白橘色的砲火此起彼落;槍手將食指搭在扳機上,透過機關槍的瞄準鏡掃視著沙漠,體內則旺盛地分泌著腎上腺素;鋒利的砲彈碎片,像除草機脫落的刀片般飛過空中;戰爭裡的人如何受盡折磨,如何悲慘死去--應該還有點別的。生命,在世界上某些最荒涼最暴戾的地方,正以種種勇敢的、樂觀的、頑強的方式宣示著自己的存在。
與他人分享食物,則是這種種方式當中最基本的。
本書,收錄的不僅僅是關於戰爭與食物的回憶,更是一場晚宴。我邀請各位陌生的讀者一起參加。一如所有晚宴,這場晚宴也集合了許多食譜、關係與共同的故事。朋友們來到你家,你為他們斟上飲料,盛食物在他們餐盤上,然後坐下。某某人說了一個笑話,逗得大夥兒哈哈大笑。後來,另一位朋友談起最近失去了親人,眾人剎時沈默了幾秒。接著,一位客人拿起吉他,刷起弦來。於是,有那麼個片刻,整個房間彷彿亮了起來,不一會兒大家又開始恢復交談,內容有輕佻的,有悲慘的,也有緊張刺激的。當三五好友坐下來一起吃飯時,你很難不在過程中感到雀躍或悲傷。
運氣好的話,你應該會擁有美食與良伴──這兩樣東西,本書裡都很齊全,至於你能夠品嘗到多少,全看你自己。既然我們都一起坐在這兒了,我相信,你應該可以得到豐富的收穫。
--
罌粟的交易
納吉布拉初次上戰場打仗,對抗的是蘇聯軍隊,時間在一九八0年代中末期。他就是在那時候認識賓拉登的,當時,在美國中情局的監督和資助下,賓拉登不斷從外國招募士兵並進口武器來加入阿富汗的聖戰者組織。對於這位出身沙烏地阿拉伯的恐怖主義份子,納吉布拉唯一的印象是:他是個「英勇的戰士」和「美國的代理人」(這兩者,老實說都是無庸置疑的事實)。在查拉拉巴以北大約一小時車程的達拉艾努爾(Dara-e-Nur),也就是納吉布拉的家鄉,納吉布拉還帶我們去看了看他當初跟賓拉登並肩作戰時待過的洞穴。那個洞穴,是山壁砂岩礦床上的一道裂痕,很不起眼,體積約一輛卡車大小。看起來,這個洞穴已經好一段時間沒有人來過了,因此我們也無法從中窺見大衛父親的兇手──賓拉登──在真實生活中的大概樣貌。甚至,地面上連羊大便都沒有。顯然這地方已經好久沒有人使用了。
納吉布拉聳聳肩說:「我們也沒有料到他後來會變成恐怖主義份子。」不只是他,中情局也沒有料到。
但話說回來,自由鬥士和恐怖份子,兩者要如何區分?想當初,包括賓拉登在內的那些阿富汗反抗軍在對抗蘇聯時,我們稱之為自由鬥士,而今,當同樣的這些反抗軍向美國宣戰後,我們卻改叫他們恐怖份子。再比如那些結黨起義的車臣叛軍,要是有國際伊斯蘭組織為了建立一個從太平洋延伸到大西洋地區的哈里發政權(caliphate),於是支持他們造反,而他們也為了爭取自由而將勢力擴張到國界以外,這時候的他們還是反俄羅斯的自由鬥士嗎?又或者是恐怖份子?伊拉克的什葉派(Shiite)民兵呢?二00三年春,當海珊政權垮台時,他們原本還高聲歡呼的,但是到了同年秋天,他們卻開始視美軍為佔領者和判教者,並群起反抗之。
那納吉布拉呢?這個原本與賓拉登並肩作戰,後來卻與之對抗,但總之都是為了伊斯蘭聖戰者組織在賣命的士兵,他又算什麼呢?在我看來,他是一個支離破碎、痛苦不堪、得不到心靈安詳的可憐人。一九九二年,他曾經短暫地在前蘇聯的亞塞拜然共和國擔任傭兵,加入該國的聖戰者組織(亞塞拜然人多半信伊斯蘭教),在領土權備受爭議的納哥諾──卡拉巴赫地區(Nagorno-Karabakh),對抗信基督教的亞美尼亞人。當時,招募他的軍官告訴他,他日後要對抗的亞美尼亞人,背後有蘇聯政府在撐腰;而在他的印象中(自一九八0年代以來),只要對抗蘇聯就是好事。更何況,他當時窮得要命。打了一個月的仗,卻沒有拿到半毛錢薪餉。心灰意冷之下,他回到家鄉,娶妻生子。只可惜平靜的生活沒有維持太久。不久後,塔利班勢力掌握政權,將納吉布拉打入大牢,罪名是:在蘇聯佔領阿富汗之後的種種大小戰役中,他曾經為馬樹德賣過命,而不幸的,馬樹德後來成了反塔利班政權的反抗軍領袖。
在獄中,納吉布拉天天遭到毒打,腦袋、脖子、胸部,全都傷痕累累。他家人為了救他出獄,只好變賣家中部分土地,拿了一千七百塊錢去賄賂獄卒(我認識納吉布拉時,他家人當初從親朋好友那邊借來的錢,還有一千兩百塊錢沒有還)。出獄後,納吉布拉決定:要保護自己,方法只有一個,就是再回到戰場上去。
就這樣,為了對抗塔利班政權和原先的同袍賓拉登,納吉布拉打了五年的仗。在這場仗的最後十五天,也就是二00一年十一月到十二月初,史賓加爾山區裡,一塊下雪的高原上,納吉布拉和一群弟兄們,渾身哆嗦著駐守在一個沒有暖氣設備的穀倉裡。他們用已經青得發紫的手指,緊緊抓住手中的衝鋒槍,等待上級下令,好對蓋達組織的游擊兵發動攻擊──當時蓋達組織的游擊兵們,正藏匿在這狹窄山谷的另一側,一個固若金湯的指揮中心裡。
然而,他們一直沒有接到命令。上級只是一直要他們等,等美軍在這裡投下炸彈,賓拉登的手下自然就會出來送死,到時候他們就能輕而易舉地在熔岩流凝固而成的白色地面上,將敵人給解決掉。
這段期間,納吉布拉一直沒有睡覺,因為他不敢睡,他害怕蓋達組織的士兵會趁他睡覺時幹掉他。為了提神,他和同袍們只好不斷吸菸、抽大麻。最後,總算有飛機在蓋達組織的指揮中心投下了炸彈,但爆炸的威力實在太強,納吉布拉有七名同袍都被這道震波給炸死。
後來,當煙霧消散後,這些聖戰者們才在瓦礫堆中發現,有好幾十名蓋達組織士兵和他們的妻小,全都已氣絕身亡。
我認識納吉布拉,是在這件事發生後的第四天。當時,查拉拉巴和附近的郊區,彷彿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寒冬,正在含苞怒放。在戰火稍微平息的此刻,婦女們總算可以在沒有男性親屬的陪伴下出來逛街,於是她們紛紛披起天藍色、芥末黃或橄欖綠的全身式罩袍(burqa),到市場上買東西;在重重厚紗的包裹下,她們透過面紗上的洞孔(她們全身上下唯一的通風處),針對著綿羊肉或香蕉的價格,跟攤販討價還價。一個禮拜前還不合法的寶萊塢流行樂,此時卻震天價響地在每一輛搖下了車窗的車子裡播放著(會說普什圖語的人,多多少少能聽懂印度語,這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為什麼寶萊塢那些過度羅曼蒂克的流行歌曲,居然可以在這塊看似冷漠無情、被轟炸得滿目瘡痍的土地上如此流行)。山間的道路上,許多車身上繪著繽紛色彩和夢幻場景(如寧靜安詳、水色清澈的山中湖泊,或草木盛放、萬紫千紅的美麗花園)的大卡車,不斷來回奔馳。市場上,有人駕著粉紅色、粉藍色或粉橘色的摩托車,後面拖著人力車,在摩肩接踵的街道上來回穿梭,有老態龍鍾、彎腰駝背的攤販,擺攤子賣起炸線糖,還有年輕的小男孩拿著剛剛切好的、汁多味美的甘蔗,向路人叫賣兜售。
但納吉布拉發現自己很難融入這個色彩繽紛、音響喧嘩的歡樂氣氛裡。他無法成眠,他焦躁不安,所以開始亂服成藥。但是沒用。一想到要回家去面對老婆和三個小孩,他內心就覺得好沈重。戰爭中那一幕幕死傷的場景,尤其是他前不久才看到的那些,如雪地裡的殘花敗柳,蓋達組織士兵們的妻小屍體,像鬼魅一樣糾纏著他,讓他不得安寧。
另一個像鬼魅一樣不斷糾纏著他的,是腦海裡一個揮之不去的念頭:他的一生,難道就這樣浪擲在聖戰的惡性循環裡無有出期?
為抹去手指上的炸線糖糖粉,納吉布拉伸手在衣服上一抹,又吞下一粒煩寧(這在阿富汗屬於成藥,可以輕易在藥局裡買到),然後將細瘦的雙掌交握在衝鋒槍槍管上,嘆道:「這場戰爭,幾乎毀掉了我的人生。我還沒長大就開始打仗。我看到很多人慘遭殺害,也看過很多女人失去丈夫、變成寡婦。我不是個正常人,我心理有問題。我這一生從來沒過過一天快樂的日子。我總是覺得很悲傷。」
跟阿富汗的大多數士兵一樣,不,應該說跟阿富汗的大多數人一樣,納吉布拉不識字也不會寫字。他唯一的一技之長是打游擊戰,例如在阿巴兩國接壤的崎嶇山區裡,監視敵軍的一舉一動,接連好幾天不睡覺躲在外面飄雪的洞穴裡或已經炸毀的屋子裡,眼睜睜看著自己的親朋好友遭到殺害。
而他唯一穩定的收入來源,竟是他一臉瘦骨嶙峋的老婆貝格罕(Begham)在自家下方坡地上所種植的罌粟花── 一排排像手指頭一樣細的罌粟花,構成了漩渦狀的圖案。
一年中有好幾個月,貝格罕一大早就得趕在日出前起床,到罌粟花田拔除雜草,再一直忙到日落為止;收成後,她再把這些內含豐富鴉片樹脂的種莢,拿到空地上,在炙熱的陽光下曝曬。貝格罕告訴我,這是個累死人的工作。每一年,她們家的罌粟田大約可收成九十磅重的乾燥種莢,但是當巴基斯坦的毒梟們於每年六月來此收購時,這些種莢只能換得大約兩千四百美元。然而這些錢怎麼夠他們去養小孩、照顧生病的父親,並修理家中那個在一九九0代被塔利班軍隊炸掉一半的破房子呢?更別說幫納吉布拉還債了(就是他家人當年為了保他出獄所借的那些錢)。
我曾經和吸食海洛因成癮的毒蟲交往過。從那之後,我已經有十六、七名,甚至是更多的朋友(這些朋友裡有畫家、音樂家、詩人,其中有些很有天分,有些則不怎麼樣,還有些則只是想附庸風雅)因為吸毒而葬送了性命──不管死因是吸食過量、腎臟衰竭,還是因為和其他毒蟲在髒兮兮的街頭巷尾共用針頭而染上了會經由血液而傳染的疾病。真諷刺啊,我想,那些進入到我曾經認識過甚至深愛過的人的血液裡,進入到藝術家群居的聚落或社區裡,進入到歐美大學校園裡的海洛因,源頭居然就是這裡,這個老舊破敗、鬱鬱寡歡的家庭農場,而這個家的某個成員,居然就是協助美國國防部鬥垮塔利班政權的戰士之一,而我還花錢請他當我保鑣呢。
但納吉布拉看不出這其中有什麼諷刺之處。
他說:「我們知道鴉片對人有不好的影響,我們知道鴉片在西方國家造成很多問題。但是你看,為了活命,這裡的每個人都在種罌粟。」
的確,放眼望去,從納吉布拉在山上的家到下方的山谷,這附近全是一片片整整齊齊、阡陌交錯的罌粟田。裊裊的煙霧,凍結在這些不合法的收成物上,遠方,史賓加爾山的上方,鉛色的雷雨雲已經開始聚集。眼前的景象,可以說是全阿富汗的縮影,又或者說是我所到過的、遭戰火蹂躪摧殘的大多數地區的縮影:這些土地雖然備受戰火與悲劇的洗禮,其景色卻美得令人摒息。忽然,納吉布拉將手中的衝鋒槍擺在左肩上,開始隨著我們在車上聽到過的某首寶萊塢流行歌曲的節奏,搖擺他結實的身體。他細瘦的臂膀,像翅膀一樣開始翩翩起舞,兩手的指尖互碰,飛向這兒,再飛向那兒,像罌粟花瓣一樣開了又合、合了又開,而且總是準確地落在拍點上。他閉上雙眼,笑意在臉上蕩漾開來。起碼在這一刻,這個身心遍體鱗傷的士兵總算得到了片刻的安寧。
看著納吉布拉在自家罌粟田裡以各種優雅的姿態翩翩起舞,我彷彿被施了魔法一樣,看得入迷。這對小指頭這麼會跳舞,我也捨不得納吉布拉為了保護我而把它們給犧牲掉呢。
--
黏有糖果紙的衝鋒槍
他的確沒這麼做。
當我們準備離開查拉拉巴時,旅館內那位站在櫃臺後的突擊兵,又表示要幫我們挑選保鑣,最後,他從在飯店大廳外下棋的人群裡挑了四個,要他們陪同納吉布拉跟我們一起踏上死亡道路,回喀布爾去。我答應他們,只要車子抵達首都,我就會付這些保鑣每個人一百塊錢。天方破曉,我們就出發了,這四人開了一輛皮卡,我們其他人則坐進亞摩罕默德那部古董級豐田休旅車裡。出發時,我和大衛還在心裡暗自竊笑,他們出的價錢,比「王子」當初出的天價實在便宜太多(更別說只有單程了)。
車子開著開著,忽然,我們的武裝保鑣們停下車,原來,這裡有一個休息站:三面煤渣磚做成的牆壁,頂著一片煤渣磚做成的屋頂,濃濃的黑煙,從屋內後方的炕裡不斷冒出──這,就是阿富汗版的便利超商。這幾名士兵宣布:吃午餐的時間到了。但,就在一個月前,四名外國記者才在這附近慘遭殺害。
我和大衛當然不想在此逗留,於是我們抗議說:我們不想停車,我們肚子不餓。我們求他們繼續開車,還從自備的食物裡掏出糖果餅乾來想說服他們,但他們都不為所動。
「齋戒月已經過了,」這群士兵的頭頭說:「我們不想斷食,只想好好吃頓午餐。你們高興的話儘管在車子裡等好了。」
於是,接下來一個小時,大衛和我大半時間都坐在那輛豐田休旅車裡。這部休旅車,跟阿富汗的大部分車子一樣,車窗上都掛有棉布窗簾,我們趕緊拉上窗簾。強烈的恐懼,讓我感到噁心想吐。大衛為了安慰我並消磨時間,提議說要玩遊戲:要是在我們離開查拉拉巴以前能在車身上掛著閃閃發光的霓虹燈的話,我們要用它來寫些什麼?
大衛首先丟出他的構想:「內有塔利班誘餌。」
「有輪子的自動提款機,」我回說:「富有的異教徒。」
至於這部當地的便利超商,我們想到的渾號則有:「四面埋伏休息站」、「洋鬼子死翹翹之龍門客棧」等。
這樣的黑色幽默,老實說並不好玩。但戰地記者要想活下去,就得學會用這種輕鬆的態度看待沈重陰暗的外在環境。我和大衛不停玩著這個變態的遊戲,直到我們的保鑣終於從休息站裡走出來為止。
車子繼續往前行,到了普勒查爾希(Pul-e-Charkhi;喀布爾東部的入口檢查哨就位在此)外一英里處,這群保鑣們再一次停下車。跟先前的王子和他那群塔吉克士兵一樣,這群普什圖族士兵們,也不喜歡越界到其他族群的地盤裡。他們的領隊踱步到我們的車子旁,示意我搖下車窗,說付錢的時候到了。我掏出身上的五百塊錢,遞過去給他。他數了數鈔票,確定金額沒錯後,把鈔票對折,再收進他長袖襯衫胸前的口袋裡。
接著,一個我極不熟悉的金屬聲音響起,在我還沒會過意來以前,這個阿兵哥已經掏出子彈,裝進衝鋒槍的槍膛裡,瞄準了我。
「巴克緒許,」他說。好不容易,有一句普什圖語我聽懂了,沒想到這句話的意思卻是:公路搶劫。他比比手指頭說,要活命就得再給他一百塊錢。
我往這幾名阿兵哥的身後看過去,視線落在納吉布拉身上。但我這位長相俊美的朋友,此刻卻顯得心不在焉,好像完全沒注意到搶劫正在上演。他的身體,正隨著某個我聽不見的節奏搖擺著,手指頭則在半空中飛舞。沒聽錯的話,他正在用假音哼著歌。顯然,他正陶醉在大麻菸所帶來的快感裡。
忽然,我聽到了一個理性的聲音安靜地對我說:把錢給他們就是了。這聲音或許來自我的腦袋,又或許來自大衛口中。
不料,我嘴巴裡說出來的卻是:「門兒都沒有。」因為我突然間覺得很生氣,氣這個男人怎麼可以自顧自和手下跑去吃午餐,留下我和大衛驚恐地度過了那個月當中最恐怖的四十分鐘;氣納吉布拉真的實現承諾,即使眼見我們快要沒命,還是連一根小指頭都不肯為我們犧牲;氣我怎麼會笨到把自己的性命託付給花錢請來的保鑣,結果這些保鑣最後還反過頭來對我們行搶;氣我自己為什麼要跟自己過不去,大老遠跑來這裡報導戰情,結果這個冷酷無情的國度和這些冷酷無情的人們(在那當下,我的確是這麼想的),卻壓根兒不在乎我會不會死在大幹線上。
當怒氣很可能把你給吞噬時,不管在什麼狀況下,發怒都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更何況在戰區,當情緒如箭在弦上、隨時都可能爆發,而且隨時都可能有人正準備扣下扳機時,發怒更可能馬上讓你送掉小命。這是個關於戰爭的事實,但我卻在那個當下選擇加以忽略。
那個時候,我大概以為,用這樣的方式死在大幹線上可以留芳百世吧,我居然對著這幾名阿兵哥搖了搖我的手指頭,還拿出小學生家長的口氣說:「小心我打電話跟你們上級打小報告喔。」
當然,在場的沒有人不曉得,史賓加爾旅館沒有電話,事實上可能連全阿富汗都沒有一具電話是打得通的。
「巴克緒許,」這名阿兵哥再說一次,說完還將手上的槍往窗戶裡遞過來。我仔細端詳了一下。這把槍的槍身上黏了許多鮮黃、鮮藍和鮮粉紅的糖果包裝紙,這些糖果有的來自巴基斯坦,有的是Hubba Bubba泡泡糖,有的則是上面有唐老鴨漫畫的泡泡糖。但是此刻,這些糖果紙彷彿在對我咆哮一樣。顯然,這個士兵是把這些糖果紙當作裝飾品黏在槍上。卡拉斯尼柯夫衝鋒槍一旦擊發,槍膛的溫度很快就會升高。可是我注意了一下,這把槍上頭的糖果紙並沒有燒焦的痕跡。而且,從那些已經變黃的環氧樹脂(epoxy)看來,自從這些糖果紙黏上去以後,這把槍就已經沒有擊發過了,而且應該已經好久沒有擊發了。難道我要成為這把槍下的第一個亡魂?
接下來的場景,簡直可以說是美國西部片的翻版,如果你有辦法想像的話。當然,背景必須從牧牛場轉變為中亞的丘陵。忽然,一群北方聯盟的士兵,不曉得從哪兒冒了出來,將槍口對著這幾名保鑣兼土匪說:滾蛋!不准傷害他們。看來,我原先的想法錯了,在阿富汗,還是有可能碰到陌生人救你一命的。普什圖族的這幾名阿兵哥,一句話也沒有說,坐上皮卡車就走了。而北方聯盟的這些塔吉克人,也揮揮手告訴我們:放心,我們可以走了。整個過程,發生的經過大概不到一分鐘。至於納吉布拉,他並沒有過來跟我們道別。
而且我從此再也沒有看到過他。
--
喚起溫情的悲劇色彩小女孩
關於加里薩醫院裡的故事,我寫了一篇報導。該報導不但登上報紙的頭版,旁邊還有攝影大師邁可所拍下的震懾人心的照片:一個快餓死的小女孩,彷彿某個住在古老修道院內的基督教聖徒,睜著一雙帶有悲劇色彩又睿智的大眼睛,身體卻已經殘破不堪。這女孩名叫法土瑪‧希洛(Fatuma Hillow),才兩歲大的她,身體已經因為肺結核、脫水、營養不良,和前不久的一次心臟病發而病弱不堪,瀕臨死亡邊緣。該報導刊出後好幾天,有超過一百名讀者從位在千山萬水之外的舊金山灣區寫信或打電話問我,他們能透過什麼管道寄支票到這家醫院,好幫助照片中這個小女孩盡快康復,因為這小女孩實在是太美也太寶貴了。該報導能引起這樣的迴響,對我來說已經難能可貴了。但阿布達拉醫師告訴我,這女孩只剩幾天可活了,等這些人的支票寄到加里薩這間燠熱難耐、蒼蠅滿天飛、營養不良的病房裡時,這女孩早就沒命了。
戰地居民生活方式,和你想的不一樣
一個小男孩,在一輛戰車車頂上發現一塊形似恐龍牙齒的炸彈碎片。他用腳趾尖將它踢離城垛的石牆,再專心且滿意地傾聽著這塊金屬掉落到前線裡的碧玉色小麥田裡時,金屬與石頭撞擊的聲音。
一名游擊兵,將來福槍搭在肩上,閉起眼睛,聽著從朋友處借來的電晶體收音機,在靜電的嘶嘶聲裡大聲播放著流行歌曲,並隨之擺動身體。
一個小女孩,身著大她好幾號的衣服(姊姊們留下來的),在罌粟田裡採罌粟。這裡,曾經被一顆地對空飛彈炸出一個窟窿,腥紅色的野罌粟,沿著扭曲的莖幹往天空的方向迤邐生長。小女...
目錄
推薦序 用食物了解不一樣的世界
推薦序 尋找亂世中的美味
本書佳評
自序
第一章 與阿馬德共享葡萄葉捲
第二章 夢見萵苣
第三章 烤羊肉日記
第四章 黏有糖果紙的衝鋒槍
第五章 在鐵達尼小館吃餃子
第六章 在槍口下喝伏特加
第七章 戰時的羅宋湯
第八章 耶路撒冷的前菜拼盤,古德斯的羊肉飯
第九章 餵驢子吃花生醬
第十章 提克里特的龍蝦
第十一章 搭布萊德利戰車去買麵包
第十二章 香料女郎
後記
謝詞
推薦序 用食物了解不一樣的世界
推薦序 尋找亂世中的美味
本書佳評
自序
第一章 與阿馬德共享葡萄葉捲
第二章 夢見萵苣
第三章 烤羊肉日記
第四章 黏有糖果紙的衝鋒槍
第五章 在鐵達尼小館吃餃子
第六章 在槍口下喝伏特加
第七章 戰時的羅宋湯
第八章 耶路撒冷的前菜拼盤,古德斯的羊肉飯
第九章 餵驢子吃花生醬
第十章 提克里特的龍蝦
第十一章 搭布萊德利戰車去買麵包
第十二章 香料女郎
後記
謝詞

 看圖書介紹
看圖書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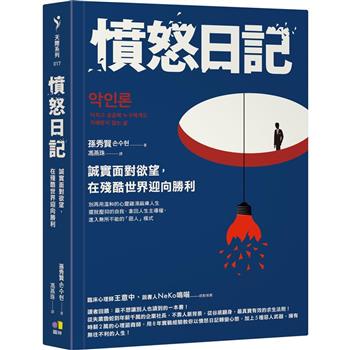





 2025【重點一網打盡】記帳相關法規概要(包含記帳士法、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八版](記帳士)](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2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