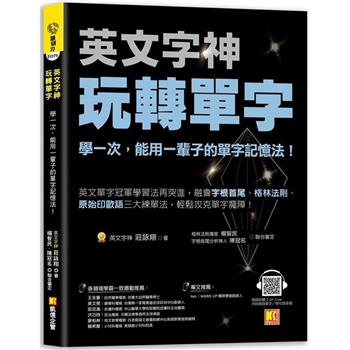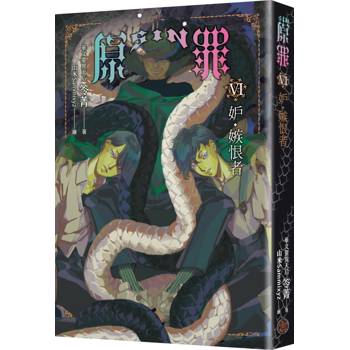這是一個母親流乾眼淚寫給女兒的編織故事,雖然她的女兒永遠也讀不到!
或許我們每個人懷抱著不同的悲傷,眼淚卻有著同等的重量……
如果把所有缺角的幸福層層編織起來,能否織成一個圓滿的美麗人生?
每個女人生命中必備的一本療癒之書
你有你的圈圈,她們有她們的圈圈……
八個女子,九段生命傷痛的故事,進入她們的編織圈圈,
發現人生不盡圓滿、卻也能美好的真滋味。
瑪莉.芭思特失去唯一的女兒後,發現自己再也無法閱讀與寫作,這些活動過去一向是她獲得安慰的主要來源。她勉強自己參加一個編織同好會,以填補她空虛寂寞的日子,但她並不知道這將會改變自己的生命。女性團友們教導瑪莉新的編織技法時,也逐漸揭露她們自己的祕密,比如失去的一切,比如愛和希望。隨著時間推移,瑪莉終於能夠說出自己的悲傷故事,因而重新發現了生命的光亮!
作者簡介
安.互德 Ann Hood(1956年 ~ )
美國小說家,目前已創作14本書包含她的散文和七本小說如遠離緬因州海岸的地方》(Somewhere Off the Coast of Maine)等。作品散見許多美國雜誌上,包括《巴黎評論》,Ploughshares,和Tin House。並經常為《紐約時報》寫社論、家政欄。目前在紐約市的New School University的藝術創作研究所教授創意寫作計劃。並與她的丈夫和他們的孩子住在普羅維登斯。
2002年4月18日,Hood 5歲的女兒,Grace死於一個致命的鏈球菌。之後的兩年,Hood發現自己無法寫作甚至是閱讀。她透過學習編織和針織得到慰藉。之後陸續創作的短篇小說都跟她的女兒Grace與她的悲傷有關。
在2004年Hood開始寫為愛編織,故事內容是敘述一個女人,其5歲的女兒死於腦膜炎。之後這個女人加入了一個跟編織有關的社團,並且與該社團的其他人一起努力。這是Hood最暢銷的回憶錄:記述了她自己的奮鬥,以及如何走過她女兒突然死亡的悲傷之旅。
譯者簡介
林婉華
曾任職教育界和出版界,目前為特約編輯、自由譯者、小大繪本館義工,擅長編寫故事、採訪寫稿。譯有《耶穌談預言》、《戰勝乳癌》、《麥摩尼地斯.八級階梯》、《坦伯頓致富金律》、《壽司與肚臍環》、《發明》、《悲傷先生的指南針》、《走出外遇風暴》、《飛碟》等書。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