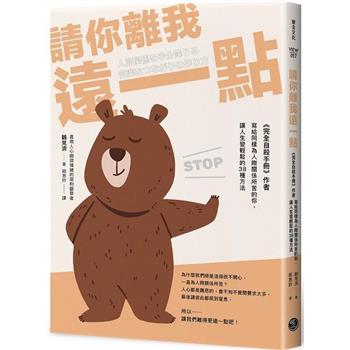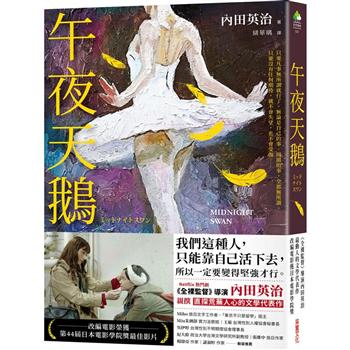一如傅柯所強調,烏托邦跟異托邦不只是「不一樣」,而是特別在這一點形成對比:烏托邦是想像的果實,它沒有真正的、可抵達的地點;相反地,異托邦真實存在,它是一個能被命名、被造訪、被居住其中的空間或是地點。(布洛薩)
布洛薩在本書中追尋異托邦而開啟的批判旅程,確實有著鮮明立場,具現於:芒通墓園;盧梭《孤獨漫步者的遐想》在被逐離人類共同體後,萌生的「與自我的共同體」(落腳於聖皮耶島);二戰太平洋戰役電影中以敘事想像力創造的小島異托邦;針對臺灣(又一座島嶼)宜居性災難的反思,以及串接異托邦、共同體和生命之所在的可能出路。(王志弘)
作者簡介:
作者
阿蘭.布洛薩(Alain Brossat)
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榮譽教授。現為國立成功大學「玉山學者」客座教授。主要研究當代法國哲學思想,並以重新思考民主深入移民、庶民與社會底層主體性議題,同時著力於文化與智識解殖研究,從傅柯哲學出發探索異托邦的諸多可能性,特別在旅居台灣多年後,發展出關於島嶼的異托邦思考。中譯著作有:《傅柯:危險哲學家》(2013)、《錯開的交會:傅柯與中國》(2019)、《遭撞翻的哲學家: 哲學評論集》(2021)、《抵抗的人民.不屈的電影:布洛薩的電影、哲學、政治札記》(2022)。
審校
羅惠珍
巴黎第八大學哲學與場域研究所碩士,旅法作家。著作有《築夢洛維尼》(2001)、《巴黎不出售》(2015)、《哲學的力量》(2016), 譯作有《傅柯:危險哲學家》(2013)、《鹽淚:巴特羅醫生眼裡的難民血淚》(2018)。
譯者
湯明潔
法國巴黎第一大學(先賢祠—索邦大學)哲學與認知論專業博士。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室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哲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法國哲學、思想體系史、政治存在論以及主體、話語和超話語等。在《哲學研究》、《哲學動態》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譯文多篇;在法國出版專著L’usage de la subjectivité. Foucault, une archéologie de la relation;已出版譯著《符號帝國》、《風暴中的哲學家》、《論拉辛》等書。
陳韋勳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士,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研究興趣是我們怎麼/如何/為什麼受治理?
王紹中
人生無處不翻譯。從字面上到字面下,從語言到非語言,從有形到無形……翻譯可說是人類生命的天職。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所畢業,「臺灣法語譯者協會——法國巴黎銀行翻譯獎」2019年非文學類首獎,相關譯作有皮亞傑《結構主義》(2018)、德勒茲《尼采》(2018)、傅柯《臨床的誕生》(合譯,2019)、塞荷《劇變的新時代》(2020)、卡胡埃《全球化的世界地圖》(2020)、傅柯《監視與懲罰》(2020)、德勒茲《尼采與哲學》(2021)。
章節試閱
異托邦、共同體、生命之所在
王紹中.譯
當前的危機濃縮在世界的宜居性(l’habitabilité du monde)危機上。更甚於過往任何時期,我們不知道在哪裡居住、如何居住或跟誰一起居住。根據西方哲學傳統,居住遠遠超過占據一個地方,擁有一棟房子或一個住所,在這兒擺上他的家具,在這兒度過他的時光,在這兒睡覺。居住是在世界中在一個特定的地點確立下來,在那裡找到他的位置,並且界定他跟環境的關係,後者是由其他人類、其他生物,以及多少靜止不動的事物所構成的。居住並不一定意味著在一塊領土(territoire)上安置下來或將其分割,因為領土——作為一種占為己有的空間(espace d’appropriation)——基本上是國家的事。但人類主體,無論他們是誰,要過上像樣的生活,便只能藉由占據空間的方式——藉由居住在一個空間中的方式,無論是透過什麼模式,定居或游牧。一個人可以宣稱自己是「世界公民」,並且用他的一生行遍地球四處移動。然而這仍舊是一種居住在地球上的方式。一個人不可能完全是無宇宙的(acosmique)、無世界居住的——或者是處於一種連根拔起、失去方向、斷絕聯繫、逐日衰弱的極端狀態中——事實上,這近乎死亡。看看在其島嶼上的魯賓遜:迷失、與世隔絕、孤獨,直到他跟星期五(Friday)的相遇——然而,他居住在此,在他的島嶼上,不然呢!
讓今日有別於過往而另立時代的因素(並且,確切地說,僅就此時代頂著人類世〔Anthropocène〕這個甜美名號的情況而言),是這個星球上無處不見的居住模式危機,層出不窮的威脅甚至危及居住在此的可能性,一個變得不宜居住的星球所帶來的可怕陰影,並且這道陰影不斷徘徊在所有的反烏托邦(dystopies)中⋯⋯
在這方面,我們或許可以談到一個臺灣範式(paradigme)。出生於此的你們無法衡量來自異地的外國人——像來自西歐的我——所感受到的劇烈衝擊。走出機場,發現這片連綿不輟的都市景觀,由大量的混凝土所構成,沿途可見一簇又一簇相互緊挨、20層樓高的建築群,高速公路和多層式交流道的交錯,鐵道沿途襯托著,令人瞠目結舌的巨大高架鋼構道路,不斷穿梭著高鐵的懸空軌道,一些蓋給底層階級並且體積較小的集合住宅,帶著它們斑駁醜陋的外觀及上了鐵窗的窗戶,宛如在監獄中,這幅景觀冷不防地穿插著幾片帶著一抹鮮綠的稻田,幾處亞熱帶樹林的僅存遺跡,彷彿這一切都在這片土地上隨機滋長,任何都市計畫盡付闕如,只在最肆無忌憚的市場法則或是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鬥爭的驅使下,上演在北起基隆南到屏東的這片橫行無阻或幾乎如此的某種房地產的法外之地……
就我而言,我花了十多年的時間,不是去習慣了這場災難,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對於這塊土地的宜居性所行使的這種侵犯(我永遠不會習慣,而我對這樣的不習慣也甘之如飴,因為這正是一道生命的跡象),就只是單單能夠與它共存而不陷入持續的鬱結。我不知道是在何處或由誰培養了這一代又一代創造出這幅世界末日、長長久久反烏托邦景觀的建築師、都市計畫師和其他工程師,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如果存在一處地獄保留給這些職業及對它們下訂單和監督的人,我真心祝福他們在那裡慢慢煎熬,直到永遠。
現在想像奇蹟發生,一切停止了,我們被告知:「好吧,來吧,讓我們從頭開始,你們獲得全權委託,我們提供你們任何條件,來讓這個島嶼重新適宜居住,重新創造一個生活環境及一些尊重其居民的人的品質的居住之地!」好吧,確切地說,這個國家的問題,恰恰是都市計畫及建築上的災難已經到了如此嚴重的地步,已經沒有轉圜餘地,這排除了任何徹底重來的可能性。在不受節制的發展主義和生產主義及狂亂的都市計畫的影響下,對環境及景觀的破壞已經達到一個這樣的飽和度,乃至於在這場災難後,人們無法再設想任何形式的重新規劃、任何讓可接受的宜居條件得以恢復的拆除/重建過程。
在西方傳統中,人們知道文明是會消亡的,而廢墟將機會留給了未來,留給了不斷自我發明並生生不息的生命——留給了文明的生成:人們可以重建、重新規劃、重新繪製都市景觀;而隨著宜居條件不斷改頭換面和重新安排,不同時代、文明,統治(等)所形成的層理(stratification)可以持續進行著。人們用高盧羅馬時期神廟的殘磚在中世紀為道路鋪砌路面。
在巴黎,奧斯曼男爵(Georges-Eugène Haussmann)在第二帝國時期摧毀了老舊的貧民街區,並透過筆直寬闊林蔭道的登場及著名的以他來命名的奧斯曼式六層建築的一致化,徹底改變了這座城市的景觀——這種種在當年皆被視為非常激烈。就這些措施加速了資產階級對巴黎西邊及中心的征服(損及下層人民的利益),從而導致巴黎的城市地理改觀這一點而言,情況確實如此。(這個由不同階層征服首都的過程,在今日以整個巴黎市的布波化〔boboisation〕告終)。但儘管如此,首都並沒有變得不宜居住,而奧斯曼式建築現在也跟巴黎的景觀及它部分的生活模式緊密結合在一起。當這些建築老舊頹圮並變得不符合衛生要求時,人們可以用一些更加現代的建築來取代它們,並且不見得會破壞整排建築物的整齊劃一、建築正面的景觀及街道的整體樣貌。
對比之下,臺灣西部讓人震驚的是都市計畫災難積重難返之明顯。如同一團又一團的混凝土,那些在此層層疊疊的東西,拿了整個「後混凝土的」、後高速公路的,以及不被囚禁在經濟成長教及金權前景(horizon ploutocratique)中的未來當抵押。這種都市計畫是以積重難返的方式劫持了未來。即便在一場核能災變或將這所有一掃而空的世界末日之後一切盡成廢墟,這景觀依然不宜居住。此外,這一切就如同在中國大陸的大都市裡的情況一樣,同一齣自尋死路的劇本再一次上演著。
或許你們可以說這是野草的範式(le paradigme des herbes folles)。觀察那些傳統平房,它們由紅磚砌成,至今猶存,或多或少處於被棄置或成廢墟的狀態,在臺灣幾乎隨處可見,特別是在鄉下,在村莊和小市鎮裡。而你們看,一旦它們被棄置,植被、野草便會以何等的速度在磚塊間重新探出頭來,鑽入廢墟,並重新構成一幅野生景觀,小型哺乳動物、鳥類,還有花草樹木在這裡取代了人類,沒有過渡階段或幾乎如此。這就是我所說的一種謙卑的、在人的尺度上的建築和棲居模式,它將它的機會留給未來。但百萬噸的混凝土恰恰相反——野草不會長在混凝土上,這種整全的(molaire)、靜止不動的、並且從根本上敵視生命及生成
的表面。更一般地說,生命不會重新生長在混凝土的廢墟上。
正是在這裡,我們開始接近我們的主題—當人們不再能夠希望藉著毀掉當下災難(le désastre du présent)的源頭(這些正是人們所認為的臺灣繁榮引為基礎的掠奪式發展主義及成長與創新宗教)來重建全部的生命形式,當人們放棄革命論述(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的……)在全球尺度上所抱持的那種涵蓋一切並全有或全無式重建的觀點時,那麼人們應該要從間隙和野草的角度開始思考。正是在災難的缺口和裂縫中,而不是在它難以想像的廢墟上(如眾所周知的,社會主義曾被認為應該會建立在「資本主義的廢墟上」),我們必須實驗一些做法,想像一些旨在重新發明生活、旨在想像出其他生活框架及形式的部署(dispositifs)。並且,正是在這裡,我文章標題中提出的三個主題展現出它們全部的重要性:異托邦、共同體、生命之所在(hétérotopies, communautés, lieux de vie)。
異托邦、共同體、生命之所在
王紹中.譯
當前的危機濃縮在世界的宜居性(l’habitabilité du monde)危機上。更甚於過往任何時期,我們不知道在哪裡居住、如何居住或跟誰一起居住。根據西方哲學傳統,居住遠遠超過占據一個地方,擁有一棟房子或一個住所,在這兒擺上他的家具,在這兒度過他的時光,在這兒睡覺。居住是在世界中在一個特定的地點確立下來,在那裡找到他的位置,並且界定他跟環境的關係,後者是由其他人類、其他生物,以及多少靜止不動的事物所構成的。居住並不一定意味著在一塊領土(territoire)上安置下來或將其分割,...
作者序
序
(複數)空間的政治
王志弘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異托邦(或譯:差異地點、異質地方、異質空間、異境、異端地帶……)(王志弘,2016:77),在傅柯著作中所占篇幅極小卻影響廣遠,在眾多學術領域中有如槓桿般,撐起繁雜多樣的主題以及思辨論述的熱情。異托邦介於真實空間與虛構烏托邦之間的定位(Foucault, 1986),以及其異質、其他、另一個、對比、倒轉、爭議等含義,在多重場域中啟動了擾動潛能。
誠如布洛薩所論,異托邦概念的價值在於其所激發的批判能力,促使我們脫離既有社會秩序,並示範另一種存在、視角及發展的可能性。但是,布洛薩也提醒我們,必須警覺異托邦概念在廣泛挪用卻失去了批判力道後,淪為「各種機會主義、裝飾性和無毒無害的用法」,取代不再有號召力的烏托邦的「撫慰人心」效果,卻隱去「令人不安」的作用。
當然,「作者已死」,概念的內涵和運用會不斷衍伸挪移,以迄膨脹、甚而爆破。學界對異托邦的理解,除了凸顯其抵抗或超越作用外,也有強調異托邦應著眼於創造差異而非投入二元式抵抗(Johnson, 2013),或可以發揮對照或揭露的效果,甚至(有如安全閥般)穩定秩序者(王志弘,2016:83)。不過,若學術介入已是政治實踐,即使面臨曖昧、模糊而不確定的現實,我們仍然必須揭明自身的價值。就此而論,布洛薩在本書中追尋異托邦而開啟的批判旅程,確實有著鮮明立場,具現於:芒通墓園;盧梭《孤獨漫步者的遐想》在被逐離人類共同體後,萌生的「與自我的共同體」(落腳於聖皮耶島);二戰太平洋戰役電影中以敘事想像力創造的小島異托邦;針對臺灣(又一座島嶼)宜居性災難的反思,以及串接異托邦、共同體和生命之所在的可能出路。這樣的立場限縮了氾濫的異托邦挪用,聚焦於批判、異議,以及偏離社會主流的持續生成過程,一段尋覓並建造共同體與生命之所在的歷程。
安置於序言撰寫者的位置,同時在城鄉規劃領域從事空間研究的「我」,與其引介本書內容而有「爆雷」之弊,不如嘗試展現異托邦作為分析工具的其他潛能,並將其捲入(複數)空間政治的爭議場域,兼論臺灣的環境規劃困境,以及異托邦如何可能是空間政治的槓桿。首先,我們來檢視序言的時空政治與翻譯的異托邦。
序
(複數)空間的政治
王志弘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異托邦(或譯:差異地點、異質地方、異質空間、異境、異端地帶……)(王志弘,2016:77),在傅柯著作中所占篇幅極小卻影響廣遠,在眾多學術領域中有如槓桿般,撐起繁雜多樣的主題以及思辨論述的熱情。異托邦介於真實空間與虛構烏托邦之間的定位(Foucault, 1986),以及其異質、其他、另一個、對比、倒轉、爭議等含義,在多重場域中啟動了擾動潛能。
誠如布洛薩所論,異托邦概念的價值在於其所激發的批判能力,促使我們脫離既有社會秩序,並示範另一種存在、視角...
目錄
序╱(複數)空間的政治 王志弘
傅柯之異托邦概念與問題 湯明潔.譯
芒通墓園裡的異托邦 陳韋勳.譯
共同體與異托邦 王紹中.譯
一座島嶼……(一個遺世獨立的世界) 陳韋勳.譯
異托邦、共同體、生命之所在 王紹中.譯
序╱(複數)空間的政治 王志弘
傅柯之異托邦概念與問題 湯明潔.譯
芒通墓園裡的異托邦 陳韋勳.譯
共同體與異托邦 王紹中.譯
一座島嶼……(一個遺世獨立的世界) 陳韋勳.譯
異托邦、共同體、生命之所在 王紹中.譯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