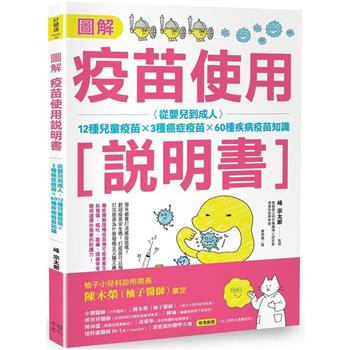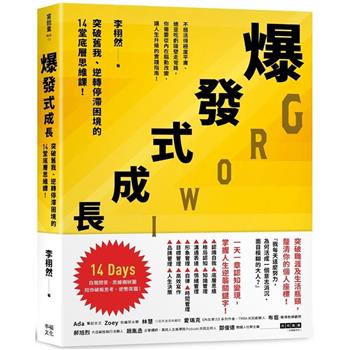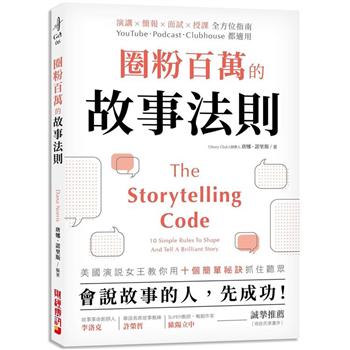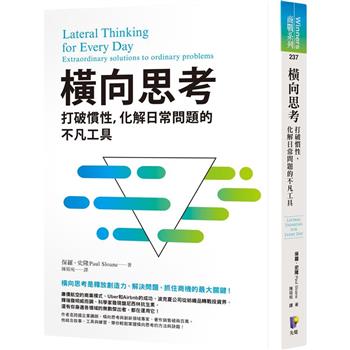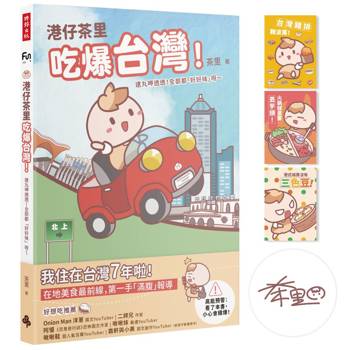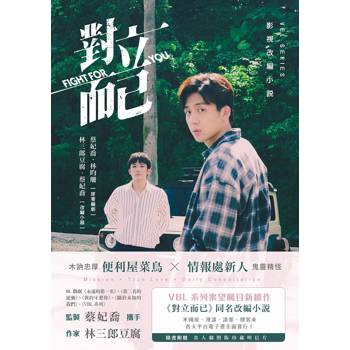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寸幸幸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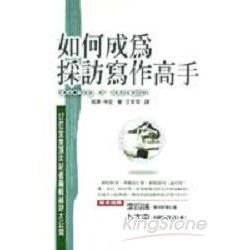 |
$ 45 ~ 210 | 如何成為採訪寫作高手
作者:William Zinsser / 譯者:寸幸幸 出版社:方智 出版日期:1999-05-24 語言:繁體/中文  2 則評論 2 則評論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如何成為採訪寫作高手
這是一本充滿了各樣看法的書。探討一些不同新聞形式的採訪寫作技巧,包括特稿、個人專欄、科技新聞、雜誌編輯、政治及公共事務報導、人物側寫、體育新聞、健康及社會新聞、自然環境報導和地方新聞。
當你在閱讀的時候,請仔細「聽」。你將會聽到十二位新聞人,暢言他們如何處理新聞、看待挫折,以及對新聞所抱持的信念。
商品資料
- 譯者: 寸幸幸
- 出版社: 方智出版 出版日期:1999-05-24 ISBN/ISSN:957679644X
-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大眾傳播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2000/03/17
2000/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