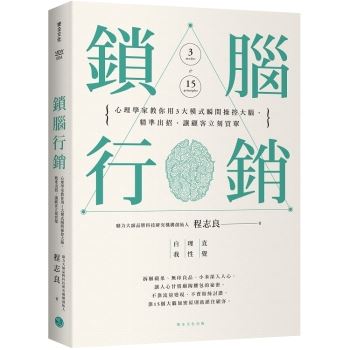學舞時期
碧娜•鮑許何時開始她的事業生涯?
是一九七七年初夏,她跟著烏帕塔舞蹈劇場到法國南錫(Nancy)的戲劇藝術節巡迴表演。從此聲名大噪,世界各地開始傳聞烏帕塔舞蹈劇場的舞作極為特別? 是一九七三年秋天,當碧娜•鮑許戰戰兢兢、並滿懷信心地爭取到著名的劇院經理阿諾•傅斯騰洪福(Arno Wstenhfer)用來吸引她跳槽的烏帕塔劇院的芭蕾舞團總監職位?
是一九六九年夏天,當這位年僅二十九歲的編舞家打敗當時已有相當名氣的編舞家葛哈•伯納(Gerhard Bohner)及約翰•紐麥爾(John Neumeier),以她的第二齣舞作《在時光的風中》獲得科隆編舞大賽的大獎?
是一九六○年春天,當這位正值二十年華的少女,以優異成績從埃森市福克旺學校畢業,獲得德國學術交流協會的獎學金前往紐約(她在此停留兩年半)進修時? 還是,她家鄉索林根(Solingen)的一位芭蕾舞老師,在看到這個把一隻腿環繞在脖子後面,將自己的身體完美地打結的小碧娜時,做了這樣的評語:這女孩真是個蛇人?
這個餐館老闆的小女兒所獲得的這句讚美,可能就是促使她未來有所成就的動機。練習,讀書,離開家鄉,考驗自己的想像力,尋找舞蹈溝通的一種新語言,發明新動作、新形式和新結構,跨越美學界限並打破藝術圍牆,最後給予舞蹈藝術新定義,讓傳統主義者感到驚慌訝異。最後她終究征服了世界,在羅馬和巴黎、維也納和馬德里、紐約和洛杉磯、東京和孟買、蒙特維多和里約熱內盧,甚至在一開始觀眾便排斥她作品的烏帕塔,到處都在歡慶她的成就。
這位編舞家從埃森搬到烏帕塔不久後,在一次訪談中提到兒時的經歷,她當時被問及出身及為何踏進舞蹈界時,如此答道:「當時我五、六歲,第一次被帶到一個兒童芭蕾舞劇團,」那時候碧娜•鮑許尚不曾看過芭蕾舞,也不曉得芭蕾舞演員要做什麼。「我就跟著去,其他人做什麼,我就努力跟著做。我還記得,老師要我們趴著,把雙腿放在頭上,然後那個女老師就說:『這女孩真是個蛇人。』」
這句話讓碧娜•鮑許感到很害羞,因為這句評語對她而言很重要。「現在聽起來很無聊,然而當時這句讚美卻令我很歡喜。當餐館家的孩子很無趣,經常很孤單,沒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我時常在十二點甚至一點都還沒上床睡覺,或坐在餐館裡的桌子下面,所以我幾乎沒有??,我父母從來沒時間好好照顧我。」
於是,剛開始她會在芭蕾舞蹈教室多待幾小時,去找同齡的孩子玩,主要是可以逃離家中那種千篇一律的無聊日子。但是不久,芭蕾舞不再是消遣娛樂而已,原因可能是大家發覺這個小舞蹈家有表演天分。「剛開始去跳舞時並沒有想太多。我就是跟著去,然後就被叫去飾演兒童的小角色,在輕歌劇中扮演電梯服務員,在非洲王國的後宮打扇子,或是當送報童之類的,或者是我也說不清楚的任何角色。但我在表演時經常很恐懼。」
這是碧娜•鮑許的生命與創作中,最大的推動力||「恐懼」這個關鍵詞首次出現的時候。這裡指的並非是那種使人癱瘓、無能的恐懼,而是可以讓人有創造力的恐懼。儘管有這些恐懼,碧娜•鮑許依舊在不知不覺中掉進劇場的天地。「我並沒仔細考慮過。或許這一切從一開始便已注定。我雖然經常很恐懼,奇怪的是,我卻非常喜歡去做。學業即將完成之前,當他人覺得不久就要畢業,所以才在好好思考或必須思考該做什麼的時候,我的心裡就已很篤定。」碧娜•鮑許幾乎是不自覺的選擇舞蹈作為職業。但當時還看不出來,它是否可以成就一個事業。
碧娜•鮑許十五歲便進入埃森市福克旺學校的舞蹈系就讀,當時該校校長是為《綠桌子》編舞的著名編舞家庫特•尤斯(Kurt Jooss)。尤斯是當時德國舞蹈界的領導人物,其地位與碧娜•鮑許二十五年後的今天所擁有的地位相同。一九二八年,尤斯創辦埃森市這所福克旺學校。在納粹正式當權主政之前,尤斯便跟納粹有爭執,因為他不願放棄他的猶太籍音樂系主任弗力茲•柯恩(Fritz Cohen)(《綠桌子》的編曲者)。一九三三年納粹上台之後,尤斯隨即帶領整個芭蕾舞團在深夜悄悄逃離德國,躲避希特勒黨衛軍的追捕,這位編舞家在英國獲知希特勒專權陣亡,儘管有人以誘人的條件要挖角他去南美洲工作,庫特•尤斯依然在一九四九年回到埃森,並主持舞蹈系,直到他一九六八年退休為止。
碧娜•鮑許師承尤斯。然而要描寫她在福克旺學校那四年中的學習情形,並不容易。當然,鮑許接受了由尤斯和他的同事西谷•雷德(Sigurd Leeder)所研發出的一種「現代」舞蹈風格訓練,即所謂的「尤斯-雷德技巧」。在她的學士畢業考時,她必須證明自己有能力以這種風格去訓練舞蹈學生。在美國舞蹈中,著名的編舞家皆極力研創自己的學校風格,且嚴格執行。然而,技法和風格對德國舞者而言並無多大意義。在福克旺學校,早在二○年代以及二次世界大戰後那時期更是如此,學生的人格、想像力與創造力的發展比特定技法的教學更為重要;就尤斯及他的追隨者而言,自由、富創造力的思考,比嚴格地訓練那些編成法典的動作形式來得有意義。
當七○年代末期在尤斯過世前不久,一位電視記者在鮑許於烏帕塔的一場首演上,問他們有關尤斯傳授鮑許何物,以及鮑許從尤斯身上學到什麼時,鮑許和尤斯經過詳細思考後,他們兩人在電視攝影機前一致表示,鮑許從她的老師身上學到「一種誠實」。一個相當正確的評語,同時也相當輕描淡寫,展現出這兩位二十世紀德國最偉大的舞蹈人物的謙虛態度。
碧娜•鮑許的特殊天分在她於埃森市福克旺學校求學時,便已顯露,老師與同學們皆有同感。「我們很早就知道碧娜是個天才!」比碧娜小四歲的蘇珊•琳卡(Susanne Linke)在後來如此證實,而琳卡因不願依循鮑許的舞蹈美學概念,於是離開舞團,展開獨舞生涯。福克旺學校特地為碧娜這位表現優異的年輕舞者設立了福克旺獎,從那時起,只有相當優秀的舞者才能獲得該獎。但德國學術交流協會(DAAD)提供她獎學金,前往一九六○年代被視為(現代)舞蹈藝術發源聖地的紐約進修,在此她開闊了視野,完成學業。這項投資所帶來的藝術價值真是日後難以估計的。
碧娜•鮑許以「特殊學生」在茱莉亞音樂學院就讀。當時她的老師個個知名,如美國的荷西•李蒙(Jos Limon)、英國的安東尼•圖德(Antony Tudor),後者是最著名的現代舞蹈編舞家之一,同時也是本世紀最偉大的古典芭蕾舞代表人物之一。此外,還有作曲家路易斯•郝斯特(Louis Horst,瑪莎•葛蘭姆〔Martha Grahams〕的音樂顧問),以及東方舞蹈專家拉美莉(La Meri)。碧娜•鮑許很喜歡拉美莉老師所教授的具異國味的舞蹈形式,特別是印度舞蹈,並將之納入她自己的舞蹈中。鮑許除了求學外,也必須實習,她獲選加入保羅•山納薩度(Paul Sanasardo)和冬雅•弗亦爾(Donya Feuer)的舞團。
原本為期一年的紐約求學後來延長為兩年半。之後鮑許因為加入新美國芭蕾舞團及紐約大都會歌劇院芭蕾舞團,而離開山納薩度和弗亦爾的舞團。此時,碧娜•鮑許跟當時剛起步的編舞家保羅•泰勒(Paul Taylor)建立深厚的合作關係。
若對這位緘默害羞的女士稍有認識,必定難以相信她會喜歡那有如巨大怪物的紐約。她對紐約的愛慕從不曾熄滅,數十年後依舊存在。「在這樣一座城市的生活經驗,」碧娜•鮑許在一次訪談記錄中表示:「對我而言非常重要。那裡的人、那個城市,體現了當代元素,混合著一切事物,不論是國籍、興趣或流行事物,所有一切同時並存。我覺得這在任何地方都相當重要。」而且,那並非跟一般人只是到此一遊般,成為無結果的經驗,「我跟紐約有極大的連結,我一想到紐約,就真的會有一點點想家的感覺,這是我對其他地方不曾有過的情緒,即是『鄉思』。」碧娜•鮑許後來對旅行很感興趣可能是因此而起,旅行成為她能在同一家劇院待二十五年的平衡力量,環球之旅讓烏帕山谷中的狹隘生活得以找到平衡點。
碧娜•鮑許終究沒有在紐約城長久生根。在那裡生活三十個月之後,她回到剛升格為大學的福克旺學校,這是她職業生涯的出發點。她返國後,福克旺舞蹈劇場隨即成立,附設在新的大學之下,由庫特•尤斯主持,這一切皆非純屬偶然。緊接著五年中,福克旺芭蕾舞團為碧娜•鮑許開啟一扇邁向世界之窗。她跟著舞團,但漸漸常以獨舞者身分四處巡迴演出,例如在斯瓦辛格藝術節、在薩爾斯堡藝術節、在義大利的史波雷多(Spoleto)舉辦的兩個世界藝術節、以及離紐約(往北)或波士頓(往西)的距離差不多的美國麻薩諸塞州的雅各枕舞蹈節。此藝術節,由現代舞蹈先驅泰德•蕭恩(Ted Shawn)創辦主持,在當時是美國最重要的舞蹈節,也是非美國舞蹈藝術進入美國的一扇大門。
但這類的巡迴表演非常稀少,每一季只有幾場演出。福克旺芭蕾舞團的巡迴活動無法跟今天的烏帕塔舞蹈劇場相比擬,碧娜•鮑許和她的同事在六○年代初的日常生活,大多是待在埃森-維登(Essen-Werden)的舊修道院中的大學練習室,每天汗流浹背的練習,一再地練習。這對一個剛從創意盎然的紐約回來的人而言,是相當挫敗與失望的,而這份絕望正在找尋一個出口。
碧娜•鮑許後來敘述,她在那段生命期間,在舞團裡不斷空轉,感到「非常不滿意」,「我很想用其他字句來形容,但實在沒辦法。當時我們也沒什麼新鮮事可做。而就是這份絕望激勵我去想,我要嘗試為自己做些事。不是為了編舞,唯一的目的只是我想跳舞。沒錯,我就是要為自己做點事,因為我要跳舞。」填補自我空虛的這個嘗試激發她未來的編舞工作,這並非不尋常,但至少比其他想像得到的編舞動機來得更好。若只是照著他人的想法舞動自己的身體、或模仿舞台上的舞步,百分之九十五(或更高些的比例)會流為趣味低劣的模仿者,無法做出完美的舞作,只有拒絕模仿他人的動作,才能讓舞蹈藝術繼續發展。
碧娜•鮑許最初的作品,既非在美感上對抗她在埃森和紐約所學的東西,也非反對一種不符合眾所需求的社會(如約同期出現的約翰•科斯尼克(Johann Kresnik)的初期作品,其因採取激烈的社會批判而受矚目,至少在《天堂?》這齣劇中,一個拄著柺杖走路的殘障者被警察打倒在地,劇中還極力袒護學生暴動,造成真正的劇場醜聞)。鮑許的處女作《片段》在一九六七年公開演出,採用貝拉•巴爾托克(Bla Bartk)的音樂,當時並未引起轟動。此劇實際上只在福克旺大學內上演,可能只有當時參加演出的人才記得該劇。
隔年,碧娜•鮑許的第二齣舞作《在時光的風中》公開上演,由米科•多拿(Mirko Dorner)作曲,一個正統現代舞蹈風格的大膽、巨大的舞台造型。但是此劇在一年之後才造成轟動||在這段期間,碧娜•鮑許效仿她的老師庫特•尤斯,為亨利•普賽爾(Henry Purcell)在斯瓦辛格藝術節中的歌劇《仙后》編舞,同時決定以《在時光的風中》參加每年在科隆舉行、對當時歐洲新生代編舞家最重要的編舞大賽。德國年輕一輩最優秀的編舞家全都來參賽,當時尚未有名氣的碧娜•鮑許能擊敗約翰•紐麥爾(現任漢堡國家歌劇院的芭蕾舞團長)、約翰•科斯尼克(現任柏林人民舞台的舞劇領導)和葛哈•伯納(一九九三年夏天過世)而獲得首獎,著實令人感到訝異。
在那之後,碧娜•鮑許的生活暫且沒有太大變化。她,誠如《法蘭克福通論報》所描寫的,依舊是「藏在隱密中的芭蕾女伶」。在這期間,漢斯•區立(Hans Zllig)繼庫特•尤斯接下福克旺學校舞蹈系的領導工作,他不僅聘鮑許為講師,同時請她帶領福克旺舞蹈劇場。於是,鮑許在埃森大學教授舞蹈,且為她所領導的舞者,幾乎在不公開的情況下,每年編一支新舞作。一九七○年,她完成一支名為《在零之後》的舞劇,由伊馮•馬雷(Ivo Malec)作曲。回顧該舞作,碧娜•鮑許在此中顯然跳脫傳統現代舞蹈的技法,開創新的概念。
在碧娜•鮑許的新舞作中,之前《在時光的風中》所大量使用的古典舞步素材突然全消失不見蹤影。舞團的五位舞者,其中一人獨舞,另四人成一組,全都穿上骨骼圖案的舞衣。他們的動作無力、沮喪、筋疲力盡。看起來彷如從一場恐怖戰爭或原子浩劫回來的生還者,正以無比的藝術力量莊嚴地舉行一場恐怖的死亡之舞。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尤亨.史密特的圖書 |
 |
$ 110 ~ 315 | 碧娜‧鮑許-舞蹈‧劇場‧新美學
作者:尤亨.史密特 / 譯者:林倩葦 出版社: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7-07-01 語言:繁體書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碧娜‧鮑許-舞蹈‧劇場‧新美學
碧娜.鮑許是德國排名第一的出口文化,因為世上無人像她這般地寫下輝煌的舞蹈史。這位當初在埃森市福克旺學校的神童、以及當今身為烏帕塔芭蕾總監的編舞家,在不到十年之間排除萬難,確立了舞蹈類型。如今,舞蹈劇場這個名詞已和碧娜.鮑許的名字畫上等號,無法分捨。
章節試閱
學舞時期 碧娜•鮑許何時開始她的事業生涯? 是一九七七年初夏,她跟著烏帕塔舞蹈劇場到法國南錫(Nancy)的戲劇藝術節巡迴表演。從此聲名大噪,世界各地開始傳聞烏帕塔舞蹈劇場的舞作極為特別? 是一九七三年秋天,當碧娜•鮑許戰戰兢兢、並滿懷信心地爭取到著名的劇院經理阿諾•傅斯騰洪福(Arno Wstenhfer)用來吸引她跳槽的烏帕塔劇院的芭蕾舞團總監職位? 是一九六九年夏天,當這位年僅二十九歲的編舞家打敗當時已有相當名氣的編舞家葛哈•伯納(Gerhard Bohner)及約翰•紐麥爾(John Neumeier),以她的第...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尤亨.史密特 譯者: 林倩葦
- 出版社: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7-07-01 ISBN/ISSN:978957326095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藝術> 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