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似假還真的生命謊言
《說謊者雅各》(Jakob der L?gner)是猶太裔德國作家和編劇家尤瑞克.貝克的成名作與代表作,被書評界譽為「以猶太人大浩劫為主題的德文小說當中最不同凡響的一本」,並且「以至今仍然無法被超越的大師級手法,娓娓道出一個難以言喻的故事」。
全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九六三年,尤瑞克.貝克已在東德影視界嶄露頭角的時候。那年他向國營「德發」(DEFA)電影公司提交了一份三十二頁的電影劇本大綱,將場景設定在納粹德國占領下的波蘭,一個於二戰末期逐步遭到清空的猶太人隔離區。劇中情節則取材自作者昔日從父親那邊聽來的一個故事。貝克事後回憶說:
父親表示自己從前在羅茲的猶太人隔離區裡面認識一位大英雄,而我應該寫出那個人的事蹟,藉此為他樹立紀念碑。我詢問那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之後,父親回答說,那個人曾經冒著被處死的危險,違反禁令私藏了收音機。他收聽莫斯科和倫敦的新聞廣播節目,然後向大家宣布好消息,給大家帶來了希望。有一天事情傳進蓋世太保的耳中……最後他遭到逮捕和殺害。
劇本大綱獲得核可後,從一九六五年開始籌備在波蘭進行攝製工作。可惜波蘭官方從中作梗取消了拍攝許可,而雪上加霜的是,負責執導的東德名導演法朗克.拜爾(Frank Beyer)由於他另一部電影的「反社會主義傾向」,在一九六六年被逐出「德發」並遭到下放。《說謊者雅各》看來再也拍不成電影了,尤瑞克.貝克生氣得乾脆把劇本改寫成小說──他的第一部小說。因此作者後來表示,我們今天讀到的這部作品源自其「憤怒之下的激動反應」(w?tende Affektreaktion)。
《說謊者雅各》一九六九年以小說的形式推出之後,相繼在東德、西德和國際造成轟動,因此一九七四年時又恢復了製片工作。然而波蘭政府再度掣肘,禁止任何波蘭演員配合演出。於是那部電影乾脆改在捷克拍攝,還空前絕後成為唯一入圍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的東德電影。後來就連好萊塢也按捺不住,在一九九九年推出了《善意的謊言》(Jacob the Liar)。
談到這裡,或許已經有人心生疑問,英雄事蹟怎麼會變成「說謊者的善意謊言」了呢?尤瑞克.貝克也曾對此做出說明:
我同樣認為那人是一位英雄,但我沒興趣寫出他的故事。因為我在關於那個時代的資料當中,幾乎總是會讀到許多……像他那般令人欽佩的英雄。我覺得再這樣寫作根本多此一舉。於是我已經把那個故事忘記得差不多了,直到某天突然靈感大發為止。
作者重新回想起父親講過的故事,並且加以改造,給真實的事件添加了戲劇性。結果那位原名哈伊姆.維達夫斯基的英雄 ,從「真的擁有收音機」變成「別人以為他有收音機」,而且他還自行炮製各種好消息,讓隔離區內的猶太人忘記眼前的痛苦,產生對未來的希望與求生的意志。接著尤瑞克.貝克不斷發揮藝術巧思與編劇長才,寫出一部「哈伊姆演義」,並且將《說謊者雅各》的主角取名為「雅各.海姆」,藉此點明故事的精髓。
「雅各」這個名字選擇得非常高明。依據《創世紀》的記載,雅各曾經愚弄過自己的哥哥「以掃」,並且在眼睛昏花的老父親「以撒」面前撒謊,騙來了「長子的名分和祝福」。 於是「雅各」始終擺脫不掉「說謊者」和「謊言」的味道。「海姆」則饒有深意,而且我們不難發現,它是一口氣快速說出的「哈伊姆」。不過二者來自不同語言,意思並不一樣。「海姆」(Heym/Heim)在意第緒語和德語有「家」或「庇護所」之意,可用於呼應雅各在故事中扮演的「心靈安慰者」角色。希伯來語的「哈伊姆」(Chaim/Hayim)更是效果十足,意為「生命」。「雅各.海姆」因而同時具備「雅各生命」或「生命的謊言」兩種內涵。
除了雅各海姆之外,書中還另有一位不知名的主角,以第一人稱的口吻向我們說故事,從「一棵樹到底能算什麼呢?」(全書的開頭),一直講到「我們正駛向我們所前往的地方」(全書的結尾)。依據敘事者的自述,他是那個猶太人隔離區的劫後餘生者,認識雅各和書中的人物。他強調自己所講的並不是雅各的故事,而只是「一個故事」。其中某些情節是雅各告訴他的,某些是他在其他當事人那邊聽到的,某些則是他自己想像出來的。換句話說,他採取與作者類似的方法,給真實的故事添加了虛構的成分。
敘事者別出心裁,將自己對樹木的思戀使用為故事的開場白。這種乍看之下讓人一頭霧水的做法,實際上是藉由「雖不存在,卻被我尋找的樹木」,逐步導引出他們的猶太人隔離區和「說謊者雅各」。樹木為何會在此產生這麼重大的意義呢?他的理由說來其實相當簡單:自從納粹德國在一九四○年初設置那個隔離區以來,敘事者已經連續四年多沒有看見過樹木了,因為那裡不准種樹!
猶太人隔離區裡面非但不准種植花草樹木,收音機更是遭到嚴禁,因為在沒有電視、電腦和網際網路的時代,笨重的真空管收音機是通往外界的最佳管道,足以打破那些猶太人與世隔絕的狀態。此外還被禁止東西多得不勝枚舉,例如人們不得持有戒指、鐘錶和其他貴重物品、不准飼養動物……,過了晚上八點更不得出門在外,因為那是宵禁時間。明白這些規矩之後,雅各可以正式登場了。
某天傍晚雅各在街頭散步時,一座瞭望塔上的衛兵責怪他過了八點鐘還在街頭逗留,要求他走去對面的管理處接受處罰。雅各不曉得時間多晚了,只得硬著頭皮進入那個不曾有猶太人活著出來的地方。誰知裡面的人竟然通情達理,要雅各趕緊回家。原來那名衛兵戲弄了他,宵禁壓根兒還沒有開始。當時雅各仍只是被說謊的對象,不過那段插曲讓他意外聽見了德國的收音機廣播:「我國英勇作戰的部隊在『貝扎尼卡』前方二十公里處,成功阻斷了布爾什維克的攻勢。」
換句話說,俄國人已經攻打到距離那個猶太人隔離區只有四百多公里的地方。此事使得原本看不見未來的可憐猶太人突然又有了明天。雅各自己卻在第二天就面臨一個大大的難題──該如何把好消息說出去。
有一位跟雅各在火車貨運站合力做苦工,名叫「米夏」的年輕人飢餓難耐,準備冒著生命危險跑去偷一節車廂上的馬鈴薯。雅各千方百計試圖轉移其注意力,甚至連關於貝扎尼卡的新聞都講了出來,卻始終不得要領。畢竟如果不說出消息來源的話,再好的新聞都只不過形同謠言而已,根本沒辦法取信於人。雅各實在不想看見米夏被一槍打死,卻又不能講明這是他從德國人那邊聽來的消息──否則人家會對他作何感想?
雅各情急之下只得隨口說道:「我有收音機。」這回米夏立刻信以為真,把馬鈴薯忘得一乾二淨,但他不幸是個大嘴巴,興奮得把事情洩露了出去。於是雅各為了救米夏一命,迫不得已說出善意的謊言之後,隔離區內很快就有兩個消息如野火般蔓延開來:俄軍正朝著他們的方向往西邊挺進,而且雅各「有收音機」。那些猶太人期盼俄國人過來拯救他們,就彷彿等待彌賽亞降臨一般。雅各隨即變得炙手可熱,不時有人過來追問收音機講了些什麼,想知道俄軍的最新動向。
如今雅各無法表明,「當初我只是隨便說說而已,我根本就沒有收音機」。為了不讓自己穿幫,他必須用更多的謊言來圓謊,每天編造有關俄軍最新進展的新聞報導。於是繼作者的「哈伊姆演義」、敘事者的「雅各演義」之外,書中又出現雅各的「貝扎尼卡演義」──除了第一次的真實報導之外,其餘都是他結合地理常識和想像力所發明出來的。雅各起先只是被迫敷衍別人,說出來的東西甚至小得還不能真正算是謊言。可是雅各很快就發現,他編造的假新聞已讓貝扎尼卡產生的正面效應不斷延續下去。其猶太同胞們原先只是「在這個受到神詛咒的年代」苟延殘喘下去,現在卻對未來充滿了希望,甚至開始進行生涯規劃,重新過著有尊嚴的生活,隔離區內的自殺率更已經降低到零。
雅各在此情況下更不能停止說謊,不能「讓希望睡著了」,否則大家將無法存活下去。他繼「被欺騙的說謊者」、「迫不得已的說謊者」以及「圓謊者」之後,進化成「充滿惻隱之心的說謊者」。雅各的謊言已名符其實成為「生命的謊言」,同時他開始領悟到,謊言越大就越容易取信於人,越能夠帶來求生的意志和勇氣。然而雅各與世隔絕的程度跟其他人沒有兩樣,如今卻被迫扮演自己所不熟悉的小說家角色,而且他「已經再也不是人」,只是收音機的擁有者。他的「收音機」則變成了怪物,讓他再也沒有正常的對話,只是繼續謊稱俄國人又打到哪裡了。
結果雅各心力俱疲。他把生命的謊言講得越來越大,讓俄軍每天攻打到離他們越來越近的地方。固然他曉得俄軍確實在向西方推進,可是他們到底在哪裡?為何即使於夜深人靜之際照樣也聽不見砲聲?隔離區內卻正在一條馬路接著一條馬路地遭到清空。雅各那位昔日在夏天賣冰淇淋、冬天賣馬鈴薯煎餅的小吃店店主,還會有辦法自圓其說下去嗎?他的謊言泡沫能夠再維持多久呢?那些猶太人的下場又將如何,他們對未來的美夢成真了嗎?
作者將三種演義結合在一起,運用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情節,給整個故事帶來非凡的張力。可是作者把故事收尾的時候顯然陷入了兩難,於是在全書即將結束時,透過敘事者之口表達出自己的疑惑──書中人物是否「有資格得到較好的結局」,抑或只能享有「雅各和我們大家所經歷過的那個結局」?其說法為:
但我就是一直拿不定主意。現在我因而同時有了兩個結局,不曉得到底該說出哪一個才好。
既然本書有兩個結局,譯者也依樣畫葫蘆把譯序分成兩個部分來寫,將結尾寫成〈譯後記〉。這麼做的好處是可以避免過早揭曉謎底,並可暢所欲言地做出解釋。《說謊者雅各》的故事主軸基本上都「有所本」,並非憑空捏造,所以不少內容可以還原出真相來。不過那只適合以〈譯後記〉的方式,等到讀者朋友們將全書閱讀完畢之後再講。譬如:全書有兩個結尾的真正理由為何?這個故事究竟發生於何時何地?本書結束時俄軍在哪裡?俄軍在什麼時候終於打進那個猶太人隔離區,找到了什麼?書中人物的命運如何?作者為何道出了難以言喻的故事?那位「第一人稱敘事者」是誰,他們一行人到底去了什麼地方?……
周全
二○一三年八月於台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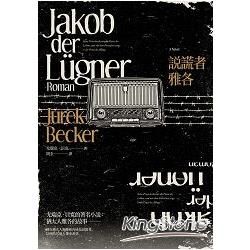

 共
共  2017/11/23
2017/1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