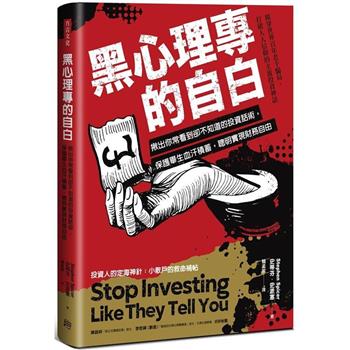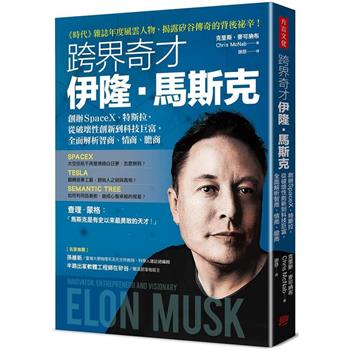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2 項符合
尹遠紅的圖書 |
 |
$ 284 ~ 324 | 仍夢香港島:2011-2024詩選集之續集【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尹遠紅 出版社:初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05-23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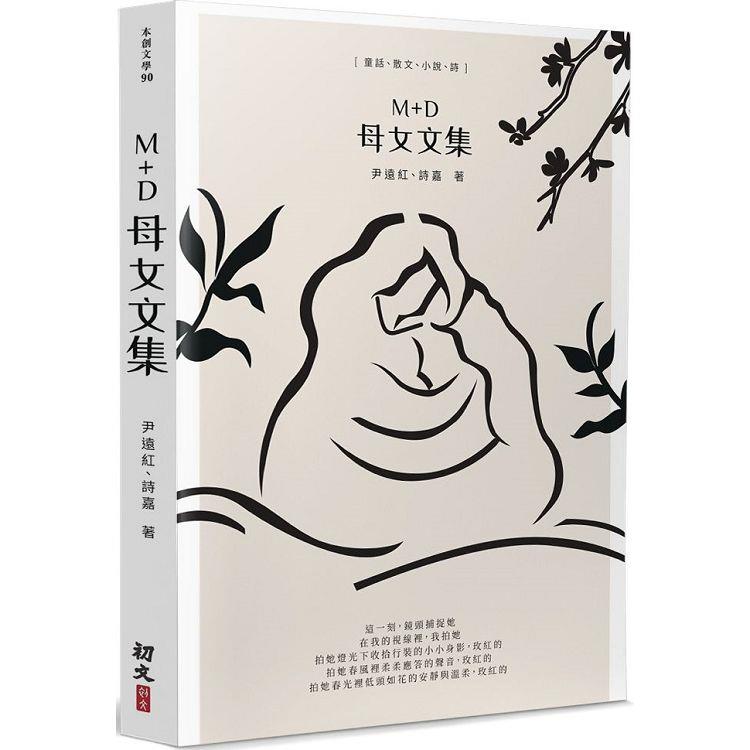 |
$ 316 ~ 360 | M+D母女文集:童話、散文、小說、詩【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尹遠紅、詩嘉 出版社:初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04-26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