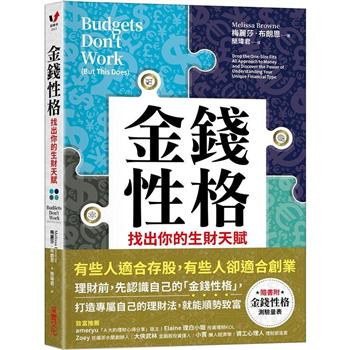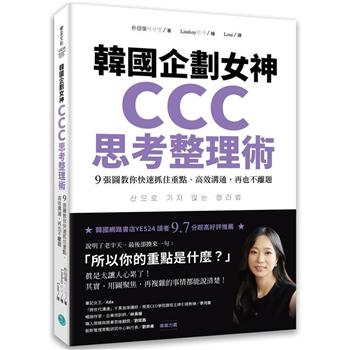找到雙方都有空的日子,定好了下次和女友約會的時間地點。照慣例提早告訴家人要出門。
「甚麼?星期五你要去覆診啊。忘記了嗎?」媽媽馬上提醒。
「……」他真的忘記了。他出事受傷後要定期覆診。不是骨科,手術後覆診兩年就不用回骨科了。他要去的是另一間醫院的遺傳科。事情發生後,檢驗出他骨質形成有些許問題,是媽媽遺傳的,經醫院轉介去兒童醫院遺傳科後,每年都要覆診,直到永遠。
他很少忘記自己的份內事,也許是潛意識不想記起與那場事故有關的一切吧。
媽媽說:「那改期吧。」
「嗯。打電話去醫院改吧。」
「甚麼啊?我是叫你出門改期!」
「不好吧……」
「甚麼不好?有甚麼重要的?我都為你請假了。」
楠不再出聲,讓對話完結。
在媽媽沒注意下,他走到一旁打了一通電話。回頭過來說:「我打了電話去醫院改期了。」
媽媽先是呆了一下,然後說:「你……哼!你還學會了暗渡陳倉、先斬後奏了!」
楠還在想「暗渡陳倉」用得對不對的時候,她已經迅速接受了狀況,言道:「算了吧。那改到了幾時?」
「反正我自己去就好了。」
「不行。我要和你去,你又會忘記的,告訴我。」
「……嗯,下星期三同樣時間。」
楠再「掙扎」一下說:「但我可以自己去。」
「不行,我要聽醫生怎麼說。」
「但你又要請假……」
「不管。」
這段對話一邊進行—或許有點不符合「進行」的感覺,總之對話發生的時候,爸爸和姐姐在旁邊偷笑。楠注意到他們,心想:有人笑,至少多了一點意義。
電話響起訊息傳來的鈴聲。會是誰?他拿出手機看了一眼,原來是遙。因為想嘗試直播唱歌,來向楠尋求歌單的意見。
楠看了他給的列表,覺得非常不錯,其實根本不需要向自己問甚麼。只是當中不乏較高難度的歌曲,遙也正因此猶豫,這些歌曲排列,實在很符合直播效果,而且他也很想唱,只是若不在最佳狀態的話,能唱的信心不大。
「你到時根據狀態再決定唱不唱,不就好了?」楠向朋友提議。
「其實是這樣的,之前觀眾聽過我唱歌之後,說期待我會唱這幾首。我想儘量在這次滿足他們期待。」朋友答覆。
明白了實行的機會很大後,楠邊想,邊輸入回覆:「那好吧。如果你沒太大信心也堅持要唱的話,那你降低別人的期待就好了。先把醜話說在前面,然後有甚麼問題就哈哈大笑著,承認是在預期之內,大家笑笑就好了。取決於你的表現,有可能令大家預期每次直播唱歌都會出事故,甚至變成一個直播中玩笑式的『任務』,那以後都不用緊張了。」
隔了一會兒,遙來訊息:「哈!你是怎麼想出來的?有點意思!」
楠無奈地回應:「這不是原創,你知道的太少了。」最後再加一句:「反正笑你的人多了,就代表看你的人多了。」
朋友猶豫不安的心,只能被殷石楠安定下來。基本上直播會發生的事就這樣定了。
「那就星期五直播吧。」楠看到朋友的這段文字後,迅速反應:「根據你早就公開了的本星期直播時間表,星期五是休息日啊。」
「時間表不用跟那麼足嘛。」
看到朋友這個回覆,楠發送了一個聳肩攤手代表無奈的貼圖。
遙與自己很不一樣,換在以前,自己一定不敢苟同,但慢慢因為遙而接受了原來生活是可以有另一種輕鬆的態度。
「算了。隨便你吧。」他發送。
楠還要告訴遙一件事:「對了,那天直播我不看著沒有問題吧?」
「可以……怎麼了?」
「陪女友。」他傳出後等朋友回覆。縱使實際上朋友是馬上回覆,甚至回覆得還比較快,楠還是有種朋友回覆比剛才隔了更久的感覺。
遙傳來:「你真是……」
「重色輕友?」楠搶著說。
「一個好男友。我想說的是這個。」
星期五到來,出門與女友約會,做了甚麼已經不記得了,因為沒有刻意追求一場要留下深刻印象的約會。
甚至他們都沒怎麼說過話。皆因殷石楠後來越想越覺得要看著遙,結果他一邊約會,一邊拿手機,戴一邊耳機看直播。
當然殷石楠想過女友會不滿意,不過跟女友在一起時,他的眼睛卻看不出這點來。雖然不肯定此舉動有多令人不滿,但殷石楠不怕,因為他認為他們的關係已經去到能容許他任性一點的地步了。他堅持繼續分神看。
有一部分的他,在想像朋友知道他這舉動之後有多意外。
「你太好了吧……」
他回:「不然出了甚麼事我會怪自己的。」
「你……」
「不用感謝我。我是一個自私的人,我這樣是為了自己而已。」他想像到這裏,禁不住展露笑容。雖然遙不會知道,但想像一下,還是沾沾自喜。
上次說不要坐地鐵回家,這次就坐巴士。楠在前頭先上車,帶著女友找兩個座位,靠窗的座位讓給女友,肩並肩坐下。突然他心血來潮,興奮地說:「我有一個關於坐巴士的……見解?想法吧。你想聽不?」
「好啊,你都這麼說了。」
殷石楠以全日最高漲的情緒說:「絕大部分人在上巴士的時候,如果一邊的四座位坐了三個人,另一邊的四座位坐了兩個人,都會選擇坐在兩個人的一邊,也就是少數的那邊。因為人抱著一個原則:你想附近越少人越好。這時候,你以為做了一個100%對的選擇,其實不然。」他整理一下思路,繼續:「因為有可能下個站多人的那一邊,所有人都下車,如果你是坐在那邊,就只剩你一個。也可能之後有人坐在你這邊,另一邊變得更少人……總之環境是會不斷變的。」他帶到自己的結論,手比劃著說:「也就是,其實是一場賭博。不管機率有多大都好,我想說的是,很多人覺得做決定的那一刻是對的,就是絕對正確,但你無法預見的事太多,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連自己賭了一次也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中途換位啊?」Lily搭一句。
「一般很少吧?通常會寧願說服自己接受現狀,也不願意站起來多走兩步,引起別人注意。這就是慣性吧。」
「是嗎?我一般都會隨意換位。我不時見到其他人也會換位。」
「哦……是嗎?」他感到有點尷尬。興致勃勃地分享了一大堆,最後發現原來自己跟他人連這麼小事都如此不同。他沒察覺,心中埋下了反省自己是否對人充滿偏見的種子。只是這棵種子並沒有那麼容易發芽,因為他在對人的看法上可是一塊頑固的石頭。
Lily問了一個似乎藏在心中很久的問題:「你為甚麼不讀哲學?」
楠回答:「當初以為自己想讀商科。反正都讀了,是好是歹,都是一眨眼就畢業。」
「可以轉學系啊。」
「哪有這麼容易。」到此對話結束。說來他確實未試過轉學系。至於為甚麼未試過,可能撇除所有藉口,答案是心底裏他不喜歡改變吧。
Lily看窗外風景。楠一直分神觀察女友,覺得安心,慶幸女朋友願意接受他、聽他說這些。他覺得自己非常幸運,遇到怎樣也願意捧著他的人。
然而他絲毫沒察覺,女友只是別過去冷冷的臉。
這邊直播非常順利,有人稱讚遙唱得好,甚至有幾個人打賞。他看見老觀眾獨孤頭大的打賞,雖然為數不多,但這是第一次在直播時間真的看見這個人出現,還是第一次打賞作為肯定,他心裏有點被觸動,多多感謝了他。
這晚不只唱得盡興,還得到別人肯定,想當然遙十分滿足。雖然殷石楠感到不對勁,不過覺得問題應該不大,原本有話想說,也吞回去了。
誰知,連殷石楠也計錯了。
有觀眾在公開的匿名社群點名批評,那次直播中,遙對打賞金額比較少的觀眾表達了更多的謝意,甚至明顯看出比收到其他觀眾較高額的打賞來得開心,也主動與他有更多的互動。那篇投稿言詞犀利,充滿諷刺和批評,迅速引起人們的注意和討論。
這件事很快傳遍整個圈子—因為這個圈子太小,訊息被傳個兩下,基本上就是大家都知道了。由於涉及與「服務態度」相關問題,事態也不複雜,連平時不太投入這個圈子的人也可以理解。
那是星期日,袁至遙和殷石楠知道消息後第一反應就是:也許世上本沒有公平,但擁有定下公平規則的權力卻不做,現在出問題了,也不算是純粹的不幸。
也就是他們首先責怪自己不妥當—儘管這不一定是事實。
楠想的是,這種事情的發生不算出奇。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其中的人不能毫無敬畏之心,何況現在要順的不是自然,是有意識的人。尤其是這個時代,有人不滿意就能做成很大傷害。
「原來我對你如此緊張,你卻未曾把我放在心上,而且眼中只有別人……」,「我心向明月,明月照溝渠……」心痛的感覺在大腦中的處理與真實的痛楚差不多。也許牽涉情感的工作特別容易出現問題,因為情感才是最容易令人受傷的。
好好控制觀眾的比較和妒忌心態,是很需要智慧的。當然,這是可以被做到的。用貢獻換地位、換尊重、換關係,是正當的—至少這是大家的共識,甚至可以被白紙黑字規定。最重要的是,可以持續地執行。有敏銳的人會好好設計一切,包括每一句該說的話,而他就是不夠敏銳,甚麼也沒有事先聲明和設計,才無意中令人不滿。
楠早有自己一套理論,只是這些想法楠從來沒有說過,沒有為甚麼,只是某些……應該是大部分適合發表長篇大論的時候,他反而喜歡沉默。
但作為關心朋友的人,他計劃總有一天還是會說出來的,只是殷石楠對自己的要求高,總之待他想通之後才說,就變成很多話遲遲沒有說,現在弄成這種情況,他認為自己是有責任的。
這天楠回家之前去了買熟食加餸,帶回來放在桌面上,讓父母覺得奇怪。平時他才不會這樣,應該是有甚麼值得慶祝的事情發生,但看他一臉呆滯,一點也不像好的心情。
媽媽問了:「你這麼想吃嗎?」
「嗯……」楠連張開嘴巴好好說一句也不想。其實他不是想吃,也沒有甚麼其他想法,只是想為別人做一點事情。為任何人,做任何事情也無拘,總之為某人做一點甚麼事情也好。
即使父母再繼續追問下去,他亦根本不能再回答,因為他正任憑一種無法表達的感覺操控身體,那是一種為了心靈上不難受,而使整個人變得麻木,然後隱隱約約覺得想找個人撒嬌,告訴對方自己有多沒用,卻也沒有那麼負面,甚至還帶著一點詩意。非但不會令人察覺自己不妥,甚至挺令人沉迷。只是這個狀態下,雖然他想做一點甚麼事情,但同時沒有動力做任何事情,就是這麼矛盾。他甚至連怎麼回來,到哪間店,買了甚麼都不記得了。
這是最終沉澱後得出來的結果。如果要找一個詞最適合形容沉澱之前那混雜了諸多情緒的他,大概是「愁」吧?
就在要開飯之前,他收到遙發來的訊息:「出來陪我?」
看到後,他馬上準備出門:「我要出去你們自己吃吧。」
「那你買的這些……」
「你們吃吧。」
到了旺角,遙遲到了。殷石楠當然不介意,更多的是擔心。遠處看到朋友走來,走得比平時慢,眼神直勾勾地看著地面,嘴半張,神色明顯憔悴,平時的笑容也消失不見。這是楠在遙面上見過最慘白的樣子。
他來到身邊發了聲:「啊。」
楠回了聲:「嗯。」
兩人到快餐店點了餐點,相對而坐。要開始吃但是食慾不佳,看起來像精挑細選過每條薯條才放入口。楠不想主動提起,但除了這件事,提任何事都更奇怪。結果兩人用餐完畢也未發一語。
楠確認朋友吃完後,打破了沉默:「好好道歉吧。」遙想都不用想,說:「我也這樣打算,只是未準備好。」
楠心裏想,現在是非常適合喝一杯的時候,但他是不喝酒的,而且也不想朋友借酒澆愁。
「去不去喝酒?」遙發問。
「你想去就去吧。」楠只能答應,也只能希望傳聞中酒的魔力能令他舒一點壓。可是他們根本不敢去酒吧,他們在附近找了一間有酒牌的Café。
坐下點了兩支啤酒。遙覺得難喝到面目皺在一起。楠笑著也嘗了嘗,覺得除了苦也就這樣。
「難喝也是好的……把內心的難受分一點到嘴巴。」楠說。遙一口氣喝了半支。不知道是氣氛關係還是酒勁這麼快湊效,遙終於開始抱怨,再多喝兩杯就大發牢騷了,但他怪的不是任何人,他怪的是自己。楠只是靜靜的聽著他把壓力釋放出來,適時努力給點安慰,慢慢地大家的話匣子都打開了。
遙:「為甚麼要比較得到的反應?我不明白。打賞是某種交易嗎?那是不是應該跟他們好好溝通每次交易?會不會有點強人所難?可是我又不知道怎樣做……」
「付出總會想得到回報,每個人關注的還是自己,主要是為了換取關注和存在感吧。畢竟關注是可以值錢的,你的反應代表了這點。不過打賞確實應該有存在感,所以期望靠這樣來刷存在感也正常。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只是不符合預期的話,反應為甚麼這麼大?」
「眼看見其他人都得到的待遇,自己卻沒有得到,確實很令人難受,是我做得不夠好,是我連這麼基本的事情也沒注意。雖然從來沒有人說過這個規矩,可能這是不用特別說,人人都知道的規則吧。花錢就要拿回『應得的』,大家都這樣想吧?」
楠不忍心看著他責怪自己的樣子。
「當感情涉及金錢,是不是就會帶來某種『應得』?這可能足夠我們永遠討論下去。怎樣也好,一般來說,對一個新人應該有點包容吧?而且有所不滿的話,理性地道出自己的不滿,下次不再支持就好。但如果抱有『懲罰別人』的心態,那只會毒害自己,實屬無謂。」
遙依舊垂頭喪氣,說:「但是有甚麼感受,確實可以向大家表達自己的真實情緒。因為我而有的情緒……」
「大家知道真相後,有人同意是有問題的話,選擇和你老死不相往來,最後客觀上你會受到懲罰的。如果一切都是理性的話,那就代表是咎由自取,也不用處理情感。一但加入了『懲罰別人』的自大,那誰能保證你受到的傷害不會超過你真正所應得的?」
楠察覺到自己好像說錯話,突然緊張,加快語速:「我不是說你是咎由自取,應該受懲罰,我只是說在充滿怨恨的人眼中,就算你家破……有再嚴重的後果也都是應得的。正因為主觀是如此不可靠,所以更突出了理性客觀的重要。」
「也對,他用字真的很……為甚麼要這麼惡毒?」
「用了『著色』詞,字裏行間透露出目的是懲罰人,也是個人修為的問題。所謂修為,大概包括可以大條道理地傷害別人時,怎麼選擇吧?其實他的修為如何根本沒有人在意……還是說實在的:他不能接受,還有很多人能夠接受,他傷害你的同時,也損害了無數其他人,這個責任他會不會負?當然不會,因為他只想到自己。」
「負責任」,這也是殷石楠從來不告訴別人自己不開心的原因。他不懂得讓別人開心回來,不負責任的事他不想做,而且事情歸事情,情緒歸情緒,自己情緒自己處理。
何況負能量是留給他自己沉醉其中盡情享受的。
遙說:「嗯……會不會損害其他人我不知道,但對我的傷害真是有的。」
「才不是這樣吧?」楠說。
他們用手機上網看大家的討論。
只是看到的第一條討論已經令他們展開頭腦風暴了。那是替他說話的,不過替他說話的人語氣也不太好,是怪那位觀眾自己甚麼都不知道,不認識那個老觀眾和他做過的事,在這裏小題大做,然後有人反駁,做個觀眾而已,為甚麼要知道這麼多?是不是要自行細數雙方以前做過的事來比較貢獻度?
遙一開始不明白這是甚麼意思,為甚麼會扯上「認識他」和「貢獻度」。但像殷石楠這種心眼多的人一看就明白。人情世故,一要看階級有別;二要看親疏有別,那麼就有「認識那個老觀眾和他做過的事,就自然心服口服」的說法。遙不只不知作何回應好,連作何感想自己也不清楚,只是覺得有人跳出來反駁一點也不出奇。
朋友不知應有何想法,但殷石楠想的可多了。
有件事雖然他早已猜到,但仍然必須問清楚,現在就是機會把一些話跟遙說:「其實你是怎麼看待觀眾的?」
「嗯……我從未試過如此受人重視,也從未試過如此把別人的快樂當做自己的快樂。那種有人對我有期待的感覺,雖然有壓力,但是每次想到觀眾會來看我直播,我都很開心。他們可能已經是我生活的意義。」
遙拿起酒杯,但沒有要喝的意思,就是擺弄一下,分散一下注意,令自己沒那麼尷尬,一邊繼續說:「我是真的把心拿出來交朋友的。」
楠點點頭,他聽到的是他早就知道的事情,他拿出最後的幽默說:「那麼直播就是大型好友交流現場?」
「嗯……算是吧?」
他們都輕輕笑了一笑。遙笑是因為不知還有甚麼好說。楠笑是因為有話還在想怎麼說。
殷石楠說:「你有聽過甚麼是『鄧巴數』嗎?總之心理學說啊,人類的能力只能同時與150人保持人際關係……」楠平時一邊思考時,只會看著人身體說話,而現在他卻正眼看著遙雙眼說:「你知道我想說甚麼了嗎?」
輪到遙把頭微微垂下,停頓了,點了點頭,說:「嗯……不……根本沒有150那麼多人跟我做朋友,就算真的滿了,那麼就會沒有其他觀眾來看我嗎?不會吧?」
楠努力去思考。可以作為根據的只有他自己,但他覺得這就夠了。他相信人人都具備所有人性,那麼觀察自己就可以洞悉所有人性,而他向來特別擅長觀察自己—這點是經過「認證」的。他為了準備將來在辦公室政治中保護自己,看過現代人之外還有縱橫法家和酷吏寫的書,而他從中肯定了自己「推己及人」的能力—因為他早從自己身上了解到人性的弱點和如何把人拖進黑暗,書中寫的對他來說都只是廢話。正因如此,現在他認為自己能看透別人的內心。他對人心有自己一套看法。
「可以有不打算跟你做朋友的觀眾,但是當每個人都對你熱情,不夠熱情的人會認為自己是多餘的;當每個人都是你朋友,不夠熟悉的人會認為自己是多餘的;當每個人都默認了親疏有別,沒有被你看見的人會認為自己是多餘的;當有人能讓你哭、讓你笑、讓你暖心、讓你痛心,自問自己不會是那個人的人……」
他停了一下。心裏想:「他會找到還有最後一個方法在你生命中留下痕跡,就是在你的心捅一刀。」他心中生起一股無名的熾熱,他清楚地意識到不應該,但有時也沉醉在這種感覺。他是理解「寧願做傷你最深的人」和「得不到就毀掉」這些危險心態的人,更是能若無其事走過來,做一下動作毀掉人下半生的那種人。至於決定毀掉人多少,就單純取決於他「自我」的破洞有多大,而他的「自我」偏偏又很容易受傷。所以恰好,他能利用這點,反過來意識到所有危險。但這些話是不能說的,會嚇到朋友,會嚇到所有人。現在表面淡淡地說:「他會想:如果某一天我離開,你也能為我哭就好了,但我配的,只有默默離場,然後被忘記……」
最後這一句也著實搖動了遙的內心,縱使他覺得好像已經不是在討論自己。卑微、受委屈的角色是殷石楠最擅長扮演的。其實他也不想擅長,如果可以的話,他也不想明知有點離題也如此想要說出這句話。
楠話鋒一轉:「階級有別,親疏有別。你說的『朋友』,會考慮『階級高低』來交嗎?是不是看貢獻?身份?利用價值?資歷?你的『親疏』又是怎麼分的?社交嗎?共同經歷嗎?共同愛好嗎?你喜歡怎樣就怎樣嗎?如何能跟你做朋友、提升親密度的渠道甚麼的,應該要說清楚吧?甚麼都模糊不清,唯一清楚的只有別人在意自己在你心目中佔多重分量,比較在你心中排名的位置,那不出事就怪了!你真的要做的話,就好好地做,不要一切都要人『估估下』,不然的話會埋藏很多禍根的。」
很現實。殷石楠在這方面現實到有點可怕。
其實楠知道,與少量觀眾緊密聯繫是完全可以作為一種選擇的,事實上很多人都這樣做。畢竟這樣做下去好處更大也說不定。只是遙沒有想那麼多,默默地走了這條路而又做得不好而已。
但是殷石楠的腦袋一旦進入了「解決問題」模式,思想就變得死板、鑽牛角尖。他說要消除「估估下」,也不是故意要強人所難,只是一心覺得既然是營業的話,就不應有曖昧的地方,也不想想可能曖昧是一切成立的基礎和有趣的部分?說來其實這是殷石楠自己對整個世界的心願。正因為他內心的深淵太大,他認為如果世界儘量淺顯簡單就好了。但很明顯,會怪異很多。
這也說明了他對這個圈子的理解:甚麼都可以發生、只要說清楚就甚麼都能被包容。
楠繼續:「我是想說,如果你自己都搞不清楚,別人更加搞不清楚,那小心會出現不只社交會遇到的煩惱,而且這麼多人,還是以你為中心……社交倦怠這些就不用說了,一旦你稍為展現出差別待遇的話,是不是要人猜測『聖意』,反思怎樣能令你喜歡?如果有人眼看你和其他人更親密而自己不得其法,吃力不討好,沮喪甚至惱羞成怒的話;如果有熟人佔據了其他人跟你互動的空間的話;如果有人自恃跟你熟絡耀武揚威的話;如果有人覺得其他人『不夠份量』與你太親密的話;如果你必須在兩個人中做取捨的話,你有能力把控這些場面嗎?你需要我繼續說下去嗎?再說下去,我可以說到你哭出來,你信不信?」
殷石楠是一個不勇敢的人,他很保守,他想的永遠先從「保護」和「避開危險」出發,而很明顯,在他眼中甚麼都很危險,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危險的人。他說的那些情況都是源於他自己平時會有的想法,而其他人是怎樣,跟他如何不同,其實他不太清楚,但「遠離自己」,就是屬於他的生存之道。其實像他一樣脆弱,同時又忍不住要走出來改變世界的人,沒哪麼多……吧?
遙呆若木雞,毫無回應。其實是他從來沒有以人性的角度想過這些嚇人的情況,被嚇到了。但楠見狀,以為他心中毫無波瀾,繼續說:「再說現實一點的問題,你要儘量取你有限的朋友……」
「不用再說了!我明白了!」遙終於受不了。他已經一秒都不想再思考這些了。
聽完楠看似中立地分析了一大堆,入世未深的遙還未聽出,其實楠並不是中立的。先不說他撇開機率,用最壞後果來嚇人,光是從他選擇說出的都是負面信息,對有甚麼好處隻字不提,理應就知道他的立場其實是不支持朋友繼續走這條路。不過楠確實從未想過扮演中立的角色,畢竟他不相信存在所謂的中立。他認為不可能確保正反方觀點的說服力一致,可能多說一句,想得深一層,他的說服力就偏向一點,那就不算中立了。所以既然他自問自己做不到中立,就不如擺明車馬。
他就是不明白朋友現在需要的,是去了解不同的想法。「儘量」保持中立才是他應該做的。
楠:「如果你自問做不到,就從一開始不要給人任何盼頭。你想不想對自己的路線作改變?」
遙明顯已經動搖得想找東西捉緊,又不知應該捉緊甚麼。遙問:「如果改,可以改成怎樣?」
殷石楠得逞了。不過他確實有他的原因—怎麼會沒有?他做事最講理由—即使是編出來的也好。除了因為他不相信遙能做好這一切之外,更因為即使與具體的人接觸時他是如此冷漠,他這種人還總是想顧及每一個人的感受。他這種心態嚴重到,甚至會忽略這不是他全權負責的範疇。他亦不知道甚麼想法才是多數、其實對大家都最好的關係是怎樣。他就是管得太多,但又不是真的了解別人。也是,他根本不覺得要去了解,只是覺得沒有比他的意思更好的選擇。
但至少他不是個會提出問題令人困惑之後,不負責解答問題的人。
「先不要誤會啊,其實,也有人是抱著凡事隨心做就好的態度,你就有點這樣的態度。但有人隨心,到某些時候就會有某些人不開心。看遇不遇到那些時候和那些會不開心的人而已。當然,也可以選擇不理他們,那些不高興的人自行離開也是正確,但是就要看無法滿足的人佔多少部分,也許有人是因為真性情而被吸引,甚至成為忠實觀眾。無可否認在現在這個圈子裏,有自己特色似乎更重要,反正扮出一副『專業』模樣也不代表能擴闊觀眾群;但在你的個案來說,現階段還是前期要給人留下好印象的階段,可任性的空間可沒那麼多……」他早已經得逞了,這個時候才來扮客觀。
他要開始了。他說:「強調『貢獻度』又會有人反感,光是看『社交能力』又會有人反感,那不特別強調重要性之下,『對貢獻有基本反饋』和『有限度的社交』可以嗎?這應該就是其他VTuber的處理,儘量對每一個人平等就怎樣都錯不了。嗯……是平等還是公平呢?兩者可不一樣。我想說,至少確保任何人為你做了一樣的事都得到基本同樣的待遇,你自己沒有規定的,就預設不能做,一旦做了就要對所有人持續地做……」一邊說,心裏不禁想:為甚麼總會遇上只有很少人會遇上的問題?然後想到自己的人生,不禁嘆了一口氣。
其實他所說的都是非常基本的事情,但「基本」代表「重要」,既然是從頭開始去建立,那殷石楠就想鉅細無遺,畢竟他就是個想一切都盡在掌握的人。
總之他向這個方向為朋友想應該以甚麼原則行事—世事就算再複雜,都只是一條條的原則,像候鳥群能組成千變萬化的陣式,都只是因牠們跟隨幾條簡單的原則。他不斷這樣推下去:「每當這般這般,就這般這般;每當那般那般,就那般那般……」
遙聽著,心裏不是滋味。明明是人與人的交流,現在變成冷冰冰的計算,好像把人變成一種可以擺佈的客體。
殷石楠捕捉到他的情緒,但是不管那麼多,只覺得任何需要苦心經營的事情,都總免不了不近人情的時候,尤其是當涉及金錢,至少公開要這樣表現。俗語說:「慈不掌兵,情不立事,義不理財,善不為官。」殷石楠畢竟是商科出身的,訂這種守則比較適合。
「我還是不覺得……」遙面有難色:「我覺得……不用變……那麼多……」似有話不知怎麼說:「沒有……」
殷石楠說道:「那至少,你應該想儘量避免有人過分關注你的種種舉動吧?你又不是想得特別詳盡的人,讓人有了成為親近你的一份子的盼頭,這可是會為你添上許多你沒想過的期望。這樣的話,對你會是一種壓力,你也不想某一天被一些與你『真正的』直播內容無關的事拖垮你吧?」遙情緒低迷,流露出意有不平,但依然說:「是……比較好……吧?」
「如果他們的支持只是為了鼓勵你繼續這個Project以及純粹的心意,是否簡單很多?首先第一步,你要把自己和這個Project分開一點,才能多一點客觀。這樣也令你減少看待自己所呈現的一切的盲點,才能方方面面塑造風氣,情感、語言、文字複雜得一言難盡。對大局要有意識、操作要有原則,但也只是能確保最基本的運行,不能帶給人最精確的『感覺』。要做到無時無刻、無孔不入地讓人接收到自己想表達、塑造的『感覺』,應先由心態入手……」反正殷石楠自己相信心的重要。
他繼續說:「不是說要完全把自己抽離,只是要比起你現在多分開一點。除了自己對身份的抽離,你和觀眾也要抽離一點,還是那句,不要完全抽離,心與心的連結當然是好的,反而太疏遠的話,他們去看外國的VTuber就好了,我們本地的VTuber就是要較親近一點。建立自己的圈子完全沒有問題,跟接觸更多的大眾一般不衝突,只是,照你這樣順從自己的慣性的話,到某程度就可能無法兼顧……」
遙順著問:「到甚麼程度?」
楠回答:「當融入不了『群體』的人再無法感受到純粹的快樂時;當只有能力滿足你物質需求的人,看不見滿足你情感需求的人需要付出成本時……你真的需要問這個問題嗎?這不是應該從小就知道的事情嗎?」不管對不對,反正這些都是殷石楠現在真心認為的。
「噢……」遙有一絲哀傷,不知道有多少是為殷石楠感到哀傷的。
「至於到底是怎樣、你又要怎樣,我不知道如何告訴你。表演者不能只像表演者,更不能不像表演者。但要再說仔細一點,那就很難……我只能以後看著你,把你往回拉一拉—如果你讓我插手你的事的話。」有些事情雖然楠自問掌握了,但還未想通如何有系統地教人同樣掌握。沒辦法,這就是教人的難處。本來就不容易,更何況現在談的是尺度問題,他又不是孔子,怎麼會有信心把中庸之道教好。
遙說:「我也只能靠你看著我了不是嗎?」
他們都點了點頭,然後雙方都若有所思。
楠正在檢視這次對話,他是如此關注自己的所有「表現」和「成果」。他為朋友想好,安排好一切做法,用盡話術等各種手段確保朋友跟著自己認定的路線走,還可以無時無刻都插手朋友的事—他確實會這樣做。他想起了那個人—自己的媽媽。
沒錯,就是這麼看似無緣無故的一瞬間,他突然驚覺自己不就是比媽媽更過分,一個妥妥的控制狂嗎?而且是把自己看世界的方法強加在別人身上,要把別人變成自己的控制狂。他終於發現這一點了,自己再一次成為了本來以為不會成為的人。
「他不能接受,還有很多人能夠接受……」這是殷石楠說的,而他卻不懂說給自己聽。
但事到如今,也只能這樣下去了。
遙沉下臉,眼半閉,看著檯面。看見朋友這樣子,楠開始怕,如果自己的想法是錯誤的話,會害人不淺,努力檢視自己的想法有沒有問題。他說:「不過其實網友有很多種,定義很廣泛。不用非常親近?某種網友之間也是可以算「朋友」,同時一視同仁,可以多於150人吧?所以也不是叫你拋棄朋友,不用擺出這副樣子。是我太……不靈活、開放……」
「嗯……」遙雖點著頭,但表情並沒好轉。接著說:「只是我不知道還有沒有以後。」
然後遙提到一些「勸退」他繼續做下去的意見。遙顯然是認真考慮過的。他說:「這次事件只是很小的因素,可能加上剛才一些帶給我的觀念上的衝擊,但最重要的還是成績……」
楠趕快說道:「成績不是剛剛開始好起來嗎?」
遙答:「就是因為好了一點我就沾沾自喜,反而提醒了我自己的極限在哪裏。」
遙看著酒杯裏的酒,說:「我實在想像不到自己真正成功的景象。我知道自己差太遠。跟別人比差太遠,跟自己的標準比也差太遠。」
「唉……甚麼叫『真正成功』?又重要嗎?」楠喝了一口,停頓一下後說:「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還來別無事,廬山煙雨浙江潮。」
「甚麼意思?」
「叫你不要……算吧。你有你自己的想法。」
殷石楠現在察覺不到,自己說出了和以前的想法不一樣的話,就算察覺到,他也不會馬上明白是為甚麼。
然後遙全身放鬆,癱在沙發。說道:「也許我不應再發夢了。我一直抱著自己的初衷,但可能從一開始就是錯的,你說呢?」
楠本覺得放棄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但看著現在朋友這樣,只覺不應這樣放棄。「勇者」不應以這種方式倒下。他說道:「初衷就像親人,終會離去,你必須接受但你不能忘記。」遙聽後黯然地說一句:「Sad but true。」接著又喝了一大口。
「不。你不明白我在說甚麼……這樣說吧……」楠放下酒杯,再說:「這是你成長的機會。成長就是不再天真,是由對世界失望開始。努力不一定就成功,正如好人不一定有好報,正義不一定會勝利。但接受這一切,做好現在,面對未來,才是勇氣不是嗎?你現在出道還算短時間,看不到未來很正常。保持希望走下去,以此作為我們的熱血,好不?」
遙停了一會……他微笑一下,然後說:「你這番話,在哪裏抄回來的?」
「抄你個頭。這是很多人的想法,很多人,在很多地方說過類似的話。最多算是被啟發吧。」
遙弄了弄桌面的牙籤盒,斜眼看楠說:「但我覺得你說得最好。」他笑了。殷石楠也笑了。
殷石楠覺得自己安慰人並沒有如此大的進步,其實只是朋友想要有人來肯定一下而已。
有很多事情,只能接受可能永遠無法達到,而儘量去做。包括他現在的安慰也一樣。惆悵,痛苦,沒有誰的鏡像神經元能安慰;沒有人能真正理解另一個人,但是儘量去做,還是有意義的……想到這裏,殷石楠突然起了雞皮疙瘩。他有如自己打了自己一巴掌,有些頑固的地方被打通了。
楠很快回過神來,向遙問:「話說你的初衷是甚麼?」
「哼嗯……」遙稍稍抬了抬頭,露出了楠想不起有見過的眼神,從眼神中看到的,是有些懷念,有些感觸。
「天邊那平凡、暗淡的星,也能是宇宙另一邊某人的太陽。」遙空虛的手去擺弄著酒杯,看著搖曳的酒,微笑道:「也許我變得越來越像你了。」
楠也微笑了一下,輕點一下頭。然後又再收起了笑容:「不……並沒有。」
「你這個有夢想的人,怎麼會像我。」
楠也連斟好幾杯。到這份上,陪朋友喝不只是一種責任,也是自我抒發。他確實不乏傷心和內疚。幾杯下肚後,後來的事就只剩下模糊的記憶了。
一晚過去。楠在一張與平時不同的床上醒來。他半睜著眼看到左邊的房門上掛著的一幅掛畫,馬上清楚這裏是遙的房間。遙停看手上的漫畫,從書桌轉頭說:「你終於醒了。昨晚你的媽媽打電話給你,我替你接了。我如實說你喝醉了,你在我這裏。」
家人知道遙是一個可靠的人。殷石楠早就談及過朋友的事—儘管他是那麼不愛分享。總之家人們似乎因為他有這個朋友而放下了很多憂慮。而且這並不是第一次在朋友家留宿。話雖如此,放任喝醉的兒子打擾別人還是有點奇怪。
「他們不來接我?」
「我說不用的。我本來想等你醒了,我們再聊點甚麼。不過現在不用了,我想明白了。」
「你可以靠自己想明白事情的嗎?」
「仆啦你。」
「嘻嘻……哈哈哈哈……」兩個人相顧而笑。
楠努力回想,只依稀記得昨晚好像有女生過來,不知是搭訕還是關心他們,然後被自己趕走了。除此之外沒有對任何事情留下印象。他沒想到自己比遙更早醉,遙也沒有嘗試到酩酊大醉的感覺,甚至如果真的有女生來搭訕,可能他還阻礙了一些重要事情發生。他懷著極不好意思的心情說:「本來是要讓你抒發的……今晚買酒回來?大家都可以醉。」
「不要了。」遙想了一下後說:「話說昨晚你罵老闆娘超好笑。沒想到你喝醉酒後是這麼放飛自我的。」
「……原來昨晚的是老闆娘啊……我要去道歉了。話說怎麼會好笑?」
「你說了一大堆很亂七八糟的詩詞還是成語,無人知道是甚麼意思。老闆娘都笑了。」楠背了過去,遮著因尷尬而紅透了的臉。
他轉回來說:「那……昨晚不好意思……」
「不用太內疚,喝醉之後做甚麼也不是你能控制的。」
「我又未去到內疚的程度……總之麻煩你了。」
「無所謂啦。朋友之間本來就是你麻煩我,我麻煩你啦。」
「嗯……」
「說起來這好像是第一次我能為你做些甚麼。你從來都不麻煩我。」
「……」
殷石楠又再陷入思考。
「你在想甚麼?」遙問。
楠嘴上跟他說:「那你決定怎樣做?」
「開個直播道歉吧。就明晚。」
「好,你需要我跟你一起寫道歉稿嗎?」
「其實我都大概想好了,只是未寫,想到咖啡館寫。你想現在聽一聽嗎?」
楠直接回答:「其實我今天是約了女朋友的……」
「是啊……」
然後楠馬上說:「明天早上可以。」
「明天早上是指過了今晚十二點嗎?」遙不知是真問還是假問。楠苦笑著說:「那是凌晨……」
「哦……那深夜呢?深夜和凌晨怎麼分?」
「……」楠無奈地說:「話說你這不是知道不算早上嗎?那就一於今晚十二點跟你通話?」
「好啊……是今晚十二點還是明天十二點?」
「……」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展略的圖書 |
 |
$ 284 ~ 324 | 庸人【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展略 出版社:青森文化(紅出版集團) 出版日期:2024-07-01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庸人
現實世界 × 虛擬世界
親人,友人,愛人,陌生人,熟悉的陌生人……人生在世離不開各種人。這是一個長不大的少年被扔進這世界的故事。
學不到家的心理學、哲學、佛學、偏頗的觀察、一顆偽善的心……可以幫他渡過生離死別和VTuber世界裏的碰撞嗎?
徘徊在現實和虛擬之間,一個不斷尋覓自我的少年人,面對一生浮沉、家人的生與死,何以自處?
一個敏感又內耗的人,最終會蛻變成甚麼?
章節試閱
找到雙方都有空的日子,定好了下次和女友約會的時間地點。照慣例提早告訴家人要出門。
「甚麼?星期五你要去覆診啊。忘記了嗎?」媽媽馬上提醒。
「……」他真的忘記了。他出事受傷後要定期覆診。不是骨科,手術後覆診兩年就不用回骨科了。他要去的是另一間醫院的遺傳科。事情發生後,檢驗出他骨質形成有些許問題,是媽媽遺傳的,經醫院轉介去兒童醫院遺傳科後,每年都要覆診,直到永遠。
他很少忘記自己的份內事,也許是潛意識不想記起與那場事故有關的一切吧。
媽媽說:「那改期吧。」
「嗯。打電話去醫院改吧。」
「甚麼啊?我是叫你出...
「甚麼?星期五你要去覆診啊。忘記了嗎?」媽媽馬上提醒。
「……」他真的忘記了。他出事受傷後要定期覆診。不是骨科,手術後覆診兩年就不用回骨科了。他要去的是另一間醫院的遺傳科。事情發生後,檢驗出他骨質形成有些許問題,是媽媽遺傳的,經醫院轉介去兒童醫院遺傳科後,每年都要覆診,直到永遠。
他很少忘記自己的份內事,也許是潛意識不想記起與那場事故有關的一切吧。
媽媽說:「那改期吧。」
「嗯。打電話去醫院改吧。」
「甚麼啊?我是叫你出...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前言
不是說道理,而是借「道理」說人。
您了解一下角色的內心和思維模式就好了。
我也不知道甚麼是應該的,甚麼是不應該的。
我只是拿「觀點」當「工具」。
還有,本故事純屬虛構。
展略
不是說道理,而是借「道理」說人。
您了解一下角色的內心和思維模式就好了。
我也不知道甚麼是應該的,甚麼是不應該的。
我只是拿「觀點」當「工具」。
還有,本故事純屬虛構。
展略
目錄
第一章:世上本無事 庸人自擾之
第二章:世上本無事?庸人本無擾
第三章:世上滿世事 庸人當自擾
第四章:世界即世事 庸人皆世人
第五章:不見自擾不自擾 只見世事與世人
第二章:世上本無事?庸人本無擾
第三章:世上滿世事 庸人當自擾
第四章:世界即世事 庸人皆世人
第五章:不見自擾不自擾 只見世事與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