媲美CSI犯罪現場,偵破命案的關鍵
法醫出現場及解剖實錄
每當重大命案發生時,法醫的抽絲剝繭、絲絲入扣地在現場分析推敲,經檢驗後證實分析,往往在破案中發揮關鍵性作用。
法醫是個與死亡打交道的行當,但主要是與非正常死亡打交道,在非正常死亡中又主要與殺人或傷人致死打交道,當然自殺和事故也時常需要法醫去澄清事實,查明真相,甄別真偽。
作者從警三十一年來,無論是做法醫,出現場,破命案,還是當國際刑警,都盡全力去發現各種案件的蛛絲馬跡,本書詳述其成為法醫的心路歷程。
從初入法醫「單飛」辦案到中國發生的大官之死命案、大型空難等事件;國際刑警組織總祕書處工作實錄——愛爾蘭史上極為罕見和兇殘的兇殺案、英國莫克姆海灣慘案等,跨國協助辦案,參與許多震驚中外的重要案件和空難事故的偵查及調查工作。細膩詳實的描繪,親臨現場般的真實;逐一檢驗再檢驗,實驗各種可能性,直到得出結論,偵破命案。
在法醫的眼裡,現場的屍體不是單純的死人,而是一個重要的物證,破案全靠他或她了。法醫面對屍體時,一大堆問題撲面而來,這人是怎麼死的,什麼時間死的,臨死前的情形是怎樣,死亡的性質是什麼,致死的工具是什麼,身上的傷是怎樣形成的,自己能形成這樣的傷嗎,現場上有沒有搏鬥,激烈不激烈,兇手是幾個人,有沒有可能受傷,是熟人作案還是生人偶遇,現場有可能留下什麼物證等等,回答不出這些問題,案子就沒有辦法破,在破案的壓力面前,法醫哪裡有時間和精力去「害怕」呢。
法醫辦理死亡案件的關鍵是要弄清楚死亡的性質,是被殺的千萬不能錯定成自殺或事故,否則就會放縱犯罪,令案犯逍遙法外。今後這個案犯不再作案便罷,如果再作案或者是其他什麼原因使案件暴露出來,案犯被抓後交代說,哪個案子也是我幹的,就會發現法醫當初定錯了,那就是造成了錯案,這個法醫就很難在這個行當裡「混」下去了。案件當中匕首捅、菜刀砍、斧錘敲、棍棒打、磚石砸、繩子勒、開槍射的,損傷明顯,一目了然的好辦,一些體表損傷微小的,如電擊,甚至是體表根本就沒有什麼損傷的,如投毒,就要特別當心了,不是有投毒的案子十幾年、幾十年都破不了嗎?
最要警惕的是把兇殺偽裝成自殺或是意外事故的。有個案子,夫妻倆一同睡覺,夜間發生煤氣中毒,女的死了,男的活了。我們接到這個案子時感到有點奇怪,因為一般來說,男的呼吸深,吸入毒氣多,女的呼吸淺,吸入的少,從生理上說,男的耐受力差,女的耐受力強,所以同樣條件下,男性更容易因煤氣中毒死亡,可是這個案子男的活了,女的卻死了,這是怎麼回事,是例外嗎?法醫辦案就是先要順著正常的思路和最常見的情況和現象去找,一旦出現異常,又沒有合理的解釋,往往就是有了問題。
睡在同一房間中夫妻兩人都應該中毒,就算是男的命大,僥倖活下來,也應該是重度煤氣中毒的樣子,頭暈噁心,嗜睡萎靡,語無倫次,失去記憶,甚至呆傻,可是這位男士沒有明顯中毒跡象,思維正常,語言清晰,對答如流。只是發現他與我們交談時,時常咳痰,痰的顏色是黑的,再仔細看,他鼻子、鼻孔和口唇都有些發黑,這又是怎麼回事,煤氣中毒沒有見過這樣的。
現場雙人床的枕頭旁就是煤爐,爐子上有煙囪直通屋外,爐子連接煙囪部位的炭灰有擦蹭跡象,男的睡在靠近爐子這一側,枕頭和被上也有少許不易察覺的黑色痕跡,我們有了一個大膽的假設。我們說,他總咳黑痰可不好,我們對他負責,幫他檢查一下,就把他送到了醫院,聯繫呼吸科的大夫對他進行了氣管纖維鏡檢查,發現他的氣管裡、支氣管裡有許多黑色物質,取出來放在顯微鏡下觀察,就是黑色炭末。經過審訊,他供述,他與妻子感情破裂後,妻子死活不離婚,只得想出這麼個辦法。
晚上他把煙囪從爐子上拔下來,罩在自己的口鼻上,當煤氣在屋裡蔓延開來時,他能通過煙囪呼吸,可憐他的妻子就中毒身亡了,煙囪中的大量炭灰被他吸進了肺裡,竟成了殺人證據。
反過來,如果把自殺或事故錯定成被殺,最後頂多是破不了案,抓不到人,公安人員白忙一場,但不會對社會造成大的危害。當然,把命案錯定成自殺和把自殺錯定成命案都不應該,法醫只要把案件性質定準確了,一般就不會發生大的差錯。
作者簡介:
左芷津
1954年出生,二級警監。1978年考入北京第二醫學院,畢業後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1986年在廣州中山醫科大學攻讀碩士、博士,1991年獲醫學博士學位,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博士警察。
1991年任北京市公安局刑偵處法醫室副主任;1992年調至公安部刑偵局工作;2000年被派駐法國里昂國際刑警組織總秘書處工作;2004年任北京市公安局刑偵總隊副總隊長;2007年任北京人民警察學院院長。2010年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助理。先後榮獲全國優秀人民警察、「第二屆全國我最喜愛的十大人民警察」、全國公安系統二級英雄模範等榮譽稱號。被中山大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聘為客座教授,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貢獻津貼。
章節試閱
無心插柳
我考大學時,一開始並不想學醫,我到農村當知青時,曾經種過地,受夠了風雲突變、疾風暴雨的摧殘,所以我特別想學氣象,幻想著知風雨、曉陰晴的本領,甚至還打聽到南京有一所著名的氣象學院,後來一同下過鄉的朋友們說,不要以為學了氣象就能在城市裡鼓搗天氣預報,給你分配到一座大山頂上天天看雲雨,測風向,記資料,雖說有老婆陪著,但一幹就是幾十年,也是說不準的事。我還想學建築,也是因為剛到農村時自己蓋過房子,後來朋友們勸我,蓋房子總要跑工地,也是個辛苦差事,再說有建築專業的學校都是特棒的學校,也就特別難考,像我們這樣,初中只上了一年就畢業下鄉勞動的,有個學上就不錯了,哪裡敢像應屆高中生似的,報志願像到飯館裡點菜一樣,想要哪個就要哪個。
一番胡思亂想之後,把醫學拉入了視野,想到學醫也不錯,不像在工廠裡和鐵塊打交道,你讓它方,上銑床它就變方了,你讓它圓,上車床它就變圓了,醫生面對的是病人,正合我喜歡和人打交道的性格,於是考了醫學院,夢想著掛聽診器拿手術刀的日子。
誰知等進了醫學院才明白,醫學生要讀五年,每年光考試課就有六、七門,五年加起來磚頭厚的書要讀進去三十五、六本,人身體上有什麼,長在哪兒,長成什麼樣都不是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只得硬著頭皮背,因此學醫沒有任何創造性,這就是我們醫學生面臨的窘境。
學醫是與人打交道,醫學生漫長的校園生活也就有了不同於其他學科的許多有趣事情,好玩得很。大二下學期開學時正值冬天,課程進入學習聽診階段。一天,老師說,今天收了個風濕性心臟病,二尖瓣狹窄合併關閉不全,雜音很典型,大家可以去聽聽。同學們聽罷,如狼似虎地一窩蜂衝到這個病人面前,瞬間九個聽診器一下子全都按在了病人瘦骨伶仃的胸前,把個病人冷得直激靈。後來為了避免這種現象,發明了一種專門教學用的聽診器,一端是一個聽診器頭,按在病人身上,另一端分成九個聽筒,可以有九個同學同時聽,想法很好,但實際用起來就不是這麼回事了。這個聽診器像個大章魚,無論是拿起還是放下,十隻「觸角」相互纏繞在一起,亂成一團,拆都拆不開,根本沒辦法用,最後老師只得強調只許一個一個去聽,一個病人最多三個學生去聽。
醫學院的學習時間長,前面兩年半在學校學習,後面的兩年半全部是在醫院先見習,後實習。記得大家輪轉到婦產科實習時,老師指著門口「男賓止步」的牌子說,你們男生要特別珍惜這個機會,很可能你們這輩子當醫生只有這一次能進到這個門裡面。聽到這話,女生們不以為然,男生們全都認真起來,絕不放過任何一個接生助產的機會。一天深夜,一位趙姓同學正在醫生休息室裡睡得迷迷糊糊,突然護士大喊,趙大夫,來接生。趙同學一骨碌從床上竄起來,抓起白大衣就往產房跑,邊跑邊穿白大衣,從醫生休息室到產房有五十多米的距離,怎麼也找不到白大衣的袖子,直到產房門口也沒能把白大衣穿上身,進了產房才發現,原來他抓的根本不是白大衣,而是床上的白布單。這些糗事在醫學院裡特別多,大家也因為太熟悉,彼此失去了神祕感,五年下來,同學間竟沒有男女生談上戀愛的,畢業後成功了的兩對夫妻,則是離開學校以後感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裡面的世界很無奈」才成的。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學校圖書館看到一本棕褐色封皮的精裝書─《實用法醫學》,隨手翻翻,看看裡面的照片,覺得挺有意思。我們是醫療系的學生,內、外、婦、兒是主課,學的就是當醫生給人治病,課堂上講的都是人得病的種種情況,然後教我們如何千方百計地把病人給救活,課堂上老師最多也就是講到病人臨死前的搶救,像心裡注射、心外按摩、氣管插管、加壓給氧、電擊除顫什麼的,從來沒講過人死了以後是怎麼回事,會變成什麼樣。對大夫來說,人死了,殮房的師傅把人推走,從那個生死的時間節點開始,以後就不再是他們的事了。
看了《實用法醫學》才知道,人死了以後,由於面部肌肉的鬆弛,是眼微睜口微開,一副放鬆解脫的樣子,並不是口眼緊閉、眉頭緊鎖,一臉受苦落難的表情,當然也沒有怒目圓睜的。面部肌肉的鬆弛還使臉上的皺紋變得平坦,因此老年人死後顯得年輕。年輕人死後顯得老,是因為臉上失去了年輕人的活力和光澤,活力是人最重要的生命表象,所以大多數人參加遺體告別時,總會感到死者變化很大,明顯不像生前,以為是遭了多大罪,其實是沒有了活力。
人死後由於體內一系列複雜的生物化學變化,全身肌肉會變硬,使各個關節僵硬固定,無法活動,這叫屍僵。屍僵可以把臨死前的姿勢保留下來,法醫檢驗時可以從姿勢推測臨死前的情況。屍僵經過一段時間,隨著人體逐漸進入腐敗,會慢慢地緩解,透過屍僵的變化,法醫可以推測出死後經過時間。
人死後血液循環停止,血液下墜,沉積在身體低下的、不受壓迫的部位,血液的顏色透過皮膚,使得皮膚呈現暗紫色,這叫屍斑。一般人都不知道人死後皮膚顏色的變化,在一些意外發生的死亡中,死者家屬常常把這種暗紫色的屍斑誤認為是「遍體鱗傷」。
在大學裡翻看這本書也就是圖個新鮮,根本沒有想到這輩子會跟法醫結緣。
正式入行
一九七八年我們考大學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編按:即大學聯考)的第二年,第一年時人們還沒有完全從「文革」中甦醒,幾乎只有那些受過「文革」前正規中學教育的老三屆高中生手拿把攥地考進大學。等到第二年高考時,人們對新社會的信任和通過個人努力改變命運,追求新生活的期待,已經提高到「非大學不上」的熱度,魚龍混雜的龐大考生隊伍,使得錄取比例竟然達到了二十五比一。
我們入學時文革剛結束不久,對政治鬥爭的厭倦和對逝去時光的緊迫感,使學校裡特別崇尚學習,每年評選三好學生就一個條件,學年考試成績平均在九十分以上的就是三好學生,不用評也不用選,一般一個班也就是三、四個。三好學生的獎品也很實惠,就是下個學年的全部課本。我們班裡幾個歲數大的,學習上特別努力。
一九八三年大學畢業時,國家還處於計畫經濟時代,學校負責統一分配,先公布一個分配方案,上面全是需要人的單位,每個學生自己先挑願意去的地方,填寫志願後,再由學校統一安排和調劑。當時對優秀畢業生的政策是,如果能連續三年當上三好學生,畢業時想去哪個單位,只要是分配方案裡有的,隨便挑。只可惜,我是連續兩年的三好學生,差一年就能隨便挑了,原因是有一年體育課沒考好,拖了後腿,各科平均下來是八十九點四分,四捨五入不夠九十分。學校知道我成績好,還擔任過班裡的學習委員和班長,也想幫幫我,就徵求我的意見想去哪裡。
當時的醫學畢業生大都想搞科研工作,爭著留校,或者是到科研單位工作,也不懂得幹臨床、當醫生最吃香,當然當時也沒有「醫鬧」(編按:類似醫療糾紛的情況)和臨床醫生屢受人身侵害的案件。我看到分配方案中除了各個醫院或醫學科研單位外,竟然有北京市公安局,一問才得知是北京市公安局來學校招人去做法醫,條件是三個:一是男的,二是不戴眼鏡,三是三十歲以下,看看自己渾身上下,這三條我都合適,就報了名。
學校知道後也支持我去那裡工作。其實我對公安局並不瞭解,家裡祖祖輩輩從來都沒有人當過警察,倒是學校的保衛科長比較熟悉,他主動跑來眉飛色舞又神祕兮兮地向我介紹,說我要去的地方號稱「天下第一科」,藏龍臥虎,神通廣大,威力無邊,可是不得了。我半信半疑默不作聲地看著他,心想,這位保衛科長在學校裡是出了名的厲害,平時他根本不把我們這些學生放在眼裡,橫眉立目、吆五喝六地可橫了,老師和學生沒有不怕他的,現在突然對我這樣關心、和藹,隱隱感到這個單位確實不一般。
當警察的要求比當醫生嚴多了,需要面試,看一看身高、相貌、眼歪不歪、嘴斜不斜、站不站得直、走不走得正,總之,言談舉止適不適合當警察。北京市公安局的法醫老前輩莊明潔科長帶領著年富力強的中年法醫任嘉誠來我家面試。
嘉誠板著面孔,一進門先倒出一堆法醫工作如何辛苦之類的話來。我心想,俗話說,「醜話說在前頭」就是這個意思吧。我明確回答道,咱也是上山下鄉、工廠農村幹過來了,還能在乎這個。聽我回答得這樣簡單乾脆,根本不像假裝的,氣氛頓時緩和了許多。接著嘉誠又隨便問了一些家裡人的其他情況,面試不長時間就結束了。人就是這樣,對不對緣,幾句話一碰就清楚了。他們走後,我估摸著,歲數大、不吱聲的應該是司機,年輕一些、總問我話的可能是科長。後來才知道,正好相反,原來他們早在門外約好,嘉誠負責問話,莊老在旁靜觀,不得不敬佩薑還是老的辣啊!
此後,我順利進入北京市公安局刑偵處技術科,算是正式加入了法醫隊伍。任嘉誠成了我的良師益友,據說當年他剛出門就說,「這個人咱要定了。」人家慧眼是不假,只是不敢說是識珠,最起碼也算是百裡挑一。而且他入黨四十餘年,前前後後只介紹過我一個人入黨,是他的關愛,更是我的榮幸。
當上法醫後的第一次解剖屍體就是任嘉誠老師帶我的。我們是文革後第一批進入北京市公安局當法醫的大學畢業生,老法醫們認為我們是正規醫學院出來的,一定都會幹解剖,其實我們只是在大一和大二時上過人體解剖課,自己根本沒有動手解剖過屍體。任老師換上隔離服,已經站在解剖台的主刀一邊了,我只好硬著頭皮站在了另一邊。我靈機一動,只見老師用解剖刀拉一下,我就用解剖刀拉一下,反正是他拉哪裡,我就拉哪裡,加上醫學院裡學解剖的功底,一台解剖做下來,老師居然沒有看出破綻,讓我挺高興,這麼緊緊張張地開始幹的法醫,哪裡還顧得上害怕死人。
真正當上法醫,幹了一段時間後,逐漸認識到法醫與原來學的醫生大不相同。醫生每天坐在醫院裡,病人來了可以直接問他,你怎麼不好了?病人會告訴醫生說,昨兒晚上著冷了,或是昨天吃了什麼東西不合適了,或是過去的什麼老毛病又犯了。醫生一下子就能把生病的原因找到,從原因就能導出結果,就知道病人發展下去將會是個什麼結局,醫生的本事就是要用醫療手段阻止病情惡化,也就是阻止結果的發生,所以治病救人是一個由因導果的正向思維過程。法醫就不同了,法醫到現場時人已經死了,結果已經出來了,需要法醫從結果出發,搜尋各種物證,解讀物證背後的現象,推測勾勒出案事件的輪廓,逆向推導出原因來,這種由果導因的反向思維過程具有極大的挑戰性,使我逐漸迷上了法醫。
「單飛」辦案
當法醫的往往對自己第一次單獨出現場辦案記憶猶新,借用人家飛行員的叫法,也叫作「放單飛」。
一般情況下,一個學法醫專業或是學醫學專業的大學畢業生,從跨入法醫行當開始到能夠「單飛」,怎麼也要跟著老法醫幹個二、三年的時間,因為「單飛」的標準是要能夠應付一般的死亡案子,也就是說,比較常見的死人案子都能應付得了。之所以需要這麼久,是因為得經過一定的時間,才有足夠多的機會把各種常見的死亡案件都見過、處理過,時間短了,見不了那麼多案子,以後真的遇上了難免手忙腳亂。
我也照例先跟著老法醫們學習了一段時間,後來去中國刑警學院進修了十個月,回來後,再跟著老法醫跑前跑後,直到一九八五年二月七日,終於放了「單飛」。這個「單飛」說簡單也簡單,說複雜還真是不容易。
那是北京一個冬末春初陽光明媚的下午,技術科樓道裡的廣播喇叭傳來值班人員「法醫、照相出現場!」的呼喊聲。無論春夏秋冬,無論白天黑夜,這個喇叭的喊聲就是命令,特別是當值班人員打開擴音器的電源,喇叭裡傳出來沙沙的電磁聲,但又沒有開始喊話時,樓裡各專業的技術人員都在屏息靜聽,不知道是什麼現場,有沒有自己的事。
無論什麼案件,只要聽到廣播喊聲,照相人員是必須去的,因為任何現場,拍照記錄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只通知照相和痕跡人員去,沒有法醫的事,估計一定是盜竊現場;如果通知照相和痕跡人員,再加上法醫一同去,就一定有人的事了,十有八九是個命案現場,要是再加上錄影人員,就一定是特別重大的命案現場,那時候條件差,不是每個現場都要錄影;要是再加上爆炸工程師,就一定是爆炸死亡案件;如果只通知照相加上法醫去,往往是非正常死亡的案子,多是意外,現場沒有犯罪痕跡可看;但是如果遇到跳樓、臥軌之類的自殺案子,痕跡人員也必須到現場甄別是自殺還是他殺。
這天是我值班,法醫室的晨會上,主任說了,左來了也有一段時間了,學得、練得差不多了,再有一般的現場就「單飛」吧。對任何一名法醫來說,聽到這話就像學徒要出師了一樣,既興奮又激動,當然,心中也在默默地祈禱:第一次「單飛」,可千萬給我來個容易點兒的案子。
聽到廣播通知,我拎著早已準備好的全套法醫器械來到樓下大廳,到值班室拿了《情況簡報》,幾個老法醫湊到值班室來看看是怎麼回事。死者名叫英勝利,是位女性,二十九歲,今天下午發現死在家中,因為死因不明,西城公安分局請求市公安局法醫支援。幾個老法醫一合計,對我說,你自己去吧。我心中暗暗一陣高興,終於讓我「單飛」了,可是嘴上仍說,還是您帶我去吧,請老師們多給把把關。老法醫說,有什麼問題回來再研究,便把我一個人扔在大廳裡了。照相室值班的是英武帥氣的小韓,我們兩人一起,再叫上兩個正在我們這裡實習法醫的學生當幫手,一行四個人就登車出發了。
到了分局,治安科主辦的民警介紹說,死者英勝利二十九歲還沒結婚。在上個世紀八○年代,雖然還沒有「剩女」一說,可這麼大的姑娘還沒有結婚出嫁,可真變成爹媽的一塊心病,家裡為了這個老姑娘的婚事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弄得雞犬不寧。這樣的家庭環境肯定是待不下去了,這位姑娘就在距離她家不遠的新街口租了一間平房,自己搬出去住了。
出事的這天早上,英姑娘沒有去上班。到了下午,單位發現她還沒有來,就派人到她家去找,家裡人說她一個人在外面住。單位同事和她的家人一同來到英姑娘住的地方,只見房門緊鎖,破門進去後,發現英姑娘已經在自己的床上氣絕身亡。單位同事驚恐之餘,連忙報警,西城公安分局治安科的警察很快就趕到了,向鄰居們瞭解情況得知,昨天晚上似乎有人從這個女孩子住房的後窗朝屋裡望了一下,女大未婚,離家單住,不明人士,深夜偷窺,突然死亡,原因不明,被害的可能陡然增加。我這個剛「放單飛」的法醫不怕事大,就怕事小,立即提高了警惕。
瞭解了大概的情況,我們趕到存放屍體的積水潭醫院太平間,從冰櫃裡拖出英勝利的屍體,這屍體既不是七竅出血,也不是傷痕累累,安詳地如同睡著了一樣,也對,人家不正是一個人死在床上嗎?我先按常規做了體表檢驗,結果不要說是沒有見到致命性損傷,就連一點點微小的損傷也沒有。
沒有發現損傷,我腦子裡的法醫想法全出來了,生怕漏掉了什麼。二月的北京天氣還是比較冷的,可不可能是煤氣中毒,剛才在她的住處看到了爐子,煤氣中毒的屍斑是櫻桃紅色的,我特別觀察了屍斑的顏色,感覺顏色不夠紅。是不是注射毒針死的,針眼小可不好找,千萬別漏了,我在她全身上下仔細找了好幾遍,沒有發現。會不會是電擊死的,電擊部位形成的微小電流斑也不好找,一定要特別注意,我把英勝利身上犄角旮旯,特別是有毛髮覆蓋的部位,都查看了,沒有見到。床上死的,能不能是被枕頭這類柔軟的東西捺壓口鼻摀死的,這種情況有時皮膚外表沒有損傷,但口腔內側的黏膜在牙齒的硌墊下,會有破損,要翻開嘴巴去看,我看到口腔黏膜光滑平整,什麼都沒有。
無心插柳
我考大學時,一開始並不想學醫,我到農村當知青時,曾經種過地,受夠了風雲突變、疾風暴雨的摧殘,所以我特別想學氣象,幻想著知風雨、曉陰晴的本領,甚至還打聽到南京有一所著名的氣象學院,後來一同下過鄉的朋友們說,不要以為學了氣象就能在城市裡鼓搗天氣預報,給你分配到一座大山頂上天天看雲雨,測風向,記資料,雖說有老婆陪著,但一幹就是幾十年,也是說不準的事。我還想學建築,也是因為剛到農村時自己蓋過房子,後來朋友們勸我,蓋房子總要跑工地,也是個辛苦差事,再說有建築專業的學校都是特棒的學校,也就特別難考...
目錄
入道法醫
初辦命案
貪官末日
將門無力
空難人寰
法國瑣事
我與「九一一」
都柏林泣血
海灣悲情
黑白鴛鴦
轉身時刻
兩傳聖火
奧運育人
入道法醫
初辦命案
貪官末日
將門無力
空難人寰
法國瑣事
我與「九一一」
都柏林泣血
海灣悲情
黑白鴛鴦
轉身時刻
兩傳聖火
奧運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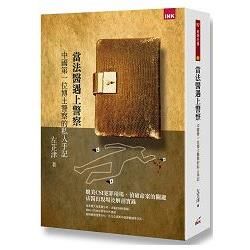
 共 10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0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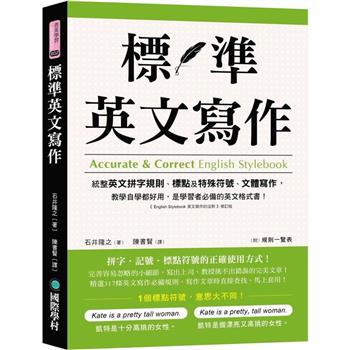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