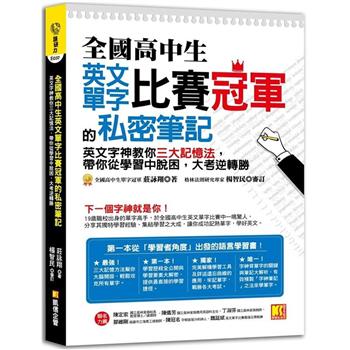我叫山姆‧包西佛,就是那個不小心燒掉艾蜜莉‧狄金生彍在美國麻州安默斯特的房子,還因此意外殺了兩個人的縱火犯。為了這宗意外案件,我吃了十年牢飯,而根據美國文學學者的來信,我將為此付出長久的代價,承受不大美好的後果。我的故事在當地無人不知,在此就不多做交代。
出獄回家後,我和父母住在一起,但搬回家和父母同住並不是很順利。其中一個理由,是我燒掉了艾蜜莉‧狄金生的房子,讓身為高中英文老師的媽媽和當地大學出版社編輯的爸爸傷透了心。美麗的文字對他們來說的確非常重要,他們從不關心電影或電視,但只要一些優雅的字句,便能讓他們陷入感動或是發出深深的嘆息。另一個原因,是安默斯特的居民很不高興我燒掉地方名宅,附加斷送鎮上兩條人命,所以拿我父母出氣。沒有人找不到我家位在奇科皮街上、可以聽見木材喀喀作響的老房子,因為車道上總是被油漆噴寫著「殺人犯!」(這個我可以理解),或是「法西斯主義!」(這我就不明白為什麼了),或是直接引用狄金生一些看似復仇的誓言,但你永遠也不知道他們想報什麼仇,因為實在很難看得懂那些塗鴉在寫些什麼。
我出獄回家後問題變本加厲。當地藝術團體組成糾察隊在附近巡邏,一些不中聽的消息開始散播,還有鄰居小孩對著我家丟雞蛋、貢獻衛生紙給我們當窗飾,哪怕他們從來不曾在乎過艾蜜莉‧狄金生或是她的房子,有一陣子這裡簡直就像天天在過萬聖節。後來事情越來越嚴重,有一次,一個人戳破我父母富豪汽車的四個輪胎,還有一次,有個人不知是出於悲傷還是氣憤,朝我家邊窗丟進一隻柏肯鞋──男人六號尺寸、右腳。
這些全都發生在我回家後的第一個月。到了月底,爸媽建議我搬出去。
「但是我該去哪裡呢?」我問他們。
「哪裡都可以。」我媽說。
「或許你可以去唸大學,山姆。」爸爸冷靜下來之後對我說。
「這的確是一個好主意,」媽媽說,「我們會很樂意幫你付學費。」
「好呀。」我說,因為我非常近距離的看著他們,這是我出獄後第一次仔細觀察他們,我看到了自己對他們做了什麼好事。
在我燒掉艾蜜莉‧狄金生的房子之前,他們看起來很正常、健康,就像那種喜歡度假、做園藝的快樂美國人,也有過一、兩次重大的危機(我還是小男孩的時候,爸爸曾經離家三年,他走後媽媽告訴我所有關於艾蜜莉‧狄金生之家的傳說,而這些都是我即將展開更大架構故事的一部分,躲也躲不掉)。現在的他們,看起來就像穿著燈芯絨褲子和帆船鞋的骷髏,眼睛凹陷甚至好像巴不得永遠縮到頭骨裡。
「好吧,」我又說了一遍,「我會去唸大學。」然後重複:「我愛你們。」
「喔,我們也愛你。」爸爸說,又開始哭哭啼啼。
「我們當然愛你。」媽媽說。接著轉向爸爸:「布來德立,不要再哭了。」
那天深夜,媽媽睡著後,爸爸沒敲門便走進我房間,站在床旁邊彎下身,彷彿想對我說什麼,卻又好像只想看看我睡著了沒。我闔眼躺著,正在思索自己人生的光明面,如何進入大學,為自己開創一個乾淨、誠實、沒有痛苦的生活,如何再一次讓父母以我為傲。我父親彎下腰,好像一輛起重機,不是準備用它的機臂高高將我舉起,就是要用沈重的球體將我毀滅。
「下樓來,」在黑暗的空間裡,爸爸的臉緊靠著我,小聲的說:「我要給你看些東西。」
我起身跟著下樓。爸爸走進他的書房,和這棟房子的其他房間一樣,四處都是裝滿書冊、頂天立地的書架。他坐下來,打開身旁的邊桌抽屜,拿出一個 Converse鞋盒給我,就是一般人收藏明信片、聖誕卡的那種紙盒。我打開鞋盒,看見裡面有許多信封,而且每件都用拆信刀工整的劃開。這些信是寄給我的,全部都是。每封信都好好收在信封裡,於是我一封封拿出來看。
盒子裡起碼有上百封信。其中有一些,就如我講的,來自美國文學學者,譴責我下地獄什麼的。這些學術憎恨信有點冗長,他們喜歡用文學性的隱喻,拒絕縮短句型,所以我一點也不想花時間看。我還收到一些典型縱火狂的來信,講來講去不外乎「燒吧!寶貝,燒吧!」這類主題。如此激烈的信依然無法引起我太大的興趣。這個世界充滿瘋子和這個世界充滿無聊的人一樣,都不是什麼大新聞。
當然還是有其他類型的信,一部分來自新英格蘭區及周遭的城市:波特蘭、布里司托、波士頓、柏林頓、德里、奇科皮、哈特福特、普羅維丹斯、皮司費德,也有些來自紐約和費城周邊的大小城鎮。這些信的寄件人全都住在作家附近,他們希望我幫忙燒了這些作家的房子。有名住在康乃迪克州新倫敦市的男子,希望我去燒了尤金‧奧尼爾的房子,因為奧尼爾有嚴重的酗酒問題,對到他家參訪的學童來說是很糟糕的示範,而這種階段的孩子應該要有更正直的學習偶像才對。一位住在麻州雷那克司的婦女,希望我一把火燒了伊迪絲‧華頓旔的家,因為到華頓家朝聖的車潮,擋住了她家的郵箱,而且在她看來,華頓根本就是個讓人討厭的騙子。而住在紐約古柏斯鎮的乳品農人,則希望我去詹姆士‧古柏焩之家的煙囪倒汽油,因為他一想到有人這麼有錢、自己這麼窮就生氣。
盒子裡還有許多來信,寫信的人期盼的都是同一件事。他們全都希望我去燒掉某些已故作家的房子,像馬克‧吐溫、露意莎‧梅‧愛考特、羅威爾、霍桑。還有些來信要我燒的是一些從沒聽過名字的作家房子。所有寫信的人都在等我出獄,而且全都願意付錢給我。
「哇噢。」我看完信之後對爸爸說。他沈默了好一會兒。這很有趣,只要我媽在場,爸爸總是顯得很軟弱,像是一個微不足道而且很愚蠢的人。但是現在,在這個房間裡,看著這些信,在我看來他非常聰明,好像戴著金屬眼鏡的佛陀一樣的安靜且穩重。從喉間到臉龐到全身,我感覺到一陣罪惡,「為什麼你不在我坐牢的時候告訴我?」
他看著我不作聲。這是一種試煉,而原因,還用問,智者都是這樣考驗愚者的,用這種方法讓他們變得比較有智慧。
「你想要保護我。」我說,他點點頭。這激勵我覺得自己應該可以說出正確的答案,於是我堅定的說:「你想要保護我遠離這些認為我是縱火犯的人。」
爸爸無法裝作沒聽見。他的理性經過一番痛苦的掙扎,開開合合十幾次的嘴唇欲言又止,感覺好像在看巨人亞特拉斯扛著我們立足的地球一樣。最後爸爸終於出聲,他傷心的說,非常傷心,「山姆,你就是個縱火犯呀。」
噢,真傷人!不過這是事實,我必須聽到,必須由爸爸的嘴巴告訴我,就像每個人都需要父親告訴他事實,然後有一天他也會對自己的小孩說實話一樣。而到時候,我的小孩也會對爸爸做出和我現在一樣的事:否認事實。
「你錯了,」我說,「我是個大學生。」我把鞋盒蓋上,還給父親,不給他機會說話就離開。回到床上之後,我向自己發誓,再也不去想這些信。我命令自己,完全忘記這些信的內容,我也認為自己做得到。反正上大學不就是這樣嗎?不就是忘掉所有不想記得的事,努力在這些陳年回憶找到路徑重新困擾自己前,在腦袋裡填滿新事物?
兩個星期後,我離家去唸大學;十年之後我才再次見到父母;十年之後我才重新又讀了那些信;十年之後我才遇到其中一些寫信給我的人;十年之後我才發現關於父母一些我從不懷疑、也永遠不想知道的事;十年之後我重回牢獄;十年之後所有該發生的都發生了。
我主修英文,因為知道自己做了讓父母失望和傷心的事,所以不管之前發生過什麼,我希望他們未來能以我為榮。而且小時候媽媽總是唸書給我聽,長大一點便規定我讀遍經典著作,還要寫報告詳細說明為什麼它們這麼了不起,所以我猜想,最起碼,我擁有了不錯的訓練與基礎,比較容易成功。
結果沒用。一點幫助也沒有。你永遠無法讓過去重來,那些我曾經相信非常偉大且充滿智慧的經典,現在看起來都是庸俗之作,根本無法吸引我。與其思索《大亨小傳》到底是不是傑作,我更著迷於觀察米爾頓教授山羊鬍子裡頭的烤乳酪碎屑。然後有一次,課堂上唸到狄金生的詩句,老師說她想帶班上同學去狄金生之家參觀,只可惜那棟房子幾年前被燒掉了,看著她努力回想縱火犯的姓名,我很清楚我並不想講自己的故事──沒有人比我更了解所有的細節。
為了要打斷並且逃離一連串的追問,以及接下去肯定會發生的責難,我假裝咳嗽跑去廁所,到學期結束都沒有再回去上課。而學期結束時我拿到D,沒被當掉的理由,就像我修的其他英文課程一樣:這學校不希望當掉任何學生,以便收到全額的學費。
所以成績不好只是我放棄英文主修的原因之一,還有另外的原因,一個更大的原因:我沒有辦法不去想有些事應該去做,有些事我還沒去試或還沒想到;我也沒有辦法不去想還有其他更新、更好的東西。我可以坐在中世紀文學課堂上,跟著包伍夫和格蘭德爾老師學古英文,滿腦子卻充滿著「應該還有什麼」的聲音。「還有什麼呢?」「還有什麼呢?」這很令人意外,因為我不是個會反抗的人,這輩子從沒大聲問過「還有什麼呢?」但是我腦子裡的聲音,一直不斷的替我問這問題。
簡單的說,後來我放棄了英國文學還有書寫它們的人──永遠的放棄,至少我是這麼想──然後轉戰包裝工程學系。這是非常好的改變,原因有三:第一,包裝工程學系比較不會發現我是燒掉狄金生之家的縱火犯,甚至不知道或根本不在乎狄金生是誰;第二,我有記住什麼易碎物品用哪種材質包裝最好的本領,我可以馬上了解為什麼小包裝洋芋片應該垂直撕、而家庭包洋芋片卻要橫向撕開,還有拉環該放在什麼位置比較好開。包裝工程的課我從來沒拿過比B+更差的成績,還在兩年之內修完四年課程,畢業後順利的發揮所學,在先鋒公司設於阿卡瓦姆的包裝部門找到產品發展和測試的工作,離史賓非爾很近。
上面是我轉戰包裝工程系之後發生的兩件好事,第三件,就是遇見了我的太太。
她的名字叫做安瑪麗,我們在大四的包裝科學性向研討會相識。安瑪麗很漂亮,是典型的美女,真的,而且身材高瘦,擁有一雙彷彿隨時都要躍起的長腿,俏麗的黑色鬈髮總是整齊的高紮在腦後,伶俐的笑臉美到讓你毫不在乎自己看起來一臉蠢相。還有什麼?沈思的時候,安瑪麗會抽一種很細很長的菸,以我觀察女人的經驗,只有非常纖細又時髦的女人才會抽菸。總而言之,她在我眼中就像義大利女神,絕對沒錯,因為她姓米拉貝里,祖先來自義大利的波隆那。
至於我的長相:我很高、像小孩一樣瘦,但是頭很大,看起來像根細長的火柴棒。我在獄中練舉重時造成一些副作用,包括自己都不知道的肌肉拉傷,這是另一件豬頭做的事。我的臉是身上最明顯的部分:很紅,有時看起來很健康,有如被風吹傷,感覺像是張懂得享受人生的臉龐,有時看起來卻像被火燒過一樣。當我羞紅了臉的時候,即使在黑暗的晚上,你也可以拿我臉上的紅光當照明。整體看起來,我還算長得普通英俊。我只有幾顆歪牙,大部分都很白,自然捲的棕髮依然濃密。如果我的頭能小一點,鼻子就會很像羅馬人。即使我的視力已經可以算是個瞎子,卻沒有讓眼鏡遮住我銳利的藍色眼睛,因為我戴了隱形眼鏡。戴上隱形眼鏡的我,一雙眼睛就像能夠看穿人的靈魂。但我依舊不能算是個美男子,別忘了我還是個處男呢,所以即使我和安瑪麗修了同樣五堂課,也不敢和她說話:安瑪麗美到讓我不敢和她說話。
「你真傻,」我們結婚之後她如此說道,「我不會美到讓你不敢和我說話。我從來都沒這樣想過,一次也沒有。」
「如果妳不是自認美麗,」我問她,「為什麼不主動找我搭訕?」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她說,但我從來沒有得到答案。
回到包裝科學性向研討會,安瑪麗選擇專攻杯蓋設計──那種放在咖啡或汽水杯上的塑膠蓋。研討會的老師愛斯納教授是個接近禿頭的男人,長得像是額頭的活動廣告。愛斯納教授對安瑪麗的案子不甚喜愛。他指出安瑪麗設計上的一些結構性瑕疵,誇張的問她是否知道咖啡如果沒倒進嘴裡而是倒在臉頰上,再順著流到脖子是什麼感覺。他問安瑪麗在聖母湖學院唸了四年包裝工程,是不是什麼都沒學到;又問安瑪麗如果沒有被大公司錄取,是否有其他的替代規劃。「因為他們一定不會錄用妳。」他說。
安瑪麗的確不是天生的包裝科學家,如果她設計的杯蓋真的拿去量產(不會的),肯定要燒掉幾張臉、打上一些官司。話雖如此,我不喜歡愛斯納教授對她說話的方式。我望向安瑪麗,她看不出一點難過,也沒落淚──她很堅強,直到現在都是──安瑪麗生氣的玩著脖子上掛的金色十字架,我覺得應該說兩句話幫她辯護。
「嘿,愛斯納教授,」我說,「放輕鬆,態度好一點。」我沒有大聲嚷嚷,所以轉頭點下一個人上台報告的愛斯納教授可能沒聽見,但重要的是安瑪麗聽到了。
「謝謝。」安瑪麗下課後對我說。
「謝什麼?」我問她,雖然我知道,當然,她是因為我說了該說的而謝我,但我可不認為自己或是任何人那麼做沒有任何意圖。
「為我挺身而出。」
「不用客氣,」我說,「要不要一起吃晚餐?」
「和你嗎?」她問道。
這是她說話的方式──直率且習慣要求簡單的事實──並不表示她對我有任何負面觀感。怎麼證明?後來我們去了史賓非爾一家叫做「學生王子」的德國餐廳吃晚餐。她是個少見的苗條義大利裔女孩,還喜歡吃德國菜,根本沒辦法叫她把手移開慕尼黑香腸盤,這只是我愛上她的原因之一。一個月之後,我們上了床,就在學生王子樓上我住的公寓裡。我肯定得到父母保守的真傳,除了享受之外,我不會開口談論任何關於性愛的事。但是我可以說自己終於失身了──或許是因為我當了太久處男,事後,我的臉竟然熱到泛紅,就像原子彈爆發一樣。我對安瑪麗說:「我是處男。」
「喔,甜心,」她說,「我不是。」她將手放在我炙熱的胸口,你可以從她的眼中看到一抹甜蜜的憂傷,可憐一個三十歲的處男。我從來沒見過一個人的心胸如此寬大卻又這麼易感,所以我問她,「妳願意嫁給我嗎?」
「我願意。」安瑪麗說。她的回應或許帶有憐憫之意,但的確有愛的成分:在我的經驗裡,你不能期待愛裡面沒有憐憫,也不會這麼希望。
快轉時間:我們畢業了。幾個月之後我們在聖瑪麗教堂結婚,婚宴在南岸的紅玫瑰舉行。安瑪麗的家人支付結婚費用並全程參與(來了許多人),但是我父母並沒有到場,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沒有告訴他們。當安瑪麗問起,「為什麼你沒邀請父母來參加婚禮?」我回答她,「因為他們過世了。」「怎麼會這樣?」她想知道。「什麼時候過世的?」
「房子失火,」我說,「他們死於那場火災。」這恰巧證明了人沒什麼創意,而且到了後面你會發現,這個說法跟事實非常接近。不論如何,我的答案看起來滿足了安瑪麗。但事實是情況越來越複雜。老實說,我能聽到腦子裡不斷有聲音在問「還有什麼?還有什麼?」而我無法確定那是自己的還是我父母的聲音。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布洛克.克拉克的圖書 |
 |
$ 272 ~ 282 | 我燒了大文豪的家
作者:布洛克.克拉克(Brock Clarke) / 譯者:王亦明 出版社:寶瓶文化 出版日期:2009-03-25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36頁 / 14.8 x 20.8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我燒了大文豪的家
◎《巴別塔之犬》作者卡洛琳.帕克斯特稱此書為:近年來讀過最棒的小說!
◎被譽為具有比爾.布萊森的幽默,和約翰.厄文動人筆調的精采小說!
◎臥斧專文推薦!
警告:如果你是一個熱愛文學的人,我們強烈建議你不要閱讀這本書!因為有個傢伙……燒掉了大文豪的家!
起訴事件:文學作家故居連續縱火案
案發地點:艾德華‧貝拉米、馬克‧吐溫、羅伯特.佛洛斯特等作家故居
犯案動機:不明
以下是來自縱火犯山姆的自白:
你人生中做過最豬頭的事是什麼?相信我,絕對不會比我更豬頭!
我從沒想過,一根掉落的菸蒂可以燒掉一棟房子,半夜沒人的空屋居然有兩個傢伙躲在裡頭嘿咻,更糟的是,那裡可是大文豪艾蜜莉.狄金生的故居!
如果你燒掉的是你家或公共廁所,或許有人會相信這是一場意外,不過一個名人的家嘛……那你絕對會被說成殺人放火,再奉送你十年苦牢!咳、咳,出獄之後我可是改過向善了,讀大學、找個好工作、娶妻生子,再也不碰文學或是書這類的鬼東西。只是,過去那把火似乎仍停留在我心中尚未熄滅,而且,還有許多人寫信來委託我,希望我幫他們燒了其他作家和大文豪的房子……
作者簡介:
布洛克.克拉克(Brock Clarke)
美國當代小說家。出生於紐約,在獲得狄克生大學碩士學位後,繼而取得羅徹斯特大學美國文學博士學位。他在2001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The Ordinary White Boy(暫譯:平凡的白人男孩)之後,陸續以兩部短篇小說集獲得文學獎。《我燒了大文豪的家》是他的第四部作品,不僅為他在美國文壇廣獲好評,創下銷售佳績,也是美國獨立書店推薦榜之首選書。
布洛克.克拉克的文章廣見於《密西西比評論》、《布魯克林評論》、《美國文學》、《新英格蘭評論》、《二十世紀文學》、《西南美國文學》。他目前在辛辛那提大學教授文學創作。
章節試閱
我叫山姆‧包西佛,就是那個不小心燒掉艾蜜莉‧狄金生彍在美國麻州安默斯特的房子,還因此意外殺了兩個人的縱火犯。為了這宗意外案件,我吃了十年牢飯,而根據美國文學學者的來信,我將為此付出長久的代價,承受不大美好的後果。我的故事在當地無人不知,在此就不多做交代。
出獄回家後,我和父母住在一起,但搬回家和父母同住並不是很順利。其中一個理由,是我燒掉了艾蜜莉‧狄金生的房子,讓身為高中英文老師的媽媽和當地大學出版社編輯的爸爸傷透了心。美麗的文字對他們來說的確非常重要,他們從不關心電影或電視,但只要一些優雅的字句,...
出獄回家後,我和父母住在一起,但搬回家和父母同住並不是很順利。其中一個理由,是我燒掉了艾蜜莉‧狄金生的房子,讓身為高中英文老師的媽媽和當地大學出版社編輯的爸爸傷透了心。美麗的文字對他們來說的確非常重要,他們從不關心電影或電視,但只要一些優雅的字句,...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布洛克.克拉克 譯者: 王亦明
- 出版社: 寶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3-25 ISBN/ISSN:978986674563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36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英美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