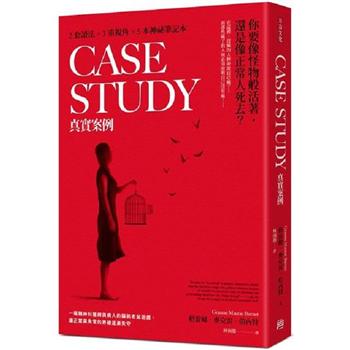「你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你不再生氣,而是把情緒壓抑在某個地方,然後你變得挑剔,覺得自己高高在上。」
讀遍東岸所有名校的柯妮.法瑞爾,爽快擺脫她在紐約最後一處傷心地,來到西岸與媽媽同住;然而,在加州等待她的,並非好萊塢式的逍遙浮華,更非晴空萬里下的繽紛絢爛……
雙親事業的低迷不振、父母離異塑造出的早熟性格、對於未知自我的蠢動和探求,在柯妮的小世界裡激起一浪高過一浪的心靈風暴。她學著摯友珍奈離經叛道的步伐,讓威士忌和尼古丁成為自己的日常,讓邂逅的男性們引導她看見另一個自己……青春期遲早要結束,她奔馳在人生的初夏裡,無法回頭,依舊奮不顧身。
本書特色
嗨,青春的你,你的青春,過得怎麼樣?
如果你喜愛法國作家莎岡的《日安憂鬱》,那麼你會在《早餐巧克力》看到美式的躁動靈魂。
如果你讀過美國天才詩人普拉絲的《鐘形罩》,那麼你也會在《早餐巧克力》看到深沉的青春苦悶。
《早餐巧克力》透過一名十五歲少女的眼睛與思想,對於青少年性向、情感與情慾的探索、男女間的開放式關係,甚至包括酒精成癮與自殘傾向的心理,均敢於直言敘寫,顛覆了傳統上對理應純潔如一張白紙的女孩既定印象。
這破壞性的成長經歷,道出了許多青少年青少女的敏感心緒,更讓人從書中窺見美國東岸上流社會與好萊塢式的墮落繁華,因此《早餐巧克力》一出版立即風靡各國,引起跨地域的文化共鳴,一共被譯作十多種語言,累計超過百萬本銷量,在在顯示它在大眾文化之間的影響力。
作者簡介:
帕梅拉.摩爾 (Pamela Moore, 1937~1964)
美國紐約人,雙親皆為作家,在摩爾十歲左右離婚並分居美國東西岸,因此她自幼即在兩地間頻繁往返。於初試啼聲之作《早餐巧克力》當中,亦能見到摩爾諸多參酌自身經歷形塑的情節。
一九五六年,年僅十八歲的摩爾出版了首部小說《早餐巧克力》,當時美國的社會氛圍認為小說內容「道德淪喪、荒誕不經」,導致這位少女作家飽受當時輿論抨擊。然而,書甫一出版即攻占多國暢銷書榜,被譯作十一種語言,累計超過百萬本銷量,在在顯示此作於大眾文化之間的影響力。
摩爾於一九五八年結婚,據她所言,丈夫是一位平凡的律師,與她在《早餐巧克力》中刻畫的燈紅酒綠人際網絡毫無所似。婚後陸續又出版了四部小說,儘管話題性不若《早餐巧克力》轟動,有些文學評論卻認為,摩爾在後來的作品中(尤其是最後一部作品《The Horsy Set》)展露出了無止無盡的沉鬱氛圍,實已透露她深受精神疾病折磨的痛苦。
一九六四年六月,下班回家的丈夫發現她倒在打字機旁邊,留下了兩人未滿周歲的兒子,以及她尚未完成的書稿《Kathy on the Rocks》──摩爾已然舉槍自盡。
譯者簡介:
王聖棻、魏婉琪
夫妻檔,從電玩中文化、技術操作手冊一路翻到文學作品、藝術理論和歷史,生冷不忌,把翻譯當成讓頭腦持續運轉避免痴呆的最佳方式。
譯有《大亨小傳》、《月亮與六便士》、《人性枷鎖》、《歐亨利短篇小說選集》、《如何使用你的眼睛》、《詩人葬儀社》、《從上海到香港,最後的金融大帝》、《墨利斯的情人》、《黃昏時出發》、《京華煙雲》、《荒誕醫學史》、《鐘形罩》、《化身博士》、《三尖樹時代》等。
章節試閱
「放春假以後我就一直沒機會跟你說話,」羅森小姐說。「你跟你媽媽相處得怎麼樣?」
「我們相處得很好,」柯妮說。有一瞬間,她對這個年紀比她大的女人問出這種自以為和她很熟的問題心生厭惡。當她感覺有人悄悄跨越她的防線時,她總是本能地退縮。但她隨即想起來,羅森小姐是她的朋友。「我們一直很好。」她還是很警惕。羅森小姐和她都知道這不是真話,但羅森小姐耐心等待這個女孩一如既往侃侃而談,因為只有她們兩人在的時候,她才能自在地說話,就像她從來沒能跟女性說過話一樣。柯妮有一大堆被她稱為「繼父」的人,通常是她媽媽的朋友,她會跟他們傾訴一個孩子永遠無法對父母說出來的擔憂和恐懼。從她六歲開始不信任母親以來,羅森小姐是她信任的第一位女性。
「我們沒辦法溝通,就是這樣。她不怎麼瞭解我,每次放假她見到我,對我的瞭解都比上次更少一點。如果做得到,我會跟她談談的,」她繼續說,「但你知道,跟女人實在沒辦法對話。她們的腦子甚至沒辦法像你那樣直線運行;我想談一件事,證明某個觀點,她們的思緒已經轉到次要但隱約相關的話題去,弄得我快發瘋。」
羅森小姐被逗笑了。「你不認為自己是女人嗎?」
「不是,不完全是,」柯妮思索著。「我不會像她們那樣想事情。男人總會說,我思考的方式像個男人。我想,如果我真是個男人,事情就簡單多了。但也可能不會。說不定我還是不喜歡女人,但當個男同志又太糟糕了。」
羅森小姐笑她太單純。「你真的想當男人嗎?」
「嗯,你知道,從我懂事開始,我就一直夢到我是男人。我現在幾乎已經習慣了,所有的夢裡我都是我自己,但是個男人。我也想知道為什麼。」她沉思著。
「你說過爸媽一直希望你是個男孩,你媽媽還要你幫她調酒,像兒子一樣照顧她。也許這就是原因。」
「也許吧。」她想了一會兒,但時間不長,因為這對她來說並不怎麼重要。
「你知道,」她繼續說,「我的假期被搞爛了,我媽難過得要死。」
「不要用『搞』這個字眼。」羅森小姐說。
「為什麼?我從小就是這麼用的。有哪裡不對嗎?」
羅森小姐沒再追究,只是說:「你只要跟媽媽見過面,總會有點敵意和戒心。」
「她是個婊子。」柯妮脫口而出。
「你心裡清楚你不是這個意思。」羅森小姐溫柔地說。
「我知道。」她任性地回答。
「那你為什麼這麼說?」
「我高興。」
「你太聰明了,說起話來一點都不像個小女孩。」
「我他媽的就是個小女孩!」柯妮突然說。「這就是我討厭和媽媽在一起的原因,好像當媽的其實是我。她因為對我發火而難過的時候,我還得安撫她,我必須一直跟她保證她是個很棒的女演員——你知道,我長這麼大只看過她四部電影,我覺得這輩子看這些也就夠了——我不知道她演得好不好,但我跟她說她棒極了,因為我喜歡讓別人高興。當尼克一次又一次離開她——或者終於徹底離開她的時候,我還得握著她的手,給她調難喝的酒,因為她不喜歡一個人喝酒的感覺,全是這種事。我真的受夠了!」
「嗯,雖然我沒見過你媽媽,」羅森小姐說,「也知道她很不成熟,但你必須忍耐,努力幫助她。她也是個非常孤單的女人,你真的是她唯一的依靠——尤其現在她又離婚了。」
「你可真他媽的聖潔,」柯妮尖酸地說。「我的意思是,你跟我爸一模一樣。講這些話對你來說輕輕鬆鬆,因為必須去做的人不是你。這些全是廢話。」
羅森小姐退讓了。她站起來,手放在柯妮肩上。
「你不需要這樣跟我說話,」這位女性溫柔地說。「在這裡的時候,你可以盡量放鬆。不需要因為害怕跟我太親近而自我防衛。」
柯妮悶悶不樂地盯著眼前。她知道,當這隻手放上她的肩膀,她抬頭看著羅森小姐時,她就會有種古怪的感覺,好像她在洗澡或準備換睡衣時偶爾會有的,彷彿有一大群人正圍觀著她裸體的感覺。
「你跟我說過,」她回憶著,「你愛我。」
羅森小姐放下手,坐在床上,面對著柯妮。
「是的,可憐的孩子,我愛你。為什麼又問一次呢?——你不相信有人會愛你嗎?」
「除非他們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
她看見羅森小姐臉上的表情,又說:「沒錯,說實話,我就是這麼覺得。還有,別叫我『可憐的孩子』!我不要憐憫,誰的憐憫都不要。沒有誰需要為我難過,因為我可以照顧自己,一直以來都是這樣。我甚至不需要任何人來愛我,因為其他人對我來說沒那麼重要。我是個冷漠的人,還有點自私。」
羅森小姐嘆了口氣。「不,你不是這樣的人。我什麼都沒教會你嗎?我不知道是誰或什麼事讓你有了這種想法,但你其實是個很熱情、衝動的女孩,如果你能給自己一個機會去愛,變成一個成熟的人,你是可能成為一個好女人的。」
柯妮抬頭望著羅森小姐,臉上挑釁的神情暫時消失了,看起來幾乎像個小孩。
「如果你幫我,也許這一切我都能做到。我在你這裡的時候,我覺得你擁有一種讓我能堅持下去的東西。我跟你在一起之後,才知道原來人們可以跟人說他們愛誰、信任誰,不必害怕被拒絕或者被利用。」
羅森小姐點了另一根菸,因為她不想說出那句她知道最終還是必須說的話。
「媽咪說,我去年聖誕去好萊塢的時候就像變了一個人。」她自豪地說。「她說她簡直不認識我了。我不再那麼怕她,她喊我名字時,我也不會那麼驚嚇了。這是你為我做到的。」她說,想引出年長女子的回應。
「柯妮,你知道,」她艱難地說,「我確實有話想對你說。在你說了這些話以後,對我來說,要開口變得很難,因為我真的很愛你,但我覺得說出來是為你好。你想來根菸嗎?」
「不,謝謝你,我不抽菸。哎呀,一定是件超可怕的事,」她笑著說。「只有那些想自殺或者被毀婚什麼的女孩子,學校的人才會給她們香菸。」
女孩刻意表現得輕浮,因為她感覺到羅森小姐要說的話會傷害她。
「我很高興你來這裡。我喜歡跟你聊天,因為你很聰明,我非常喜歡你。」
噢,天哪,柯妮心想,千萬不要說出我害怕你就要說出口的那句話。
「但是你知道,你應該多花點時間和跟你同齡的人在一起。你可以從她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這裡有很多聰明的女孩,她們的書讀得跟你一樣多。」
「我厭倦了跟我同年齡的人,」她絕望地說。「我一直是跟媽媽的朋友們一起長大的,我發現跟他們說話更自在。年紀大點的人比較有意思。」她在年長女子的臉上尋找理解。「這你知道的。」
「這就是問題所在,」羅森小姐說,「你從來沒學過怎麼跟同年齡的人相處,斯凱斯布魯克給了你一個學習的好機會。這比你從我這裡學到的任何東西都重要。」
柯妮站了起來。她感受到了,當她從《紐約時報》上得知母親嫁給了好萊塢影星尼克.羅素時,也有類似的感覺。柯妮此刻覺得自己半懂不懂的,模糊地意識到,自己正在失去一個心愛的人。
「你的意思是,你不希望我晚上再到這裡來,不希望我下課之後坐在你桌子旁邊,或者找你說話。」
「是,我就是這個意思。」女子無奈地說。
「那你為什麼不說?我受得了的。」她把那本《芬尼根守靈夜》扔在床上。「我想我最好把這個還給你。」她說,轉身準備出去。
羅森小姐站了起來。
「柯妮……」
柯妮停下腳步,在門邊突然轉過身來。心想,說不定她改變主意了。
羅森小姐走到她身邊,低頭看著這個女孩,眼中滿是悲傷。她彎下身,吻了柯妮的額頭。
「請不要生我的氣,」她說。「我別無選擇。」柯妮始終不懂羅森小姐這句話的意思。
柯妮尚不知曉自己有多失落,她只感覺到失去東西的疼痛和一種麻木感,似乎從這一刻開始,她的生活就要變樣了。
「放春假以後我就一直沒機會跟你說話,」羅森小姐說。「你跟你媽媽相處得怎麼樣?」
「我們相處得很好,」柯妮說。有一瞬間,她對這個年紀比她大的女人問出這種自以為和她很熟的問題心生厭惡。當她感覺有人悄悄跨越她的防線時,她總是本能地退縮。但她隨即想起來,羅森小姐是她的朋友。「我們一直很好。」她還是很警惕。羅森小姐和她都知道這不是真話,但羅森小姐耐心等待這個女孩一如既往侃侃而談,因為只有她們兩人在的時候,她才能自在地說話,就像她從來沒能跟女性說過話一樣。柯妮有一大堆被她稱為「繼父」的人,通常是她媽媽的朋友...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