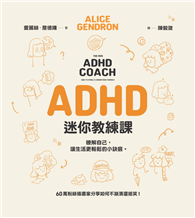心之高牆,才是最難掙脫的禁錮……◇ 隱玉之名作!榮獲「山本周五郎賞」,已改編拍成電影!
◇ 長銷不墜!熱賣超過80萬冊,亞馬遜書店讀者4.5顆星感動推薦!
如果殺一個人,就可以讓世界重拾平靜,
可以讓所愛的人堅強,為什麼不呢?他沒想到自己會這樣殺人,當刀刺進肋骨時,所有痛苦化為解脫,瞬間迸流而出。他也沒想過殺死重宗後,自己會怎麼樣?從今往後,他的人生只有此刻。
重宗是這家醫院所有病友們害怕的對象。
嚴格來說,這家醫院收的是「傷患」,只是他們的傷口用眼睛看不見,例如:櫻花病房的阿中曾因幻聽和妄想而差點掐死父親;菊花病房的敬吾整整九年都把自己關在房內;甚至蘭花病房最和善的秀丸爺爺,也是「死過一次的人」……
受傷的心,在這個小小的世界裡努力綻放生命,重宗卻是個破壞者,暴力、威脅,無惡不作,然而院方束手無策,其他人也只能祈禱自己不會是下一個受害者。
他也跟大家一樣祈禱,卻是為自己一心守護的那個女孩。女孩的青春是他無緣擁有的,女孩的微笑是賜予他救贖的光,他絕不容許重宗對她有一絲一毫的傷害。但是,重宗的視線卻開始盯上女孩了……
身體的傷可以吃藥擦藥,但心裡的傷呢?往往將世界封閉起來的其實並非外在的設限,而是內心的枷鎖。然而,絕望若是入口,希望便是出口,書中這群帶著深深的「心傷」卻仍勇敢活著的角色,正如同一段段真實人生的縮影,而透過帚木蓬生的娓娓訴說,所有的單純和複雜、快樂與痛苦、孤獨與喧囂,都有了最動人的依歸!
作者簡介:
帚木蓬生HOSEI HAHAKIGI
日本著名的醫生作家,一九四七年生於福岡縣。東京大學法文系畢業後,先進入TBS電視台工作兩年,之後赴九州大學醫學院就讀,步上精神科醫生之路。兼具文學與醫學的專長,也使他擁有獨到的人道關懷,對於人性更有深刻的洞見。他下筆極具力道,內斂的筆端卻飽蘊著強大的戲劇張力,令人震撼也令人感動,也因此自出道以來即得獎不斷。
一九七五年以《頭骨上的旗幟》贏得「九州沖繩藝術祭文學賞」;一九七九年以《白夏的墓碑》入圍「直木賞」;一九九○年以《賞之柩》獲選第三屆「日本推理懸疑大賞」佳作;一九九三年以《三度海峽》榮獲「吉川英治文學新人賞」;一九九五年則以《閉鎖病棟》榮獲「山本周五郎賞」,並於一九九九年改編拍成電影「生命之海」;一九九七年他再以《逃亡》獲得「柴田鍊三郎賞」;二○一○年以《水神》獲得「新田次郎文學賞」;二○一一年又以《和平》榮獲第六十屆「小學館兒童出版文化賞」。
另著有《內臟農場》、《希特勒的護具》、《黑穗醋栗之舞》、《安寧病房》、《國銅》、《空夜》、《空山》、《非洲之蹄》、《胎兒》、《千日紅的戀人》、《受命》、《聖灰的暗號》等多部作品。
譯者簡介:
王蘊潔
在翻譯領域打滾十幾年,曾經譯介山崎豐子、小川洋子、白石一文等多位文壇重量級作家的著作,用心對待經手的每一部作品。
譯有《不毛地帶》、《博士熱愛的算式》、《洗錢》等,翻譯的文學作品數量已超越體重。
臉書交流專頁:綿羊的譯心譯意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名家推薦︰
《卡迪斯紅星》直木賞大師逢坂剛專文解說!【日本文化名家】李長聲.【日劇達人】小葉日本台.【中正大學台文所教授】郝譽翔真情讚譽!
帚木的作品中,總是對弱勢者或背負不利條件的人投以溫柔的眼神。他雖然沒有大聲吶喊自己內心的想法,卻深深地、重重地傳達到了讀者的心裡。──直木賞大師/逢坂剛
看了很感動,忍不住邊看邊啜泣……閱讀的時候胸口發燙,很少有一本小說能讓我們有如此豐富的體驗!一本讓我們重新思索「人生」的好書!──日本書店店員
作家與醫生都是在探索人生。帚木不僅診視人的病,也觀察人心,更難能可貴的是,無論在現實抑或小說中,他始終站在了患者一邊,爲患者代言。──日本文化名家/李長聲
一群被社會遺棄的「病人」,一段搥心肝的人間悲歌,每個主角的人生盡是百般的心酸與無奈。這或許是舊時代的悲劇產物,不過即便現在,我們對故事中所稱的病友又了解多少?本書沒有義憤填膺的控訴,也無須刻意的矯情煽情,但就因為平凡,所以更加讓人動容。
合力演出的舞台劇,傳遞的是對親人無限的掛念。為了守護僅有的希望可以不惜代價,那樁事件的背後又究竟蘊含多少的羈絆?在《閉鎖病棟》裡頭,人身自由的拘禁算不了什麼,大家渴望的是心靈的解放與寄託。-日劇達人∕小葉日本台
解說:關於《閉鎖病棟》
直木賞大師/逢坂剛
距今十八年前的一九七九年,世界各地受到伊朗革命的影響而面臨第二次石油危機,日本成為亞洲各國中,第一個成功舉辦七大工業國高峰會(東京高峰會)的國家,跨出了第一步,確立了日本在國際社會中的定位。
那一年,有兩位新人作家宛如彗星般出現於日本文壇,而且,他們的作品屬於日本書市前所未有的「國際冒險小說」這個全新領域。其中一位是創作《非合法員》的船戶與一,另一位就是《白夏的墓碑》的帚木蓬生。兩位作家的作風和寫作風格都完全不同,卻為娛樂小說的世界引進了國際視野,成為該創作領域的先驅。
在此之前,並非沒有以國外為舞台的推理、間諜小說或冒險小說,更早之前,結城昌治就創作了《高梅茲的名字就叫高梅茲》(音譯),生島治郎也寫了《黃土的奔流》,都屬於優秀的作品,但都只是單一零星的作品,無法帶動整個領域的發展。然而,《非合法員》與《白夏的墓碑》這兩部作品讓人產生一種預感和期待,未來將開拓出一個小說的新世界。隨著之後「國際冒險小說」這個領域的發展,也應驗了當時的預感。
很不幸的是,船戶的作品因為提前了十年發表,因而遭到閱讀市場的抹殺,但帚木的作品入圍直木賞,應該算是受到了正確評價,然而最後沒有得獎,只能說,他的作品同樣太早問世了。
即使如此,毫無疑問地,這兩部作品成為之後在該領域創作者的問路石。
*
當時,我在工作之餘,立志成為作家,曾多次投稿參加雜誌的新人獎。那時候,其實我已經完成了處女作《卡迪斯紅星》的初稿,總共寫了一千四百多張稿紙。
但是,一個外行人即使寫了厚達十幾公分的手寫稿,不要說奢望能夠出書,甚至找不到編輯願意看自己完成的書稿。我了解到欲躋身於作家之列,首先必須讓人認同自己是專業的作家,於是積極參加新人獎。我的參賽作品是以西班牙為舞台的推理小說,這是以前從來沒有人寫過的,雖然入圍了決選,最終卻無緣抱獎而歸。
正當我對自己的能力和目標產生疑問之際,文壇出現了船戶和帚木這兩位新星,這件事帶給我極大的激勵,同時,卻也帶給我更多的焦慮。對一個作家來說,最大的痛苦莫過於其他作家已經搶先寫了自己想寫的故事。
但轉念一想,以我的觀察,國際冒險小說(當時還沒有那麼明確的認知)領域尚未開拓,我仍然有機會擠入先驅之列。
翌年一九八○年,我那篇以西班牙為舞台的短篇小說如願獲得新人獎,我順利地踏入文壇。現在回想起來,可以說我能夠得獎是拜船戶和帚木那兩部作品所賜。
*
對於純文學出身的帚木來說,或許並不樂見自己的《白夏的墓碑》被歸類為國際冒險小說,但是,無論作者喜不喜歡,這都是一部劃時代的作品,成為在一片前人不曾走過的原野上開墾的第一把鐵鍬。
之後,帚木以曾經工作過的電視業界為題材,創作了《第十二年的影像》(一九八一年),以及再度以國外為舞台所創作的醫學推理《黑穗醋栗之舞》(一九八三年),平均每隔一年就創作出一部新作品。但是,在作品集《天空的色紙》後,不知是否因忙於精神科醫師的本業,有好一陣子沒有推出單行本,等了好幾年,才又再見到帚木的作品問世。
一九九○年,帚木的《賞之柩》入圍了目前已停辦的「日本推理懸疑大賞」決選,當時,擔任評審的我強力推薦這部以爭奪諾貝爾獎為題材的推理小說成為該屆大賞,不光是因為作者的資歷,更因為我覺得這部作品的整體結構、文字和表達能力都遠遠超越了其他作品。
然而,在評審過程中,他純熟的寫作技巧反而招致「太嫻熟了,無法留下深刻印象」的評價,而隨著強大對手《抱著黃金飛翔》(高村薰)出線,帚木與大賞擦身而過,只得到佳作。當時,帚木和高村的作品都具備了極高的水準,兩者競爭時,無論誰抱得大賞,另一方應該都輸得心服口服。
在此之後,帚木的創作力爆發,陸續發表了多部作品。在《非洲之蹄》、《內臟農場》等多部佳作問世後,終於以《三度海峽》榮獲「吉川英治文學新人賞」,並以本書《閉鎖病棟》榮獲「山本周五郎賞」。他在文壇上的活躍表現令人瞠目,他所創作的另一部以第二次大戰中的德國為舞台的大作《總統的護具》,是日本人創作的歐洲現代史小說中,屈指可數的力作,我個人將這部作品列為一九九六年年度小說的前三名。
*
引言似乎有點長。
本書《閉鎖病棟》是以作者最熟悉的精神病院為舞台的小說,屬於一部教養小說。雖然是以精神科為主題,但如果以為是時下流行的異常心理推理小說就大錯特錯了,這部極其嚴肅的小說和那種流行小說完全屬於不同的境界。
近十年來,美國出版了不少以異常心理為題材的犯罪小說,當然,這些作品或多或少反映了現代美國社會的病理和病源,但日本的國情與美國不同,如果照單全收這些殺氣騰騰的小說,恐怕會難以消受。我看了湯瑪士.哈理斯的《紅色龍》和《沉默的羔羊》後,就覺得不想再看了。活剝人皮、挖取內臟、砍斷手腳和虐待幼兒固然刺激,但以此論斷「人類原本就是異常的存在」,恐怕也讓人不知如何回答。
帚木的《閉鎖病棟》同樣描寫了各種罹患精神疾病的人,卻創造與描繪出一個和那種充滿血腥刺激的小說相反的世界,這是第一部從病人的立場,公正地描寫精神病院實況的小說。我所說的「公正」,當然不光指沒有歧視的觀點,更代表書中沒有那些矯情卻毫無助益的同情與憐憫,而是以與病人相同的角度,描寫和我們「本是同根生」的精神病人的優缺點,這種堅定的態度才能激發真正的理解與共鳴。
看完這部作品後,讀者必定會因為發現精神病人其實比我們更單純、更正面而感到愕然,甚至會覺得是自己異常,也許他們才是正常人。如果在閱讀過程中,不曾有過一絲這樣的不安,我反倒會為這樣的讀者感到不安。
當發生兇殺事件時,有時候可以在報紙上或電視上看到、聽到「兇手在看精神科」之類的內容,有什麼必要說這句話呢?這種報導只會助長「看精神科的病人等於危險」的誤解,對讀者根本沒有任何益處。在精神科的病人中,的確包括了罹患具有危險性、兇暴性疾病的病人,但是就像維護社會治安的警察機構中也有壞警察一樣,任何世界的人都有好有壞。這樣的比喻或許有點不恰當,假設有一個警官當了小偷,不至於會有人把所有警官都當成小偷吧?《閉鎖病棟》這部作品提出了省思,提醒我們要用公正的態度看待事物。
書中出現的人物是你也是我,《閉鎖病棟》並不是指某家特定的醫院,而是象徵著我們所處的這個受到管理的社會整體。
這部作品的重點,在於排練醫院表演會上的節目時所提到的以下這段話:
「病人已經無法扮演其他的角色了。那個人曾經做過什麼,而某個人又曾經做過什麼……大家以前曾經做過各種工作。……每個人一住進醫院,全都變成『病人』這種另一個世界的人,完全抹殺了之前的職業、人品、喜好等所有的一切,變成了行屍走肉。阿中希望其他人知道,包括自己在內的病人並不是行屍走肉。他要告訴大家,在身為病人的同時,我們也可以扮演好病人以外的某個角色。」
那是人類主張自己是人類的吶喊,是世界上最悲痛的吶喊。
帚木的作品中,總是對弱勢者或背負不利條件的人投以溫柔的眼神,無一例外。在本書中,即使對唯一的壞蛋重宗這種黑道兄弟,也不吝於給他一線救贖。
帚木蓬生的小說總是令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我喜愛的桑多斯.艾爾南迪士(Santos Hernandez)古典吉他所帶來的芳醇音色世界,閱讀他的小說,可以感受到和彈奏桑多斯吉他時相同的慈愛與平靜。吉他這種樂器由吉他手放在最靠近心臟的位置彈奏,而且是用自己的手指直接彈出音色,是極富有人性的樂器。
我想,這就是所謂觸動琴弦的小說。
──本篇解說完成於一九九七年三月
名人推薦:名家推薦︰
《卡迪斯紅星》直木賞大師逢坂剛專文解說!【日本文化名家】李長聲.【日劇達人】小葉日本台.【中正大學台文所教授】郝譽翔真情讚譽!
帚木的作品中,總是對弱勢者或背負不利條件的人投以溫柔的眼神。他雖然沒有大聲吶喊自己內心的想法,卻深深地、重重地傳達到了讀者的心裡。──直木賞大師/逢坂剛
看了很感動,忍不住邊看邊啜泣……閱讀的時候胸口發燙,很少有一本小說能讓我們有如此豐富的體驗!一本讓我們重新思索「人生」的好書!──日本書店店員
作家與醫生都是在探索人生。帚木不僅診視人的病,也觀察人...
章節試閱
聽到護士叫自己的名字,她從沙發上站了起來。
放了觀葉植物的候診室內只有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女人,即使島崎由紀起身,那個女人仍然埋頭看著雜誌,不知道是否擔心由紀尷尬。
門後的護士拉開簾子,指了指置衣籃。
由紀脫下毛衣,拉下裙子的拉鍊。藍色毛衣雖然摺得整整齊齊的,但袖子手肘的位置仍然鼓鼓的。
「內衣褲也脫完後,請穿上這個。」
護士親切地說著,遞給她一件手術服。
「好。」
由紀輕聲回答,接過手術服。
白色棉質手術服並非新品,但肌膚可以體會到清潔的感覺,想到之前有人穿上這件手術服,躺在手術台上,由紀的心情稍微放鬆下來。
然而,當她彎下身、抬腿脫下內褲,塞進洗衣籃內的裙子下時,悲傷的感覺再度湧上心頭。
她只看了護士一眼。這是不同於上一次的年輕護士,當視線交會時,對她微微一笑。走進手術室後,那名護士也不經意地觀察由紀的動靜。由紀很被動,她只要垂著眼,按照護士的指示去做就好。她儘可能不東張西望,努力讓大腦放空。
她按護士的指示仰躺在手術台上,隔著手術服,可以感受到冰冷的手術台。她的姿勢就像翻過身的烏龜,用力張開雙腿。
由紀沮喪地睜開眼,前方沒有任何東西,只有漆了白色油漆的天花板。四周打著木框,靠窗的地方有淡茶色污漬,那污漬的形狀有點像蓮花。周圍被簾子的軌道隔開了,只能看到這麼小的範圍。
「島崎小姐,等一下會注射麻醉劑,等妳醒來之後,手術就結束了,不會痛。醒了之後,請妳先去隔壁休息一下,傍晚就可以回家了。」
戴著綠色手術帽的臉擋在天花板前。一個和自己祖母年紀相仿的女人這麼有威嚴地和自己說話,讓由紀感到有點不可思議。由紀決定把一切都交給她處理,用力點了點頭。突然,她覺得即使永遠都不醒來也無妨。
「請妳慢慢數數。」
針頭扎進了右手手臂,那一點感覺特別冷,之後身體隨即溫暖起來,意識漸漸模糊。當她數到六的時候,舌頭打結,沒辦法數到七。
「妳肚子裡有一個小寶寶,差不多這麼大。」
穿著白袍的醫生在由紀的面前竪起大拇指。醫生沒有說懷孕,而是說有小寶寶,似乎道出了醫生的想法。診察室的木桌已經用了好幾十年,和椅子前端相碰的地方凹了五公分左右。圍牆上泛黃照片的老舊程度和在圖書館看到的紀念照不相上下,應該是哪一所女子醫科大學的畢業照吧!所有人都穿著日式畢業袍,只有站在前排的一名男子留著鬍子,穿著好像禮服般的大衣。
這是由紀有生以來第一次踏進婦產科。踏進這家醫院的大門之前,她已經實地走訪了十家醫院,最後靈機一動,開始在黃頁電話簿中翻找。黃頁上介紹高瀨順子醫院距離車站八分鐘的路程,她實地觀察後,發現這所兩層樓的醫院好像在立正般挺著身體,擠在圍著高大圍牆的豪宅和新建的樓房中間,油漆剝落的看板和霧面玻璃的入口讓醫院看起來更寒酸,但院長是女性,附近也沒有什麼來往行人,於是,她下定了決心。在養護學校周圍又繞了一圈後,由紀推開了醫院的大門。
脫下鞋子,換上室內拖鞋後,她戰戰兢兢地探頭向掛號櫃檯張望。一個身穿白衣,正在仔細擦拭藥品架的四十歲女人回過頭。從她臉上略微驚訝的表情,由紀知道自己看起來很年幼,所以越發緊張起來。但是,她已經無路可退了。她出門時穿了制服,但在車站的廁所換上了洋裝,臉上沒有化妝,梳著妹妹頭。
「健保卡呢?」
她沒有健保卡。
「那檢查費用也要全額自費喔!」
那個女人一臉同情地說。由紀很想知道要多少錢,但她沒有勇氣發問。她身上只帶了原本要繳給學校的三千兩百圓,如果不够的話,改天再來補繳。由紀在點頭時暗想道。
她在那個女人遞給她的資料卡上把生日整整提前了四年,地址欄內也填寫了同學家的地址。
她在空無一人的候診室內等了大約十分鐘,不一會兒,一個嬌小的女人打開診察室的門請她進去。那位把一頭灰色的中分頭髮綁在腦後的,就是高瀨醫生。
「我想檢查一下有沒有懷孕。」
由紀不記得當時自己露出了怎樣的表情,即使在老師辦公室與班導以外的老師說話時,也從未這麼緊張過。說完之後,她整個人好像累癱似地坐在圓椅上。高瀨醫生沒有立刻回答,打開病歷,用很粗的鋼筆寫了一、兩行字,然後放下鋼筆,轉頭看著由紀,雙手交疊在白袍上,用關心的口吻問她從什麼時候開始生理期沒來,有沒有其他症狀,以及對方的男生和家長對這件事的態度。
尿液檢查後,還做了超音波檢查,最後是內診。
「病歷上寫著十八歲,憑我行醫多年的經驗,妳應該不滿十八歲吧?」
當醫生告訴她肚子裡有小寶寶後,又這麼補充道。
「我每次看到像妳這樣的女孩來診所,都會覺得很難過。這等於扼殺了一個小生命,妳的身體也會受傷。」
高瀨醫生低聲說話的表情真的很哀淒。「我自己沒能够生下一男半女,可能是我雖然接生了不少小寶寶,但也埋葬了相同數量的生命。」
由紀低著頭,雙手規矩地放在腿上。
「如果情況允許,最好是生下來,所以,妳再好好想一想。妳可以和妳男朋友商量一下,但最晚要在一、兩個星期內決定。想要拿掉孩子時,要請妳男朋友或是妳媽媽陪妳來。」
「我自己一個人不行嗎?」由紀無助地問。
「如果妳還未成年就不行,因為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我不敢告訴我父母,我男朋友也不會來。」
她一開口,眼淚就撲簌簌地流了下來。醫生沉默片刻,最後一臉沉痛地說:「妳下次來的時候再說,即使一個人來也沒有關係。」
由紀在櫃檯問到的墮胎費用是她根本付不起的金額。
即使在教室時,她也整天想著這件事。上體育課時,她推說生理痛很嚴重,所以請假休息。她很羡慕身穿運動衣,在運動場上蹦蹦跳跳的同學,其他同學在她眼前玩壘球的吆喝聲彷彿遠在幾公里外。自已根本沒那個心情來學校……
第二天,她提早離開學校去找打工的工作。她也去了平時從來沒去過的河對岸的鬧區。中午過後的街道上,有些商店拉下了鐵捲門。當她想要找工作時,覺得原本以為滿街都是的肉店、麵店、水果店和麵包店一下子變少了。
霓虹燈亮起後,街上才開始醞釀活力。由於這裡屬於校區外的範圍,不必擔心會遇到輔導員,但她還是怕遇到熟人。她來到河畔時,突然感到飢腸轆轆。一排柳樹下,有十幾個還沒有開始營業的攤位,正在河邊垂釣的男人啃著飯糰,注視著水面。扣除回家搭電車的車票錢,她只剩下不到一百圓。
她走進街角一家離大馬路二十公尺的便利商店,買了一個甜麵包。額前微禿的老闆接過一百圓硬幣,親切地對她說了聲:「謝謝惠顧。」這時,由紀發現櫃檯的厚紙上寫著「徵收銀員」,入口的自動門上也貼了相同的紙。
「你們徵的收銀員要工作到幾點?」
「沒有明確規定,最好是傍晚生意忙碌的時候來幫忙。」老闆回答時露出親切的笑容。
「白天不行嗎?從上午九點到三點左右。」
「是妳要上班嗎?」
「對。傍晚之後,我要去簿記學校上課,所以不能打工。」
由紀想起剛才在路上看到的商科學校看板,編了一個謊言。老闆用僱主的眼神重新審視了由紀。
「如果妳不介意的話,白天班除了收銀台以外,還要幫忙搬貨和分貨。」
於是,他們談妥時薪五百五十圓,從九點工作到三點半,午休三十分鐘,週日休假,月底付薪水。
第一天上班時,由紀帶去的履歷上只有生日和學歷的欄目是虛假的。由於由紀說了一口東京腔,老闆也相信了她說父母離婚後,從東京剛搬來外婆家的謊言。
她穿制服出門,在地鐵站的廁所內換上便服。上午負責拆商品,貼價格標籤,下午負責收銀台。雖然並不是重體力工作,但老闆接二連三地吩咐她做很多事。
一天可以領到三千三百圓,工作十天可以領到三萬多。她無法預測到底可以工作到什麼時候,一旦被學校或家裡知道,恐怕不得不被迫離職。
即使打工到月底,也賺不到目標金額。
打工第一週的星期五,由紀加班到天黑後才離開便利商店。馬路斜對面有一家書店,高中生、下班後的粉領族和中年上班族都在那裡翻雜誌。
當只剩下一個客人站在店裡翻書時,由紀小跑著過了馬路。她需要助跑激勵自己。
「呃,我需要錢,可不可以和我交個朋友?」
她用只有那個男人才能聽到的聲音問……
●
隔著木板牆壁,可以聽到阿堂誦經的聲音。
清晨五點半。開始誦經的前幾分鐘還很小聲,但隨著越來越投入,就越來越肆無忌憚,聲音大得幾乎連天花板也跟著震動起來。睡在隔壁房間的阿中最先被吵醒,接著是走廊對面六人房的人,然後是對面隔壁的房間,所有人都像骨牌倒下似的逐一被吵醒。六點的時候,有如蒸氣火車爬上坡道般的喘急聲傳到了活動室對面的女病房,整棟病房大樓都好像被火車拉著走。阿中說服自己是在黎明時分搭上了臥舖車,無可奈何地閉上了眼睛。
當牆壁的震動達到最高點時,餐廳的鈴聲響了,誦經聲也戛然停止。
阿中在護理站前的盥洗室漱洗過後,去病房大門口拿了報紙,回到自己的房間裡,從早報的頭版開始看起。「反射鏡」專欄的內容和他一個月前寫給報社社長的信完全相同。至少阿中相信是這麼一回事。
阿中每個月寫四封信給社長和負責「今日運勢」的責編,隔週會陳述自己的意見。幾個月後,這些內容就會出現在報紙上。
──一月出生的人,「今天要把之前未完成的工作處理完畢」。
──二月出生的人,「輕視規定將後悔莫及」。
這兩則內容都和他上個月月底寫給「觀星天人」專欄的內容一模一樣。盜用別人的創意,竟然連一封感謝信都沒有。阿中已經習慣被外面的人輕視了,所以不會為這種事生氣。
八月出生的人「要運籌帷幄,好好表現」,這一點和阿中的預測大相逕庭,但他還是決定按原定計畫外出。
秀丸爺爺已經站在窗戶下的中庭裡,拄著枴杖望著天空。秀丸爺爺每天早上都會從四樓到一樓,仔細觀察這棟病房大樓的各個樓層,這是他多年的習慣。阿中打開窗戶揮了揮手,秀丸爺爺也看到了他,向他道早安後笑了起來。
「等一下去接你。」
阿中打開了只能開到半個頭寬度的窗戶,對著樓下叫了一聲。秀丸爺爺輕輕揮了揮手。
早餐像往常一樣,生雞蛋、味噌湯、滷海帶、炒酸菜。阿中在桌旁坐下時,已經有十個人把剩飯倒進了塑膠桶裡。
村上先生坐在角落的位置,很有耐心地仔細咀嚼,他把炒酸菜放在舌頭上細細品味,小口小口地喝味噌湯。負責收拾的阿定和小黑眼神憤恨地看著吃飯速度特別慢的村上先生和阿中,當村上先生放下筷子準備喝口茶時,阿定立刻跑了過來,收走他的托盤拿去流理台。
阿中拿著剩飯走到餐廳角落去看烏龜。盆子裡的石龜伸長了脖子,一動也不動。當初不知道是誰從河裡抓回來的,二十年來,牠的龜殼直徑已經長到四十公分了。石龜沒有名字,大家只能叫牠「阿龜」。昭八每隔三天會為烏龜換水。而烏龜會連同水一起把掉在眼前的飯粒吞下去。
阿中打掃完餐廳後,昭八提前結束工作回來了。他用不太能發出聲音的嘴巴「啊、啊」地叫著,忙不迭地做著手勢。他想要說,他馬上去換衣服,等他一下。
五分鐘後,他身上穿了兩件毛衣、換上了布鞋、戴著棒球帽現身了,胸前掛著Nikon的照相機,一臉得意的表情。
昭八雖然失聰,也無法說話,但他會讀唇語,所以知道別人在說什麼。自從在某次運動會上要求他負責拍照後,他就瘋狂愛上了攝影,用殘障年金買了一台單眼相機。他每個月的零用錢幾乎都花在買底片和沖洗照片的費用上,然後把照片分送給大家,分文不取。如今,他儼然是病房專屬的攝影師。
阿中和昭八去對面的菊花病房找敬吾。
敬吾住進這家醫院還不到一年,他光腳穿著拖鞋就準備出門,昭八制止了他,為他在開襟衫外加了一件厚外套,換上了球鞋,再用梳子幫他梳理了一頭亂髮。敬吾一臉乖巧的表情,就像一年級新生讓母親為自己梳理。
敬吾比剛進醫院時的表情安詳多了。當時,被三個大漢從車子上拖下來的敬吾目露兇光,呆立在原地,瞪著天空。一頭及肩的頭髮好像擦了很多髮膠般發硬,脖子上積滿了咖啡色的體垢,腳上的指甲長到把腳趾頭捲了起來。他那個曬得黝黑,像農夫一樣的父親猶如押犯人般押著兒子的脖子。他母親不斷地在他耳邊重複:「別怕,別怕。」
那個女人就是昭八的親姊姊,昭八進這家醫院三十年,她從來不曾來探視過,只有昭八的母親和父親偶爾會來看他。
聽說昭八當初被警官送進這家醫院時,腰上還繫著繩子。他在家中的儲藏室放了一把火,把儲藏室和隔壁家都燒光了,幸好沒有造成任何人傷亡。由於他智能不足,再加上心有鬱悶,所以把他送進了醫院。警官在院長的診察室內解開昭八的腰繩後就轉身離開了,簡直把自己當成了送貨員。
昭八完全搞不清楚狀況就被送進了醫院裡,最初幾年過得畏首畏尾的。他無法說話,再加上他也無意說話,其他人都不知如何和他相處。吃飯的時候,只要旁邊有人,他就一口也不吃;把他關進了保護室,再把食物送進去時,他就在轉眼之間把食物吃得精光。
昭八住在隔離病房時,曾經逃離醫院三、四次。他從鐵窗之間或是廁所的天花板逃走,還有一次是趁職員忘了鎖門時,巧妙地逃了出去,但他每次都回去自己的家。翌日,他的家人會打電話到醫院說:「昭八又回來了,等一下我們會送他回去。」
第二天,昭八的父母把他送回了醫院。
「昭八,村裡和家裡都已經容不下你了。」
昭八面無表情地聽著母親含淚對他說的話。
「放火燒了自己家和鄰居家的人,怎麼還能夠繼續住在村裡?我們之前賠償了隔壁的萬次爺爺,但問題並沒有解決。如果你回家,全村的人整天都會提心吊膽,況且,你姊夫根本容不下你。
「所以,希望你能夠瞭解。這裡就是你的家,你要在這家醫院和大家做朋友,讓醫生和護士喜歡你。只要你乖乖的,媽媽盡量每個月都來看你。雖然我很想更常來看你,但因為要顧及你姊夫的想法,沒辦法這麼做。媽媽從來沒有忘記你不幸的人生。媽媽會來看你,所以你以後不要再逃回家了,知道嗎?」
昭八的母親最後還是沒有讓眼淚流下來。他的父親紅著眼眶,在一旁靜靜地聽著。昭八茫然若失地聽著母親說話。
「昭八就拜託各位了。」
昭八的母親鞠躬拜託護理站內的護士,也對聚在餐廳的其他病人鞠躬,說了相同的話。
護士送昭八的父母走向出口的方向,昭八沒有跟上去,就站在護理站前目送他們。
那次之後,昭八不再試圖逃走,他母親也如約每兩個月來看他一次。
五年後,他母親罹患子宮癌去世。父親每年中元節和新年來繳住院費時,會順便會面,但父親也在四年後因腦溢血離開了人世。
雙親去世後,昭八年金不足的部分申請了低收入補助,在經濟上也和家裡完全斷絕了關係。
敬吾的父母,也就是昭八的姊姊、姊夫送敬吾進這家醫院時,對主治醫師隻字未提昭八的事,當然也沒有去探視昭八。
後來,是一位資深護士發現昭八和敬吾的戶籍地址相同,察覺了他們之間的關係。追問敬吾的母親後,終於得知了真相。
既然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弟弟也和兒子住在同一家醫院,敬吾的母親也不能再無視昭八,在探視敬吾之後,也順便來到開放病房,把敬吾也住進這家醫院的事告訴了昭八。
比起擔心外甥精神出了問題,昭八更為能和姊姊重逢以及和敬吾住同一家醫院而感到高興。
三個人一起走去蘭花病房。
秀丸爺爺坐在六人病房角落的床上練書法,看到阿中他們,立刻收起硯台,把寫了毛筆字的紙捲了起來,細心地擦拭毛筆後,用水桶裡的水洗乾淨。
昭八把輪椅從走廊上推了進來,兩人一起攙扶著腳不方便的秀丸爺爺坐上輪椅。
「不好意思,謝謝。」秀丸爺爺深深地鞠躬道謝。
他們向病房護理站裡的護士打了聲招呼說:「我們走了。」即使他們幾個病人單獨外出,護士也不會皺一下眉頭,全拜秀丸爺爺的好人緣所賜。
走出大門後,必須沿著ㄑ字形的山崖下山。沿著坡道剛走出院區的位置,豎了一塊像溫泉勝地常見的四方形看板塔,白底上用黑字寫著「四王子醫院」。由於油漆快剝落了,所以不太引人注目。
醫院的招牌上雖然沒有「精神病院」的字,但當地人都知道這家醫院的性質。
十五年前,病人們曾經排著隊伍外出。二十個病人等間隔地排成隊伍,宛如士兵般目不斜視地往前走,只有最前面和最後面是醫護人員。他們花三十分鐘走到紫藤花盛開的宗國寺,又花四十分鐘走去水質清澈到可以游泳的伊吹川,再花二十分鐘走到有古墳的高塔原。這是他們每個月一次的列隊散步。不久之後,有一半的病房不再上鎖,病人在白天時可以自由外出。可以隨時走出醫院這項政策是如同監獄拆除了高牆的重大改革。
病人們紛紛走到坡道下方的招牌前,踏出一步後,立刻折返回來,彷彿前面有禁止通行的欄杆擋住了去路。於是,不敢單獨外出的人聚在一起,還是排著隊一起外出。有一天,阿中在車站前的三橋食堂吃麵,旁邊的客人目瞪口呆地看著病人的隊伍經過,老闆用食指在耳朵上方畫著圈,以動作向滿臉錯愕的客人說明了情況。
如今已經看不到這樣的景象了。前一陣子,阿中也一個人走進了三橋食堂,剛好遇到五、六名病人外出散步,老闆說:「那裡的人最近走路也很像正常人了。」老闆似乎以為阿中是住在附近的居民。
三橋食堂的兩側正在籌備開電器行和書店,他們就是在這裡遇到了迎面而來的島崎由紀……
聽到護士叫自己的名字,她從沙發上站了起來。
放了觀葉植物的候診室內只有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女人,即使島崎由紀起身,那個女人仍然埋頭看著雜誌,不知道是否擔心由紀尷尬。
門後的護士拉開簾子,指了指置衣籃。
由紀脫下毛衣,拉下裙子的拉鍊。藍色毛衣雖然摺得整整齊齊的,但袖子手肘的位置仍然鼓鼓的。
「內衣褲也脫完後,請穿上這個。」
護士親切地說著,遞給她一件手術服。
「好。」
由紀輕聲回答,接過手術服。
白色棉質手術服並非新品,但肌膚可以體會到清潔的感覺,想到之前有人穿上這件手術服,躺在手術台上,由紀的心情稍...



 共
共  2011/12/14
2011/12/14 2011/12/14
2011/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