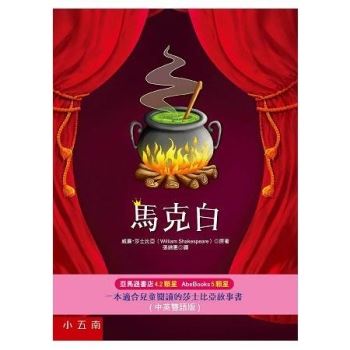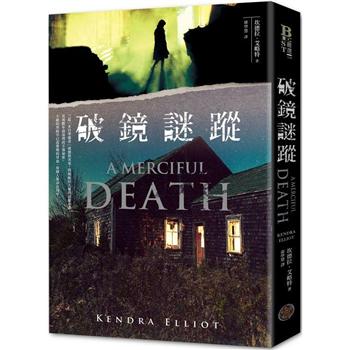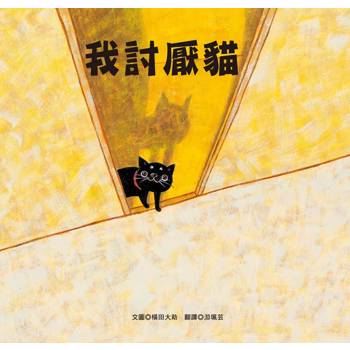序
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的設立,乃緣於大師對文學的熱愛與期待。他曾表示,在他學佛修行與弘揚佛法的過程中,文學帶給他智慧;他也日夜俯首為文,藉文學表達所悟之道。因為他深知文學來自作家的人生體會,存有對於理想社會不盡的探求,也必將影響讀者向上向善,走健康的人生大道。
幾次聆聽大師談他的閱讀與寫作,發現他非常重視反思歷史的小說寫作以及探索現實的報導文學,而這兩種深具傳統的文類今已日漸式微,主要是難度高且欠缺發表園地,我們因此建議大師以這兩種文類為主來辦文學獎;而為了擴大參與,乃加上與生活息息相關的人間佛教散文。大師認同我們的想法,這就成了這個文學獎的內容。此外,大師來台以後,數十年間廣結文壇人士,始終以誠相待,他喜愛文學,尊敬作家,於是而有了貢獻獎。
這個獎以「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為名,意在跨越政治與區域的界限,從二○一一年創辦以來,由專業人士組成的評議委員會和分組的評審委員獲得充分的授權,運作相當順利。我們通常會在年初開會檢討去年辦理情況,針對本年度相關作業進行討論,除排定推動程序,會針對如何辦好文學獎,進行廣泛討論,特別是宣傳問題。
二○一三年,我們把前三屆人間佛教散文的得獎作品結集,由香海文化出版,一套三冊,分別是《瞬間明白》、《推開黑夜》、《娑羅花開》,各以其中一篇為書名,組合起來竟似悟道後行動如花開璀璨;去年,報導文學讓我們驚喜連連,於是趕在贈獎典禮之前把它出版了,人間佛教散文原就相當穩定,一併付梓問世,各以其中一篇的主題命名,是為《綠色沙漠》與《回歸圓滿》。今年的報導文學也有好成績,人間佛教散文今年首度排名,更有亮點,一併出版,是為《你從哪裡來》、《琉璃有光》,和去年一樣委由聯經公司出版。
我們將更專心更有耐心地把這個獎辦得更好更有意義。
李瑞騰
序
性情所鍾,即為有佛
「人間佛教散文」創作獎進入第五年了。五年來參與這獎的評審,細細閱讀每一篇作品的當下,是我擾擾俗世生活中難得靜定喜悅的時光。二、三十年來,我評審過國內大大小小的文學獎,美好的感覺當然有──其中包括感動、驚喜等等,但質疑、痛苦的經驗也從來不少──緣於永遠會有一些怪異、糾纏、冗漫、艱澀的書寫,讓人不耐。唯「人間佛教散文」,容有生嫩稚拙的文字、附會勉強的佛理,但基本上都平易可感,也都不失樸實真誠,更何況確有曖曖含光,觸人心弦、發人深省的佳作。其所寫的人、事,絕非日常生活中陌生罕見的人、事;其所興發的情、思,則絕為我們自己往往就有的情、思。這樣的作品,除了備覺親切之外,更奇妙的是讓我們經由這份親切,獲得平日求之不易的寧靜、篤定,繼而產生清清淡淡卻實實在在的喜悅──原因無他,示現的是眾生性、是眾生情,我們因之能入,亦因之而能出,遂在平平實實中感受,亦在自自然然中領悟、昇華。
「人間佛教散文」創作獎,四年來每年皆取十名,不分名次,蓋其旨本在希望透過此吉光片羽,見證人世的真實、佛理的親切,固不須別其高下、分其軒輊。但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既然它也是文學創作,則不能不慮及藝術表現的品第層次,畢竟,那也是真實的存在。於是,自本屆開始,「人間佛教散文」改取八名,排其序位──我們要強調,這不是內涵義理的分等,而是藝術表現精緻程度的明確化──當然,這都只是評審的觀點而已,並非優劣的絕對準據。
得獎的八篇作品,寫親情的最多,計有〈老菩薩〉、〈父親的傷〉、〈那爺倆午後的賞鳥活動〉等三篇,有趣的是,三篇都描寫了無限溫暖的祖孫之情。祖孫之情是近年各文學獎常見的題材,此一現象多少反映了現代社會家庭親子關係變遷的實相。三篇的文筆都自然、真誠而絕不炫奇,文中閃耀的燦然親情照亮每一位讀者的內心。〈老菩薩〉尤其精彩,交織悲喜之情而終歸為喜──此即佛諦,評審一致推為首獎,良有以也。寫師生之情的一篇:〈一個都不能少〉。文章以第三者視角,藉由偏鄉最常見的場景以及最質樸的筆調,為一位可敬的教師塑像,其間穿插孩子的純真,迤邐寫來,緊張、輕鬆,嚴肅、詼諧兼而有之,讀之暢快淋漓,充滿感動。寫情傷的二篇:〈上山〉、〈獸身譚〉。二文一平一奇、一柔一剛,風格雖迥異,而最終皆能尋回自我,淡定面世。類似的作品雖不少見,但二文仍因作者敘寫之自然真切,乃使讀者自得興悟啟示。最後,寫生死、寫無常的亦有二篇:〈琉璃光〉、〈假如我活一萬歲〉。二文風格亦異:前者獨思冥想,後者眾聲喧嘩;前者淨秀、後者縟麗;前者讓人在歎惋惆悵中參透生死無常,後者讓人在衝撞錯愕中翻越生死無常,皆可讀之作。
我個人綜覽這五屆的作品,確實感受到技巧的精進、水準的提升,而不變的是,較諸他類文學獎作品恆多一分真樸平易──這原是人性的本質,也是佛理的本質。在這日趨扭曲錯亂的年代,「人間佛教散文」顯然提供了淨化的甘露,幫助我們找回本心,幫助社會找回和諧。衷心期盼「人間佛教散文創作獎」年年持續,步步生蓮,讓我們得以永遠享受如春風的和煦、如春雨的滋潤、如秋陽的溫暖、如秋收的豐實。是為序。
何寄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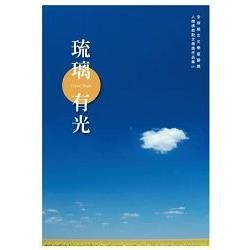
 共
共